书名:南明史:1644—1662
作 者:[美]司徒琳
译 者:李荣庆 郭孟良 卞师军 魏 林
责任编辑:易 强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3116-3/K·2388
中文版序
朱维铮
17世纪中叶的南明,其实是四个或五个抗清政权的统称。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抬举明帝国某个亲王充当领袖,彼此间却并没有承袭关系。每个政权的生存时间,短的不过一两年,长的也仅十来年。通计不到二十年,只可称作历史的瞬间。
历史也真古怪。有时上百年过去了,留下的记录平淡无奇。但有那么若干瞬间反而在后世会激起回响,并且引发历史学家们不倦的探索兴味。
南明史便显然属于这样的瞬间。
还在20世纪初,那些愤恨清朝腐败统治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排满革命”的名义下发誓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战的时候,如何从南明的历史先例中汲取自己的革命诗情,已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诗人的愤怒,不能代替冷静的历史研究。清末最热心歌颂南明为抗清而献身的忠臣义士事迹的,往往也是光复会成员的南社诗人们。但也正是这些以浪漫主义的热情为民国催生的青年们,在他们梦寐以求的反清革命成功后,发现迎来的不是“汉官威仪”,而是旧污陈垢装点的“假共和”。希望幻灭了,痛心疾首的悲吟代替了斗志昂扬的高歌。随着诗人的沉默,由近及远的历史沉思变得凸显,那远点便在明清之际。
事实上,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刚刚化作历史,关于南明历史的反思便已开始。清初江南相当一批学者在这方面都是有心人。新兴的帝国当局对于此种努力日感疑惧,终于在以宽容异端著称的康熙皇帝晚年,一次株连达数百人的史狱,使得南明史研究从此成为禁区。待到18世纪后期乾隆皇帝出于实用的考虑,将当年曾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下大功的故明降官降将贬作“贰臣”,意外地造成南明史研究变相开禁,那时有关南明的历史陈述早已残缺混乱不堪。当南明的课题在20世纪前期再度提上历史研究日程以后,人们发现如同研究17世纪即明亡清兴之际所有课题一样,对南明那十八年的研究,也必须从清理基本史实做起。
清理南明的基本史料和历史事实,吸引了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关注。章炳麟、梁启超、孟森、陈垣、胡适、钱穆、萧一山等,都早已发表引人注目的论著。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的但焘中译本在“五四”前夜出版,也起过推波助澜作用。久享盛名的大史学家陈寅恪的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更提供了一个实例,显示即使在一个“点”上清理历史事实,也何等不易。
或许这正是南明史研究缺乏综合性专著的原因。自从1957年谢国桢的《南明史略》出版以后,至今在国内未见再有类似专著问世。谁也没有想到,这几十年来,域外的汉学家已在南明史领域下过那么多功夫,终于导致首部英文版的综合性的《南明史》,在1984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刊行,并立即引起国际汉学界的广泛瞩目。它的作者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司徒琳教授。
还在研究生时代,司徒琳(Lynn A.Struve)便为南明时代的历史复杂性和研究的艰苦性所吸引,毅然放弃了已见成绩的文学研究,选择《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运用:清朝史籍中的南明》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并为此再赴台湾和日本进行长期研究。这篇优秀论文使她于1974年成为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嗣后再经十年孜孜不倦的潜心研究,终于完成了这部杰作。
说它是杰作并非夸张。作者征引的文献,包括国内外现存的有关南明诸政权的大量记载,以及20世纪中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是那样丰富。况且作者也不以直接引用为满足,而是对于征引的古今文献都细加考证,以确定其可信程度。这使本书的注释与正文结合成为相当严密的整体,再辅以详尽的参考文献目录,也使本书堪称读者了解南明信史的佳制。
以往我们的南明史论著,包括通史或断代史著作的有关篇章在内,常给人某种先立论、后举证的印象。将满汉间的民族冲突化约为爱国与否的斗争,将南明诸政权的建立简单说成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而对于那些政权本身的考察反而语焉不详,便是我们常见的陈述模式。司徒琳显然不满意这样的陈述模式。她的《南明史》将考察重心置于这些政权本身。她认为本书所考察的南明四政权是明朝世袭君主统治在首都失陷后十八年内的继续,因而也是导致明朝统治由强变弱的两大难题造成的内在困扰的继续。那两大难题便是“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正如本书引言最后所强调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是把明朝引向灭亡的唯一矛盾,“同等重要的是前近代经济变迁的多重因素也在起作用”。但作者所以将视野主要放在那两大难题的纠结不已上,是因为她认定历史事实已明白昭示,正是由于处在生死关头之时这种纠结造成的内部冲突反而越发严重,招致了抵抗运动节节失败和各个政权逐一消亡。人们自然可以对这样的见解提出异议,但倘若仔细通读全书,便很难否认那是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一个角度。
如同许多西方汉学家一样,司徒琳研究中国历史,力求保持客观的态度,而竭力避免对于个别人物和事件作出褒贬式的评价,尤其注意南明那些不同人物面对传统难题交替出现时的角色变换,或者说在实际历史进程中的心态和行为的变化过程。这使本书关于中文论著中常有定评的那些人物和事件的陈述,经常显得与众不同。见解本身可以讨论,但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多年来,我们的历史研究,过度热衷于所谓历史人物的评价,过度注目于某些历史积案的是非,而对于过程本身却往往不加细察,这难道不是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吗?
司徒琳的《南明史》,原著以叙事细腻,风格简练,文字优雅著称。承作者好意,在三年前中译本初稿刚出来时,便要我帮助审订。我是相信严复所立译书需要信、达、雅三准则的,而以为首要的是信,即准确表达原著的文意。作者的中文造诣本来很高,完全有能力自行校订,但仍以为中文译本由中国学者校订可能更宜于中国读者。校订改译的经过,作者为中文版写的后记已予说明。这回我再次应邀访问印第安纳大学,译稿已全部完成,于是不得不兑现诺言,通读之余,对译文作了若干修改,还是希望既信且达。至于是否给原已改订得很畅达的译文,略增雅意,抑或反而佛头着粪,那就不敢说了。
但我相信,司徒琳教授这部《南明史》中译本的出版,必将受到学术界同行和读者的欢迎。关心南明史的读者,有了一部深入浅出的好书可读;研修明清历史文化的青年学子,增添了一部系统性强而内容丰富的参考书。而研究明清史的学者们,不论对于本书的内容、结构和见解作何估计,想来都愿意一读的。因为本书在美国纽黑文和英国伦敦同时出版以来虽已有七年,但至今在欧美汉学界仍是关于南明的完整历史的唯一专著。我们至少可从中窥见海外说英语的同行们在这一点上的研究现状。
1990年12月
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高级学院
中译者序
这本由美国学者司徒琳教授撰写的《南明史》的汉译工作,缘起于我的研究生导师秦佩珩教授(1914年1月—1989年6月)的建议。抗战时期,秦佩珩先生由北方流亡到成都继续他的教书生涯。面对外族的侵略,先生抚今追昔,对南明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先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品评南明人物和史实,砥砺民族气节,寄托对北国的眷恋。上个世纪末,当秦先生看到这本英文版的《南明史》时,就建议我和郭孟良等另外几位研究生将其汉译。其中既有他希望了解海外汉学发展状况的意愿,也蕴含着秦先生深厚的民族主义爱国热忱。然而,时光荏苒,当这本《南明史》汉译本问世时,秦先生已经离世。我们谨以此汉译本《南明史》告慰先师的在天之灵。
美国汉学研究创始于19世纪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20世纪前期一批资深中国学者为躲避战乱,远渡重洋,进入美国高校,进行汉学研究。他们用英语写作,零星出版了一些汉学著作。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结束,为了解中国这个对手,美国公私机构,拨出专款,建立基金,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汉学研究。此后20多年,美国主要以台湾作为其汉学发展的依托,开展学术交流。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美国汉学教学体系也逐渐形成,著名大学都有专任教授主持和开办汉学课程。汉学学术交往重心也从台湾地区转到中国大陆。进入本世纪,越来越多的美国高等学府设置汉学课程,培养博士研究生,有关中国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大量涌现,其中不乏见解独到、值得存世之作。美国汉学已成为当今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不可或缺的一方重镇。
美国汉学有其明显的特点:首先是学术严谨。举此《南明史》为例,其书原文近300页,而注释、地图、索引、参考书目和附录等就占据130多页。书中所列中文、日文和西文参考书目达300多种。从这些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原作者在《南明史》的写作过程中,已将有关南明的重要著述大致收罗殆尽,足见原作者治学态度的严谨。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汉学严谨的治学风格应该为我们所敬重。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国内明史大家谢国桢教授于1958年出版的《南明史略》一书,对南明政权的更迭及各种政治势力消长条分缕析,述论中肯而全面,是南明史治学不可忽略的大作;而司徒琳教授的《南明史》出版于1984年,却未将谢国桢教授的《南明史略》列入其参考书目,这不能不说是美玉中的微瑕。
其次,美国汉学重视史论,长于论辩。这种情况是和美国史学传统相一致的。美国历史殊短,大的历史事件几乎都发生在眼皮底下,史学考据意义不大。因此,解释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不同观点间的互辩,成了历史研究的特点。对于中国历史事件,美国学者并不追求做到每事考证确凿,他们很大的功夫都用在了对新奇的理论和观点的追求上面,所发表的见解常常出人意表。1964年,美国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亚洲研究》上连续发表题为“中国乡村集市和社会结构”的系列论文,洋洋数万言,建立起“蜂窝”模型,比况中国乡镇集市,分析其社会功能,字字珠玑,句句落到实处,令人折服,可以算得上海外汉学的典范。
司徒琳教授的《南明史》也有其史论支撑点。它以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做为基础,不断释放史学见解。在其历史叙事中,朝臣中清流和浊流的不睦,文官武官的倾轧,成为南明政权崩塌的重要原因。这种见解和国内明末党争的论述相互呼应,显得平实而贴切。然而,读者应该留意,英文版《南明史》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是“忠臣”(Loyalists)。在作者看来,忠臣是南明诸政权的支撑者。其实,南明时期,弘光等政权的相继建立和维持是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激发分不开的。清朝之前历代的中国虽然是帝制形态,但汉民族居住区,府州县分界而治,各级官员考绩流转,文官国家制度早已形成,并且得到黎民百姓的认同,遇到外族入侵,就会激成民族主义的对抗。明末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事件无不与民族主义反抗情绪相关联。南明时期,农民军也和南明政权妥协,联手反抗异族的入侵,国内史学界称之为“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这种情形说明,在统一的文官国家制度发育较早的中国,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意识早已形成,它的存在并不借助现代国家的形成。上个世纪末以来,西方学界出现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研究热潮。但是,涉及中国民族主义时,大多数研究只关注民国以来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他们否定中国帝国时期存在着民族主义,而认为民族主义只是现代国家的产物。比如,加州大学教授韩禄伯(Richard E.Strassberg)于1983年撰写的《清初文人孔尚任的世界》就是如此。书中使用“Nation”这个词时很谨慎,往往用“忠臣情节”“反清情绪”等来替代民族主义一词的使用。这一点和英文版的《南明史》缺少民族主义的讨论是一致的。有关明清之际的海外汉学著作中民族主义讨论的缺失,反映了西方学界在中国问题上价值体系的特质。这或许正是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的分野所在。指出这一点并无损于这本《南明史》的价值。正相反,译者认为这本《南明史》用西方人的视角和方法解读了明清之际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它严谨的历史叙事,独特的史学见解,为中国历史研究做出了贡献,是海外汉学著作中的佼佼者。
《南明史》一书的汉译曾得到各方的关心和支持,在此新版付梓之际对他们表示感谢。译文对原文或有曲解和误译,都因译者肤浅所致,并非有意而为,读者诸君其原宥之。
李荣庆
2015年夏 于临海
英文版序
[美]司徒琳
众所周知,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学者才使用“南明”这一称谓1。而在17世纪把受了致命伤的明朝取而代之的清朝,此时其本身亦已“内忧外患”交相困扰,步入了最后的几十年。“南明”一词的晚出是可以理解的。此词与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对其他朝代,尤其是对南宋的称谓一样,意味着对某些政权表示尊重,视其为正统。而清朝官方对这些政权的态度是尽量予以抹煞。大多数清朝学者提及1644至1662年这段时期,总是称为明末、明季、南疆,或是用前朝亡国的典故以为暗示。但是在20世纪头十年,清朝被推翻,民国肇造,反满情绪随之而起,于是南明一词广泛使用。不过,本书使用此词,只是为了行文方便,无意赋予这一时期以特殊的地位。要是另有用意,那也只不过是表明对这一历史研究课题的尊重而已。
西方学术界对南明几乎没有什么研究。过去十年,无论是质还是量,对17世纪中国的研究大有进展,但是有关该世纪中叶的历史却是一片空白。这种对南明反抗清朝征服中土的忽视或回避,原因或许在于,卷帙浩繁的原始资料不是分散零乱,就是颇有问题。1970年,我还是研究生,即已开始思考这些问题。1974年,我提交博士论文,也涉及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2。而后十年,我一直觉得这些问题令人烦恼。但是在这几年中,有关的参考书目我已有所掌握,对于哪些著作是南明原始记录也所知颇多,我尽量使本书立足于最可信的资料之上。这些资料不是出于亲历目睹者,即是出于事后不久作辛勤搜求者,我摒除了大多数清人的第二手和第三手资料。对于道听途说之作,即使出于我所喜欢的作者之手,也不予引用。因此,对南明史有所知的读者会感到惊奇,在我的注释和引用书目中,一些人所熟知的著作极少出现,甚至绝不提及。我不能说,有关南明的第一手好资料,我已搜求殆尽。遗漏在所难免,而且有些重要著作我无法获得。至于大量的20世纪南明史著作,大多供新闻与宣传之用,因此只引用在我看来其中最有学术价值的那部分。
中国人如何写南明史,此事本身就饶有兴味。从1640年到现在,中国史家一直认为那个时代意义重大,他们的观察方法常有改变,这反映了过去340年中国学术环境的各种变化。这些变化有时微细,有时剧烈。要是我在本书中不讨论,我对南明史实的处理方法与过去3个世纪各种诠释相比,是彼此符合,互相偏离,还是走中间路线,那么,本书的叙述将会是迷雾一片。若是在注释中讨论有关南明材料真伪的大量问题,将会大大超出本书的篇幅。考虑到这一点,同时也为了满足同行的兴趣,我打算另写一本南明史学史,既作为中国史学的“社会学”研究,又可供资料指南之用。就目前而论,治南明史者可参考刊于《剑桥中国史》第七卷的有关南明书目的拙作。此外,他们定会和我一样,为已故谢国桢先生的《增订晚明史籍考》的出版感到高兴3。
在整个中国历史中,17世纪是头等重要的时期之一。数十年中酝酿而成的变化浪潮在该世纪中叶达于峰巅,而后浪花四溅,散为各种事件,既令人振奋,又使系统的研究与诠释甚为困难。大多数西方学者对此的注意力集中在相对稳定的早期和晚期,对于中期发生之事避而不谈。那些敢于探索中期状况的人所采用的方法颇值得赞扬。他们对地方一级的事件与变局作了细致观察,揭示了在某些地区诸种因素如何相互交错。此外,这些地区研究也揭示了人的因素,满足了我们想了解当时真相的要求。另一类著作是从经济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阶级对抗出发,地区研究颇得此类著作之助,不过并未受它们的束缚。更为传统的看法则重视政府官员是否具有道德与行政才能。另有不少著作描写有名的明朝忠臣以及其他各色引人注目的人物。这些看来是富于戏剧色彩的老生常谈,但是往往很符合那个时代。一位同行恰当地指出,“南明事件确实多彩多姿。即使仅注意到最可靠的原始材料,各色人物和事件也令人不可思议。……”4
我认为这些方法都有效,但又感到,只有众多学者以各种相关的方法作了大量研究之后,一部扎实的17世纪中期的通史才有希望出现。此外,在我看来,由于对当时重大的政治与军事发展缺乏清楚而全面的解释,17世纪中期史的研究工作不易进行。美国同行们把此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工作集中在清朝方面5,而我比较熟悉明朝方面的资料。因此我觉得,目前我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写一部像本书那样的既全面又不铺陈的南明通史。至于明朝如何衰落,满洲如何成功,明朝的理学文化如何影响忠贞之士的行为,百年来社会经济脱序和政治动乱的关系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在本书中亦会有所了解。我设法适当地把这些问题显示出来,但回答这些问题不是我的目的。我宁愿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这一丰富多彩的时代作一个精确而又全面的观察。
地图
1.南明各朝主要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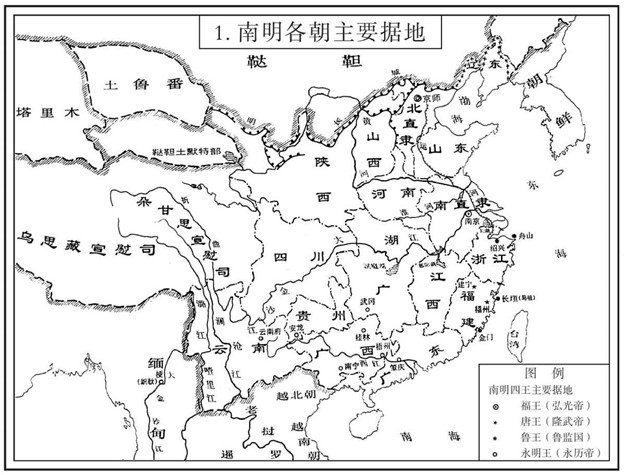
2.弘光防御计划(164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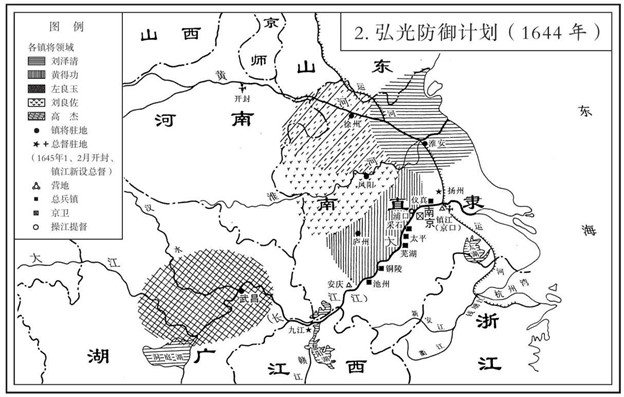
3.清军征服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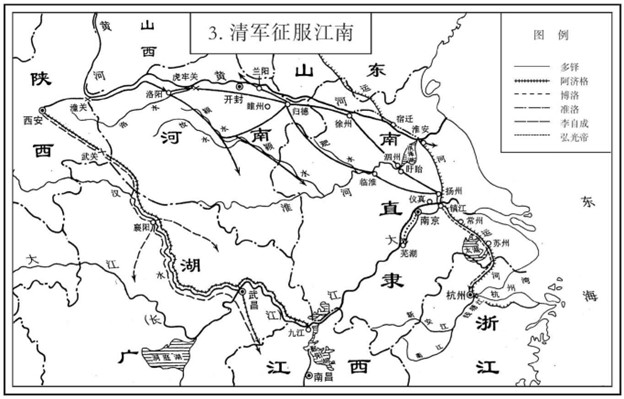
4.长江下游主要抗清中心(1645年夏—1646年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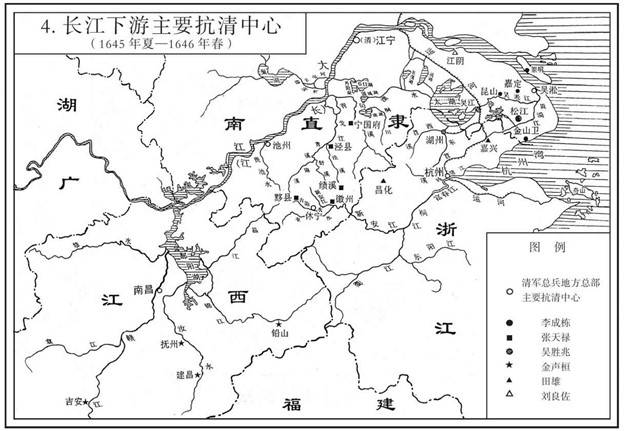
5.鲁监国与隆武时期的抗清形势(1645—164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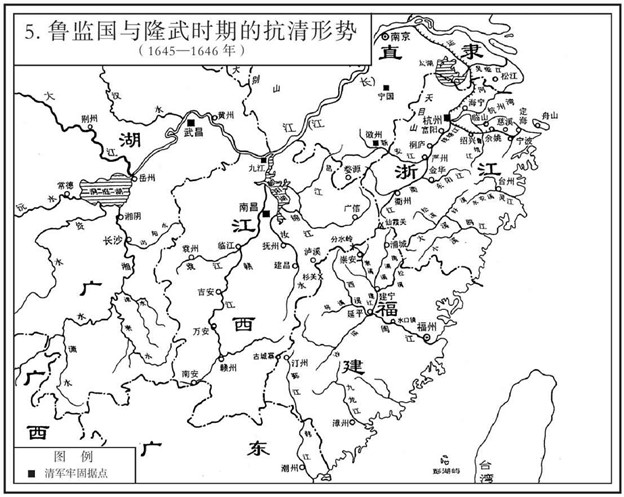
6.湖广明军据点略图(1645年冬—164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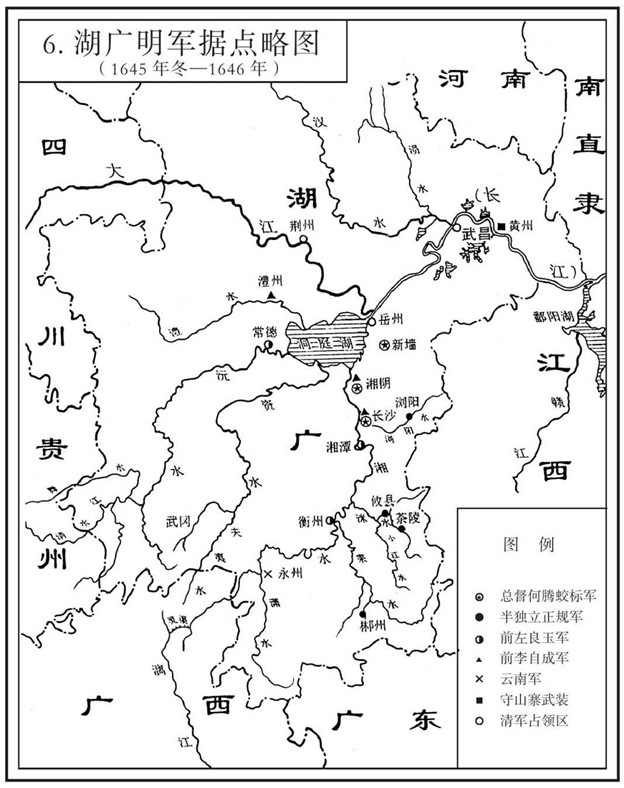
7.清军侵入浙东与福建(1646年7—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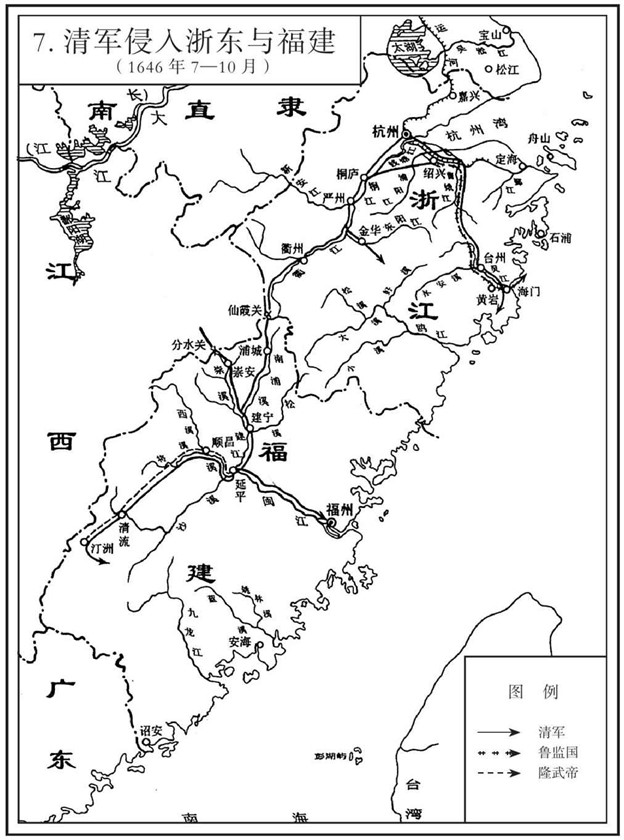
8.清军首次侵入两广与湖广南部(1647—164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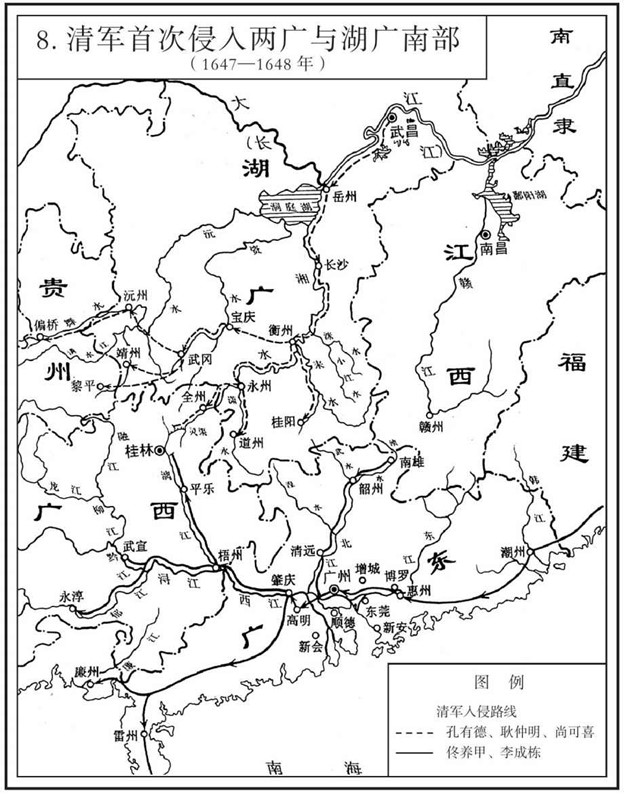
9.永历帝行踪(1647—164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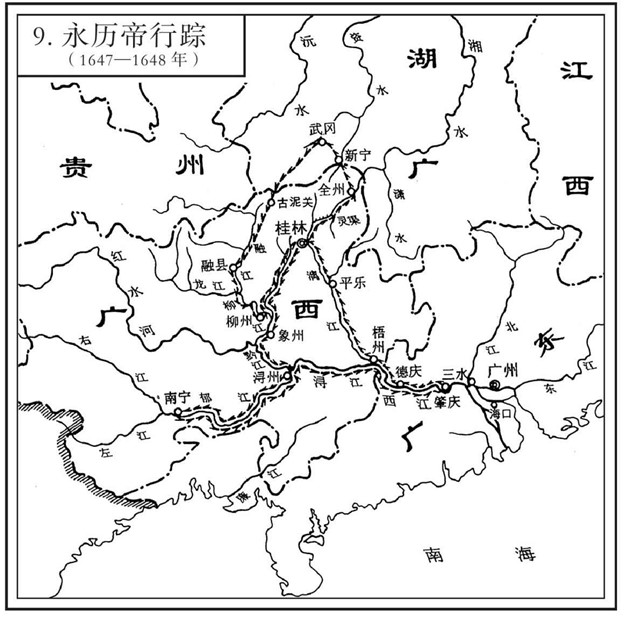
10.鲁监国主要行踪(1646—166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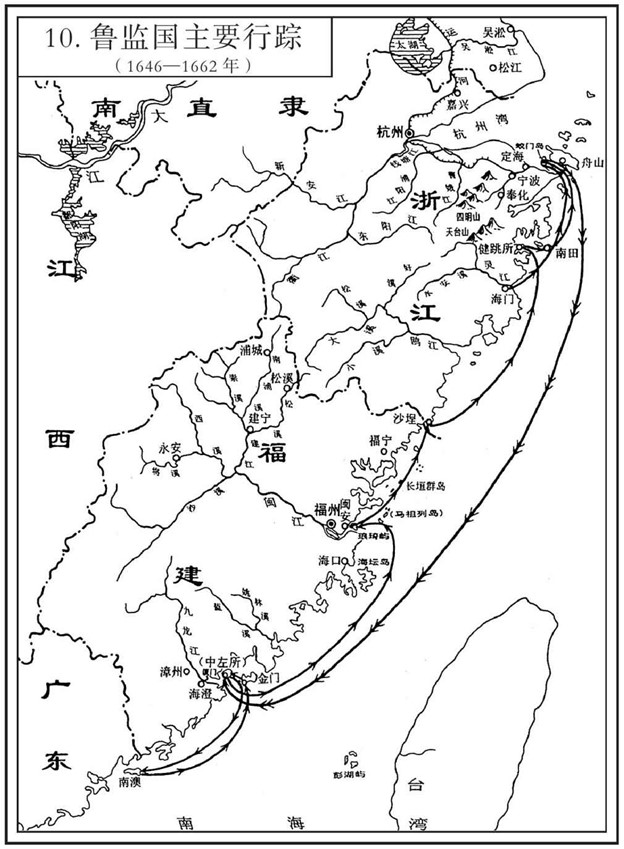
11.李自成残部主力转移(1646—164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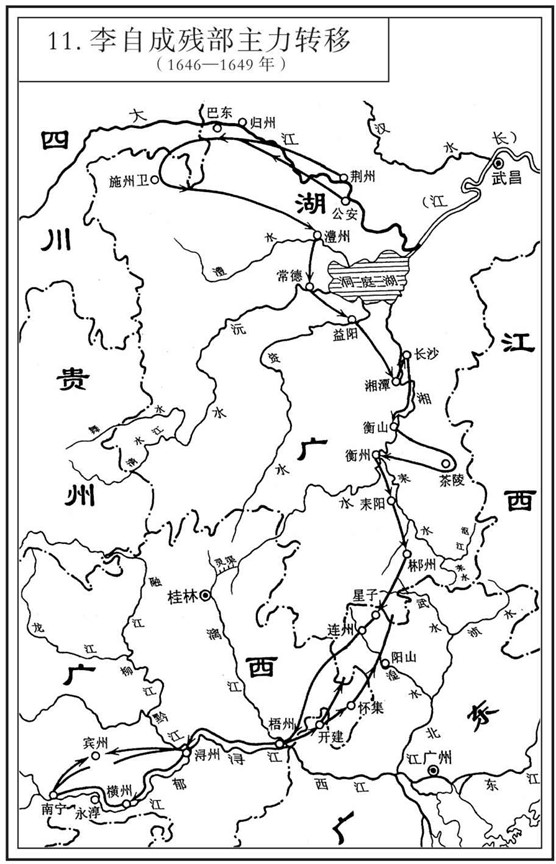
12.清军第二次侵入两广(16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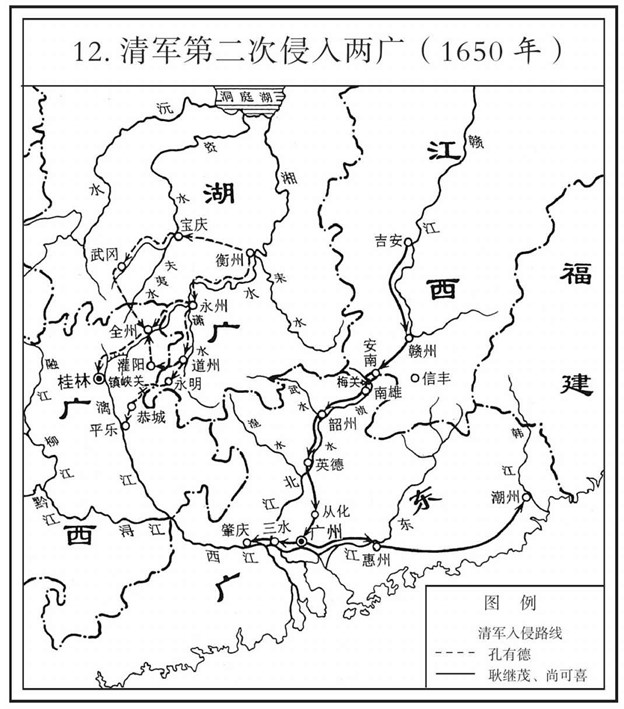
13.李定国与孙可望的东进战役(1651—165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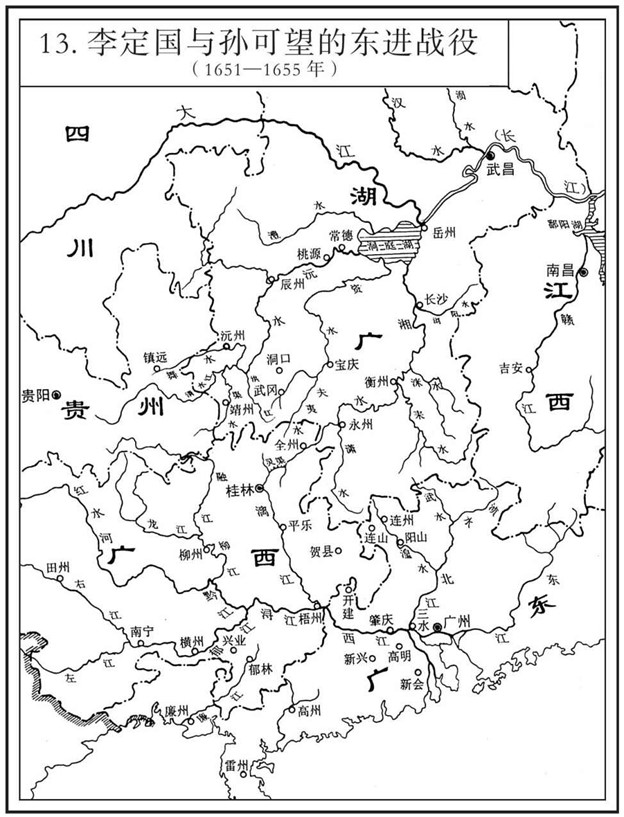
14.永历帝行踪(1651—165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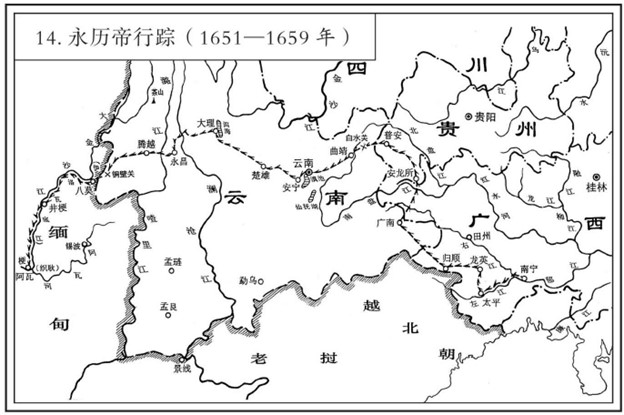
15.郑成功主要行踪(1647—166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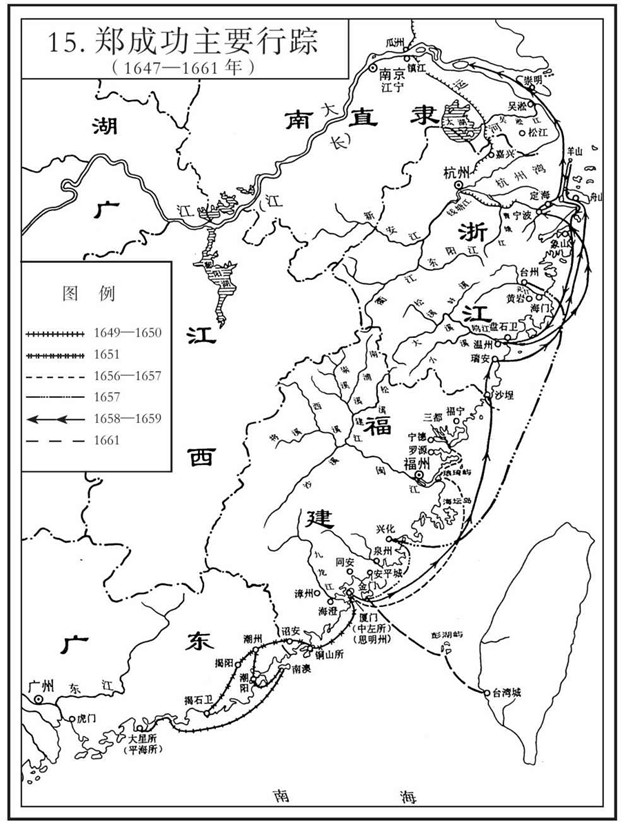
16.清军侵入贵州、云南(1658—165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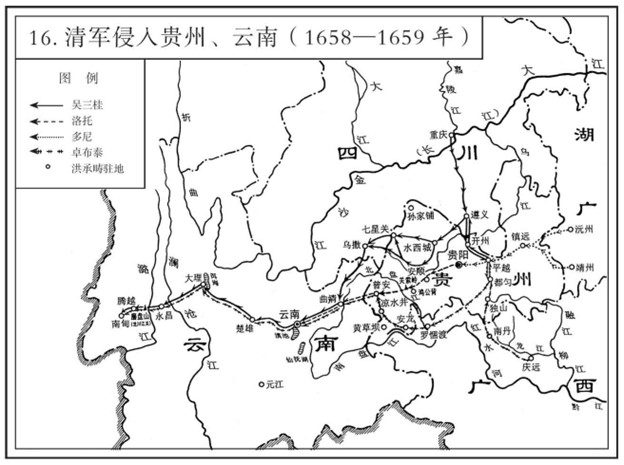
17.长江之战(165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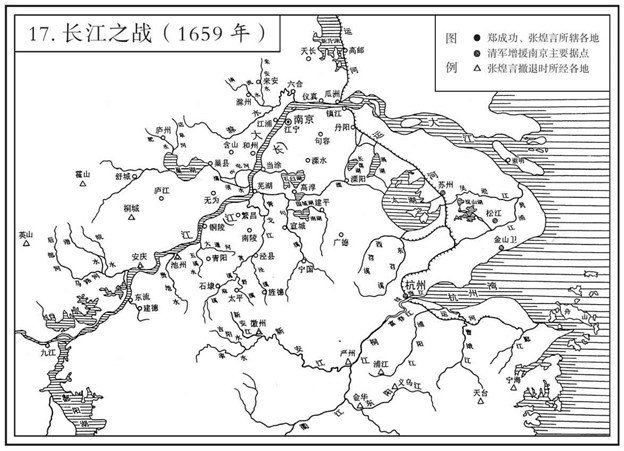
引言
明王朝究竟终于何时?这是个颇有哲学意味的历史问题,任何答案都或多或少带有某种随意性6。就中国通史的教科书或大事记来说,指出1644年便够了。那一年的事件无疑是重要的:明朝的崇祯皇帝,在李自成的叛军践踏北京并攻陷皇宫之际,自尽了7;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便与满洲的摄政王多尔衮联合,使满人得以将叛军逐出北京,进而占领了整个华北平原8。可是,严格地说,1644年并非明亡清兴的分界线。满洲领袖皇太极,还在1636年,就做了国号为清的新王朝皇帝了;而永历帝,明朝最后一名自称君临全中国的亲王,却到1662年才被灭。
倘若探究国家兴亡旨在寻求启迪,则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便会凸显。对于1644年前满洲的诸多研究,当然着重于他们从寻常部落到独特国家的演化,以及他们的太祖努尔哈赤(1559—1626)的关键业绩9。至于明王朝在什么时候确认完结——换句话说,它力量丧尽而败局已定在何时——则是一个有点阴郁,却能活跃想象力的问题。
那是在声名狼藉的太监魏忠贤窃夺权柄、使得“朝廷的政治与道德可能属于帝制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10的17世纪20年代吗?或者,发生在同一世纪的30年代,即虽然有了个精明的皇帝,而明王朝的政府仍然衰颓和缺乏士气,既无力阻挡满洲内逼乃至时而突入东北边的长城,也没法将“流寇”活动限制在西北部陕西省境内11的那个时期?此外还有判断灾难根源在于万历朝(1573—1620)的,认为万历皇帝打破了长期拒绝上朝的纪录,从而造成了“宪法”的危机,至明亡而余波犹存12。可是假如考虑到每个主要王朝的统治中期往往会有财政难关,那么问题又似乎出在嘉靖朝(1522—1566)的初期,因为此时朝廷财政的具有惯性的陈年旧例,无法适应变化迅速的经济需求,因而明政府应付宏大问题,尤其是军事问题的努力必然受挫13。
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下去,无疑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起源,也就是追溯到人类受生之初所有胚胎都已蕴含死亡的基因。幸好我没有追步这类偏爱的愿望。
本书的研究,只是直截了当地将明朝君主世袭制度的结束,定在某个时间。过了这个时间,作者便认为没有真正的明朝君主可言。本书亦想阐明,在明都北京陷落已经整整18年以后,明朝的君主世袭制的灭亡时刻是怎样到来的。本书不拟对明朝被削弱和复兴受阻的种种因素逐一给予精确的评估与分析,然而本书特别注意1644年前后一再出现的两个问题,它们使我们看穿了有明一代始终存在的两大严重困难,那就是(一)文武官员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军人的贬抑);(二)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
在中国历史上——尤其自晚唐及宋代以后——这两个问题始终存在,到了明朝,变得格外凸显。在明代大部分时间,它们大致以个别形式存在着,仅在几个问题上出现交叉。然而在南明,当武装能力与皇权有效统治都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它们仍纠葛不已,便对勤王事业造成了致命伤。同这类问题密切相联系的,就是久经小心培植并不容异己染指的文官优势地位。这个文官系统,在明代较诸中国历史的任何时代,都更自以为是(以及到头来自取灭亡)。
一个在“洪武”精神中建立和巩固的国家,却出人意料地很快将关注由武事别移。明朝的太祖(1368—1398年在位),依仗他在政治上的精明和在水陆作战方面的韬略,逐出了蒙古人,打败了国内敌手。在他的后裔中差堪相比的只有他的第四个儿子成祖,此人在15世纪前夕发动内战从侄儿手中夺取了帝位。但成祖选择的年号却是“永乐”。而太祖,虽然他的年号令人肃然以及他费心创造的勋贵制引人注目,却并不希望尚武精神在普通民众中植根和传播。毋宁说,他所追求的是减轻一般人的兵徭负担。这样就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祖训:军人的身份世袭,使军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的身份相区别——正当此时,中国的世袭制已在社会政治的价值观念中遭到摒弃,代之而起的是依照才能而赋予威望、身份、特权以及其他奖赏14。
明代军人组织的世袭性见于两方面:第一,普通兵士和军官都来自永久隶籍的“军人家属”(军户)。他们为了随时准备征战所需的给养装备,而耕作属于国有的所谓军垦土地(军屯),并在所驻的战略网点(卫和所)接受编制和训练。第二,那里的军事贵族(勋臣),拥有诸如公爵、侯爵和伯爵等永久性头衔,都是皇帝以其殊勋授予他们的。这些人通常担任五军都督以及京营提督一类高级职务,而且其贵族头衔(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他们的职务)世袭罔替15。在15世纪和16世纪初,军屯制与卫所制两方面,连带军事贵族身份制都令人惊异地退化了,因为文职官员,特別是兵部官员,逐步控制了军事要务。
财政措置失当所造成的偏差,外加文职官僚的漫不经心和蔑视,致使军户的生活水准和士兵的服役条件都恶化得令人吃惊。物质匮乏更加重了世袭军人身份带来的社会耻辱。私脱军籍,在役潜逃,以及虚登名册,都成常事。驻军实力下降到远低于计划标准。剩留的士兵又被经常性地安排非军事工作,譬如运输或建筑,甚至充当军官的仆役16。为了弥补世袭军屯制的缺陷,而设置的全民皆兵制度(“民兵”和“民壮”),不是由于应征乏人而无从推行,便是在各地文官的操纵下逐渐变质,很快表明其目的不在增加军额,而在于榨取额外税收17。确实,由于以征银代徭役已成为明朝户部岁入正宗,因而在1637年复行民壮制的廷议刚提出便遭驳斥,理由便在于政府经受不住随之而来的岁入减少。结果,无数的地方自保组织建立起来,以对付17世纪40年代的流寇和南进的满人,其目的都严格止于自卫,他们既没有得到来自高层的协调,也没有被利用进行地区性防御18。
当世兵和丁壮的数量都不敷所需,政府便不得不日益依靠雇佣兵(“募兵”),这项开支的不断增长,以及常规军费在16和17世纪的持续上升,致使明朝的国库和后勤部门都不堪重负19。况且,与欠饷的屯卒相比,欠饷的佣兵更加危险。屯卒通常有家可归,而佣兵则由社会上流离失所的群体中来——根弱,又多是冒险者,一旦被武装和接受军训,却不能及时给予粮饷,便视反叛与掳掠为理所当然的事,而原来招募他们却是为了保护人民。当兵变、暴乱以及其他的社会骚动愈益普遍,招募斗士也愈加容易,只要提供饷银即可。但对他们的训练和控制,却越发困难。战地指挥官不得不采用非常手段以保持兵员数量,于是有了半私有的军队。对付这批暴戾乖张、桀骜不驯的士兵,可取之方是抚慰,而不是绳以军纪。所谓明末农民军,大部分由此等社会“渣滓”构成。而当时的社会从不把做人的尊严给予普通士兵20。
于是,明朝会把那些被鄙弃的人视作一流勇士,便不足为奇。“狼兵”来自遥远的贵州某土著部落,以骁勇善战著称,也以劫掠平民而恶名昭彰21:“贼如梳,军如篦,土兵如剃!”22“狼兵”被用于有限的战役以及事毕即被遣返原地的状况,正是明朝文官与军队分离的缩影。
那些被文官们屡屡指为娇生惯养、无能和“纨绔”的军事贵族们,已成了受到鄙视的另一群异类。大多数声望卓著的勋贵世家是在王朝开端即太祖和成祖两朝建置的,但从15世纪初叶起便鲜有新的册封23,而这种体制也显得越发不合时宜。加之,勋贵们纵使永久保持由朝廷给予他们的高贵身份,他们的权势和威信却逐年下降。在这种关系上最为显著的是五军都督府和京营的演化史。两个集团本来都是袭封高级军事贵族者的禁脔,但二者渐渐变得越来越服从兵部的节制,而且勋贵职权的衰替还表现在它受宦官侵蚀上,正像被文官侵蚀那样24。重要军事职务的指派权也旁落于非贵族军人即通过考试的武举人和武进士手中。从15世纪晚期起,由兵部定期举行这种考试(像文职业务考试的略小翻版)25。
明代的军事建构的破败,常被归因于“承平日久”。情况真是如此吗?的确,明朝不像宋朝那样承受着长期的沉重压力。但它有过许多烦恼,诸如需要同时对付内部的造反者和南方的邻居缅甸和安南;北方的蒙古人始终是潜在的威胁,不时恐吓着北京。在一次“轻举妄动”中,被他的首席太监诱出举行有勇无谋亲征的皇帝,做了西蒙古酋长(瓦剌可汗——译注)的俘虏并被扣留年余,从而在明廷引发了一场巨大危机26。牟复礼注意到从这次崩溃中“中国人没有吸取应有的教训”27,这个裁决也可适用于明朝其他的军事努力28。
作为“中国的第三条边界”的防御设施29,即东南沿海的海防能力,到15世纪初以惊人的速度降低,而在明初海上力量曾大大发展,如今则完全逆转了30。当16世纪中叶倭寇(日本的海盗)的侵犯特别严重之时,海防也陷入悲惨的境地。于是招募了特别部队并建立新的指挥组织。在这场斗争中,朝中最能干的将军戚继光,再次取得制止掳掠者的成功;为此,“彼实练新军”31。由于不重视戚继光的经验,在17世纪,中央政府只能靠招安海寇,才能在沿海维持表面的和平。
“旧中国”的军事没落,使得儒家思想不是被责难,便是受揶揄。就负面而言,长袖善舞的儒家官僚学者,被指称把持要职而浪费了务实、有才干和勇敢的许多人才,因此应为国家易受夷狄侵略负责。但从正面说,他们则被誉为以文制武,并使协调技艺在较量中胜过角力技艺的群体。费正清在《中国军事经验的多样性》一文中,强调中国官员将战争看作他们应付五花八门的问题的终极手段,“诉诸武力等于承认文治的失败”,他们“高瞻远瞩地主张,尽可能不用暴力以维持秩序”;即使战争不可避免,他们仍然认为,“战争过于复杂,不能让武人擅自处理”32。
后一描述要是赋予明朝就过度慷慨了。巧匠在手头总备有一套工具,对每一件都按精细的工作程序予以关注和维护。作为安定和谐的匠人,明朝的官场在这方面很拙劣。军事力量不仅受文职衙门的管束,还被搞得失去效用。武人不仅受文官统辖,还被降了格。将士们远远没有得到共同事业中低级伙伴那样的尊重,反而受到忧虑、猜疑和厌恶之类的待遇33。正如明亡后一份揭它短处的评述所云:
唐宋以来,文武分为两途。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节制,与兵士则离而不属。是故莅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莅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势不可叛!34
如上引所示,并非所有明朝文官在军事业务方面都注定是白痴,那时的政治家对于明朝关于军事方面的一贯的态度和政策也并非全盘接受。尽管如此,飞黄腾达却主要不是依靠军功。既能驰骋于戎阵,又能揖让于庙堂,这类人委实罕见。虽说居上位者理应才兼文武,事实上官员们认同的是他们的文职身份。在明代中国不会有如同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或者黑格(Alexander Haig)的官员35,也不会有做了州长或市长还向选民炫耀以往军功的上校。这样的角色变换,在明代士大夫是不可思议的。
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应对这种右文偏向负责。但任何观念形态,除非与权势者利害攸关,都不会得到长久的反复的宣传。尽管个别大臣曾遭空前的凌辱,尤其在本朝太祖皇帝的专制年头36,但到了明中叶,文官体系也臻于全盛,士大夫们极力使他们自己变成精英中的精英。勋贵、宗室、权阉——无一幸免于来自孔夫子武库的弹药的轰击,由于他们全部缺乏科举考试必备的文学教养,因而均被认为没有领导社会的道德资格。如此排斥异己在相对承平时期也许自有作用,但在南明,当王朝已在生死之间挣扎,需要它的所有精英都最大限度团结之际,文官系统和其他社会成员——尤其和武人——的疏离,也达到无法弥合的程度。
通过某种历史的透镜,可以看到南明史上文官建构被军事建构冲击——驱除的转向过程,既痛苦又缓慢,直到结束,宫廷的唯一支柱来自并非源于明朝体制的军事组织。文武权力之间此消彼长的下一阶段,应当是远在东南的郑成功和西南的孙可望的军事组织中有文职管理出现,并已有这种趋势出现的若干征兆。然而清朝制止了那些萌芽发育的机会。
文职官僚在明代尽管势力庞大和唯我独尊,却并不坚如磐石,且在两个方面取决于强大的皇权:第一,为了它的实际存在。君主和官僚实际上是互相依存的关系,虽然他们时常激怒另一方,那却是一种“必要的张力”,是传统的中国人尊严的健全所需要的。有意义的是,明代的君主制的独裁统治和官僚垄断权二者在中国历史上都达到顶点。大臣们匍匐在明帝宝座前都带着受虐狂者的神态,但“在顿首中,自尊透过自卑凸显”。37第二,官僚体制需要一个强大的、果断的皇权来现实地行使它得自于“天”的最终权威,并借以抑制官僚体制的派系纷争。中国的政府内总存在着密布的派系,因为中国总在制度上提供条件,使那种易于转移的权力(派系权力)发荣滋长。那是政治科学的一种观测,并非讥刺38。派系是一切官僚机器的润滑剂。对于历史学家的问题应当是:在怎样的情形下日常的派系竞争会变得狠毒起来,导致自相残杀乃至导致本团体的最后自杀?在明代,官僚体制的高血压症和致命的党争,主要原因在于辅佐皇帝的难题。
我已说过皇权对于官僚是重要的,因为那种制度,在多数朝代,通常包括皇帝和他的合法代表,一二名主要大臣或者说首辅。但1380年猜疑心极强的太祖以谋叛罪名处死了他的丞相,完全废除了相权,并规定任何官员敢于建议重设此制便予处死39。这就导致在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尚书之上,只有皇帝才可处理上达国家金字塔顶端的那些复杂而大量的例行公事。太祖几乎可以独自处理,然而他的子孙们既无此能力,也无此意愿,来负荷如此重任。接着,皇帝和行政机构之间的这个裂缝,则由“非法的”或“违宪的”成分所填补,即宦官和大学士。明朝受到宦官专权的困扰甚于任何王朝。他们扮演的荒诞角色被认为是君主专制的必然产物40。但更准确些,不妨认为他们获得这种角色,是由于明代列宗在专制政体内充当专制君主(并非认为他们没有胡作非为)都不及格。大学士制度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作如是观。
甚至早在太祖时代,皇帝已从翰林院借用相当多的高级文书人员。通过每三年一次科举考试的出色俊彦,通常会进入这个帝国最高的官方学术研究院,开始他们的征程。慢慢地,这些从“翰林”出身的秘书们更频繁地成为重大决策过程的依靠。在15世纪的第二个25年里,他们已构成真正的内阁,所受加衔也已超过统治集团中其他任何成员,并且在那个世纪的第三个25年内成为推选首辅的惯常来源。大学士的职责,也从单纯地奉旨草诏,发展成不等奏疏呈送皇帝,便预拟皇帝旨意而秉笔为他代订路线指示或者作决定。早先的皇帝们惯于把那些建议看作只是建议,但后来的皇帝们则倾向于认可他们的大学士的智慧——经过首辅——并将略作改动的“票拟”直接予以批准41。于是,大学士们便获得了间接的执政和立法的权力,而内阁职位的攫取所需经过的翰林院也成了举国政治权谋的一个主要鹄的42。
然而辅佐皇帝的难题未能由此化解,因为无论大学士的职能多么必需,它依然属于模糊的惯例,很不舒服地高悬于皇帝与官僚之间,并且不被任何一方所充分信任。43
经理的助理决不可说成是助理经理。大学士据有非正式的执政权力,他们被迫忠实地服从皇帝的任性。此外,不顾他们名义上兼有部院大臣的职位,他们究属实质上的内廷成员,不能期望从外朝得到一致的支持与合作。某些大学士虽然变得强大而有势力,通常与皇帝宠幸的宦官结盟,可是他们似乎必不可免要被外朝多数官员的怨恨所挫败。难题是怎样设法在已经取消宰相的制度下成为一名宰相。44
假如首席大学士曾有祖训赋予的职责,并非是个不稳定的衍生制度,则此位置被这个或那个官僚派系所猎获,都可引出朝政趋于安定的效应,因为此派当别派居优势时,它要给予哪怕是忿忿然的承认。但由于它的公职权限最终模糊不清,它的占有者就总可以被认为在越职而受指控,特别是他们假若尝试在政府中获得坚固势力并像宰相可行的那样行使领导的时候。结果,派系斗争加剧了,因为问津内阁统治权失败的任何重要派别,都可依据成宪做理由攻击它(无论是谁都通常以道德术语来精确表达)。这个首辅位置连对最柔顺谦和的在职者都是座烤炉,而且得随时充当皇帝过失的替罪羊45。有谁试图通过那个公职向政府施加真正的影响,必受弹劾,理由不外是乘危篡取特权,或把皇帝引向堕落46。的确,它就是首席大学士张居正(1525—1582)果断的行政改革由高涨到激起“反行政机构”运动的同一理由,后者是由明末“东林”社团所领导的47。因为皇帝与官僚之间的空白领地曾由宦官和大学士来填补,所以17世纪20年代东林领袖在魏忠贤暴政下殉难,以及东林余绪复社在30年代攻击强人首辅温体仁为“阉党”,便都不足为奇48。
由于缺乏宰相制,君主的无能和派系的争执这两大古老难题,在明代越发难解了。更糟的是,它也使另一个古老难题,即中国士大夫内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二者的基本分歧,因而加剧。虽然个别人物纯属何种典型的区分颇难49,但在涉及任何治国政纲的争论中,总有这两种见解的对立。前者言辞犀利,后者应事老练。同时这种交锋也总在超越具体主张正确与否的层面,因为中国人的传统的社会政治议论大抵带有弦外之音,所以它也被看作基本观念的直接反射,譬如人的本性及由此而来的那些应有的道德功底锻炼。
考虑到本书宗旨,关于中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二者的通常分歧之一,即他们之间所横亘的如何克服人性弱点的见解鸿沟,指出下列之点便已够了。前者大致认为人人可臻于至善——至少可以很大改善——经过灵魂的或意志的悔过而达到。他们改造人的举止修养的门径是伦理的教诲和劝诫——经常如此却不必定如此,腔调是自命公允的。而后者对同事或上司做人的短处无论怎样都更倾向于容忍。他们办事顺利的捷径是对此多所迁就或有意利用——经常如此却不必定如此,腔调是冷嘲热讽的。这相反的两种观测角度用于如何辅助皇帝时便产生以下结果:依据一方,既然谁都甘愿接受皇帝血胤中那些实不可免的无力胜任者和无可救药者,那就也应甘愿承受那些或可出现的诸如首席大学士这样人物的权力增长。如此容易接受可能不完美环境的态度遭到反对,那些坚决争“国本”者以为,不管这块素材怎样不足数,他都可以教育好,引导好,从而能够由他亲手操持政府的缰络。换言之,大臣的一类喜欢相信,“要是皇帝不能管事,就给他一个能管事的人吧”;而另一类倾向于说,“皇帝必须要管事,同时我们有责任确保他能管并且管到”(当然不超过习惯和先例的限度)。
考虑到上述因素,也许就容易了解,为什么万历朝发生的问题,对明朝官僚体制的震荡那样巨大,致使它再没有恢复固有地位。在儒学复兴论者(特别是开创东林运动的那班人)看来,张居正非但在皇帝倘被启蒙便决不会赞成的情形下,傲慢无礼地僭越皇权,而且为了私利,有意隔绝皇帝与可能启迪他的那些人的接触。稍后他们便大胆地反对愚昧的皇帝本人,因为他不断稽迟正式指定他的宝座继承人——从而也贻误后者正规的(即儒学的)教养的起点。在对当朝皇帝(他统治四十七年的大部分时间拒绝会晤他的大臣)的影响已被剥夺之后,他们如今又行将丢掉下一次机会。因此,他们忧心忡忡,以为嗣续大事倘不赶紧决定,那么国家就会送给非儒门的丑类,即那些自我膨胀的宦官们或首辅们。他们不幸而言中。国家先给了小人,再给了夷狄。然而倘若“清流”的儒学复兴论者的抗议不是那样咄咄逼人,如此令稳健派敬而远之或望而却步,并且诱发了猛烈的反击,那么这两次权力丧失有可能避免或延缓。在南明,我们同样将看到那个辅佐皇帝的难题从未化解,甚至到末日仍在引发论争与宿怨。
一般定谳在晚明尚未衰亡前总述及官场的普遍腐败,以作为王朝毁灭的肇因。然而“腐败”是个笼统的字眼,要求特殊的界定和社会学的解析。(哪些行为是合乎惯例的,或者说由制度上或经济上的状况必然导致的?)在大多数案例中,它似乎更多属于某一情况的结果,而非其肇因。官员们纳取贿赂,欺骗和勒索他们的子民,长此以往,不正之风于是产生,即无视与他们人人有关的政府前途而采取不正当行径。不管国家的前途被假定为哪一种,是基业不朽还是易代在即,他们都既无认同感又无事业心。即使不能完全归咎于恶性的派系冲突,当一个群体丧失其团队精神时,这个滋殖腐败的异化心态也肯定要与日俱增,正如17世纪头四十年明朝官僚体制出现的断裂所表明的那样。况且,由于前述的原因,它被来自专制皇权的强制惩戒所阻遏的可能也微乎其微。
另外有两个难题,也是明朝特有的,在南明相关史料中均有记载:(1)遍布各地的明朝诸亲王、郡王,其中多数缺乏基本的领导能力;(2)广泛的社会不安与混乱,在1644年北京失陷和地方政府的权威与能力已到公然被质疑的程度之后,都加剧了。较诸前述难题而言,这些都是主旋律的副部,并非因为它们对理解这世纪中叶的社会政治状况较不重要。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在关于南明的这部著作中,我选定的重点领域是那个政权体制的内部难题;其实亲王郡王问题和广泛的社会不安问题,对于当时的清朝也同样是大问题。
与其他王朝不同,明朝贵族享有终身爵禄的,是太祖的所有男性后裔——大概还有他们的姑母、姊妹和女儿。只有储君被留在首都,其他的皇帝子孙举行成年礼后,便带着御赐的大规模地产(附带大量佃户和扈从),被派驻到畿外王国上去。嫡长子继承这些亲王的头衔和地产,而庶幼子和其他子孙也被分封爵衔和皇室土地,这些土地在各省多半集中于某些州府中。起初,这个制度的意向,是在国土每一隅都安插皇帝的血亲,以巩固王朝的统治。但在一系列高贵的亲王发起反对在位皇帝的叛乱之后,这个制度所具有的意义,更像是保持亲王们和重要皇族的距离,将亲王们限定在其封土之内以远离首都的一种计划。他们逐渐变得动辄都有莫大限制——例如,亲王郡王们未经皇帝许可不得擅离封土,他们本人及其随从官员也不能参与各种军政事务的管理。而且,所有皇族成员都不许从事任何职业和参加科举考试,或者在享受爵禄外做任何事情50。
明朝初期宗藩制度设置之时,没料到亲王和其他食禄皇族的人数会不断膨胀,也没料到他们的供养会成为国家岁入的严重负担,这种重负在16和17世纪达到这样的程度:据1553年的一个估计,从各省每年存留的税粮中所支付的宗藩禄廪,是岁供北京粮食的两倍。这时,食禄者总数已逾2.3万人,到万历朝晚期这个数字更超过8万人,而且政府绝对不可能像先前那样供给他们了。尽管某些亲王郡王的领地在继续增加,其他皇族的禄米却被削减与缓供,就像他们的婚配和袭封的情形那样,爵位较低的许多宗室成员因而穷困潦倒。1590年,宗室中无爵者被许可谋求诸如农工商以及想从事的各种职业;到1606年,亲王郡王以下各级宗室成员都获准可参加科举考试,按规定凡取中者总是被指定到各省担任较低职位,不得到首都做官51。虽然士大夫们普遍认同宗室成员必须从事某种职业,却并不欢迎他们一心一意地闯入文官的公务圈,而把他们看成是懒惰的、无知的和道德不可靠的。
众多的亲王郡王和宗室成员在南明时期兼具祸福二重性。一方面,无论忠于明朝的人士集合在何处,那里也就多半有个亲王郡王适合作为恢复事业的象征,或者较为罕见地担任抵抗集团的实际领袖。但由于这些亲王郡王们过去彼此从来没有联系,在国家政务上也没有任何亲身经验,他们的观察力与追随者的眼界都是狭隘的,同时他们的领导造成忠明活动出现许多不同的、常常互相竞争的中心。至于明朝的下层宗室,备受贫困和无所事事的怠倦所折磨,一旦清朝表示,他们如降服便可得到荣耀以及终身衣食无忧52,许多人便会轻易转而归顺清朝。当然,清朝也感到对付无处不在的那班明朝的亲王宗人是很大的麻烦,不管他们充当敌手,还是充当不可信赖的合作者。供养如此一批彻底的寄生者所需费用,对于清朝的负担能力来说也是沉重的,尤其是它正面临因征服战争的不时之需而财政支绌的状况。但倘若他们食言,拒不履行对明朝皇族的许诺,则后者将造成不利的政治分割状况,这一恐惧使清朝宁愿对他们实行厚待政策53。
明朝皇族的处境只是晚明时期身份制遭侵蚀的一个例证。事实上每个社会阶层都能发现传统认可的诸等级间的关系正在猛烈扭曲的证据——例如,地主和佃户,主人和仆役,雇主和佣工,士人和非士人。17世纪前半叶以如下事件的频繁与恶性地涌现而凸显于中国历史,譬如:卖身奴仆反对家主的叛变,其要求从财物和人身自由到摆脱家主的羞辱,不一而足;反对地主的抗租,则是由改易不公正的惯例的要求所煽起的;矿业、手工业和运输业的全体人员罢工,抗议政府措置失当,以及地区的或周期的经济失调;宗教的派别组织和非法的秘密会社,针对权势者的镇压而奋起抵抗;前已述及的军队叛变和大量的农村起义,大多都由官员压榨和自然灾害协同造成的饥荒所引发;还有各类盗匪——本地的或区域的,来自山泽或湖海的——把那些四分五裂的各色人等作为食料。不消说,一个王朝的没落时期同它的盛年时期相比,情形的失常总是趋于更加糟糕,更加不可弥补。但在晚明,反叛精神在社会中的那种喧嚣和弥漫,却是特异的。现代学者们倾向于把这个时代看作阶级斗争高涨的岁月,而且把注意力集中于地主—佃户、家主—奴仆之间的冲突54。但广泛的考察已表明,社会关系的崩溃,甚至出现在同一社会等级之内,例如某些家族或团体的长幼尊卑之间55。
似乎很难否认,造成明朝社会不稳定的原因,除了明朝政府统治失效,同等重要的还有前近代经济变迁的多重因素在起作用。同样难以否认,恐惧、忧郁和疑忌也弥漫于晚明社会,从而导致南明的下层组织发起抵抗运动并取得成功56。但这种状况,以及社会因而蒙受的普遍军事化,不论对于明朝还是清朝,都是极大的麻烦57。本文只想指出,17世纪40年代中间,这些社会“矛盾”发展到了如此地步,以致只有等到战争的艺术应用之后,和平的艺术才有用武之地。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在从另一方手中并从冲突中的各种武装力量手中夺得社会控制权之前,是不可能制定改善社会的政策的。征服力量最终取决于军事力量,而明朝酿成的否定身份制的危机,最严重的即在军事领域之内。
第一章 首次抵抗:弘光政权
1644年4月初,李自成叛军横扫山西北部,直捣明朝首都北京,北方局势一片混乱,险象环生,结局难以逆料。消息传到陪都南京,官员们愈益感到担心。4月12日,北京的崇祯帝征调所有能来勤王的军队开赴北京,并特别命令山东总兵刘泽清前来救援58。但是刘泽清置此命令于不顾,却向南开拔。而在长江流域的其他将领则从未接到北上的命令。反正这些人也没有准备北上。虽然前几年在南直隶的西南部曾击退过“流寇”的侵犯59,但是该地区现在除了长江和南京的驻防军外,并没有大量的常备军。而且陪都百官有理由相信,太子,甚或皇帝本人可能过不久就会前来南京,因此,长江下游的所有军队就地做好准备是十分重要的60。长江中游的洞庭、鄱阳湖区域的明军,虽然数量众多,但因张献忠部叛军刚撤出湖广省,此时他们正忙于恢复对该省的控制。而且他们毕竟离得太远了。可能有所行动的军队都在南直隶的淮河以北地区,由于受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军队的压力,此刻也已陷入混乱之中。这些部队为兵士的叛变、逃跑及怯懦所困扰,宁愿到淮河以南避难,也不愿到北京勤王61。
4月24日午夜后不久,叛军击破广宁门(今广安门)而涌进北京,翌日攻入紫禁城,崇祯帝在内廷北首的煤山投缳自尽62。但是直至5月5日,明朝的淮安巡抚才得知北京陷落的消息,而淮安城内,“闻京城失守,众疑信相半”63。
次日,消息传到南都,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史可法,立即会晤其他高级同僚,发布檄文,着手集合勤王军队。但是他们随即便不得不考虑:要把这支军队带入何种境地?南方局势不稳,北方情况亦未明朗。举例来说,他们要“勤”的“王”,究竟现在哪里?史可法渡过长江,在浦口防区着手准备迎敌,但除此之外,就无事可干了。有些人已在南方“草泽”组织义军,也被下令制止64。
南中诸大老每集议事堂,惟相向攒眉,竟日无一语。或仰视屋之罘崽,咄嗟而已。问曰:“事如不可知,将奈何?”
竞以靴尖蹴地,作叹息声,各各散走65。
5月15日,崇祯帝驾崩的确实消息传到淮安。又经三天才传到南京。这一消息使南都领袖人物大感震惊。南京的高官们意识到,必须组织新朝廷66。他们着手应付这种动荡局面之际,必须增强团结合作,和衷共济。不论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在实际意义上,都应有这样的表示。但是随后发生的却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自相残杀。在南京建立第一个南明朝廷的官员,设法使不满分子安心,尤其急于安抚军队。这原是顺理成章的事。在此危急之秋,军队实力确需增强。但是军队得寸进尺,走得太远,官僚系统和南方士人中最有威望的领导人物对此不能接受。武人要扩大权力,就须寻求支持,于是相互结党,并拉拢那些受整个官僚系统,尤其是受“正人”排挤的不满分子。急于和武人结盟的,是宗藩、宦官,还有那些因东林、复社得势而仕途受挫的官员,尤其是因十七年前魏忠贤倒台而被逐出政府并被贬为“阉党”的那些人。
这些人结合在一起,手段粗鲁,立刻引起了“清流”领袖人物的反对。于是妥协精神终止了,一场为权力与原则而战的决斗开始了。“清流”逐渐失势,甚至颇孚众望的温和派在政争中也无法立足。于是南京朝廷几乎没有了有眼光的政治家,也丧失了民众的支持。那些在这场冲突中获“胜”的人认为,他们过去受了屈,被剥夺了权力和影响力,现在终于重新获得这些了。但是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战胜者和权力一起毁掉了。受到“清流”的猛烈抨击、处于招架地位的得势一派的首领,为了固位,采取了短视的政策,其恶果连他自己到后来也无法控制。他的集团四面楚歌,草木皆兵,虽与皇帝联合在一起,也统治不下去了。传统的南明史著作集中于几个主要人物——英雄与坏蛋,殉难者与卖国贼。即将出现的篇章也会对此作一些赞扬和谴责。但是这些个人都应该放在某种政治力量造成的局势中去观察,那个局势似乎有它自己的某种动力。
选择新皇帝的时候,党争即已开始,而且势头不弱。在南方几个藩王中67,准备得最充分、和皇帝血统最近的是福王(朱由崧),他与东林党有夙仇。而且,他又落入了最有实力的武人之手。几十年前,东林党拥护万历帝的长子,不让他宠爱的郑贵妃所生之子立为太子,这位郑贵妃之子正是当今福王之父68。由此案酝酿而成的党争使官僚们时时面临动荡,持续三朝(万历[1573—1619]、泰昌[1620]、天启[1621—1627])引起激烈争执的各大案,在某种程度上以1629年东林党暂居上风而告一段落。即使这些争执对于居住在河南富饶的皇庄内的当今福王及其先父没有影响或没有关系,不同成分的官僚仍然或指望或畏惧这些事件在福王治下会重新评价69。
有鉴于此,某些骑墙意见便以为,北京陷落之前,崇祯帝的太子及两名幼子还在城内,至今生死未卜70。若是某一藩王即了位,而太子随后出现,要求登上大宝,那该怎么办?所以应暂缓立新君。又有人援引“立贤不立长”之义,主张立潞王(朱常淓)。潞王此时已自北方的王庄逃出,到了南直隶。即使一般人以为,潞王只是粗涉文学,雅好古玩,而且“指甲长可六七寸,以竹管护之”71,不过他和那位以好色、无知与不负责任著称的福王相比,还是有贤明之誉。但知道那些亲王底细的人毕竟很少,即使在高级官员中也是如此。多数人以为,选谁都没有关系。同时人们迫切希望有某位藩王立刻登上大位,以稳定南方;而在政治人物中则有一种自私的打算,即希望自己被看作那名藩王的一贯支持者,而不论那藩王是谁。于是在崇祯帝死讯传到南京数天之后,南直隶的文武要员之中就开始了幕后磋商,为官职而讨价还价,并且注意掩盖踪迹,不使马脚外露。
然而消息传来,福王已在淮上受到保护,支持他登上大位的是东南防卫所赖的北直隶将领,于是拥戴福王的看法便迅速形成一致。有两人加入这个军阀联盟比较晚,却成了它的领袖,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总兵刘泽清,另一个则是凤阳总督马士英。二人都有理由反对文官集团中的主流派,希望自己的地位因“清流”受抑制而得到加强72。在南京,一些军功贵族以及其他政治投机分子也随声附和。当百官聚集,行礼如仪,向明朝列祖列宗禀告以福王承继大位时,爆发了一场令人不堪的争斗。一些显要文臣被指为阻挠择嗣,高级勋贵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甚至拔出佩剑,向敢言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姜曰广砍去73。新朝廷建立过程的随后各个阶段,类似的文武冲突一直不断。
江北的武臣集合了一支大军,送福王沿大运河南下。6月3日,福王衣冠不整,乘船抵达南京东北一个主要码头。次日,南京的高等文臣与勋贵礼迎福王。福王自惭形秽,拒绝即皇帝位,诉说自己备受困苦,不克荷此重任74。不过到了6月5日,他已在全副朝廷仪仗簇拥之下,经过高皇帝孝陵进入了南京的皇宫。百姓站立路旁,观瞻仪式,陈列香花宝烛,心情振奋,如同节庆来临75。
但是,当福王在其守备衙门的临时住所第二次接受百官朝贺劝进时,灵璧侯汤国祚大声指责户部不发军饷,把朝仪都打断了,摄礼部尚书吕大器立即予以制止76。岂知当讨论到福王应直接即皇帝位,还是在局势明朗之前暂做监国时77,勋贵们再次咆哮起来。多数廷臣赞成监国,待逾月后再入继大统。但是刘孔昭等人要求直接即位。他们一直对主张暂缓登极的诸文臣的反对意见表示怀疑,指责这些文臣“原有二心”78。与此同时,考虑新朝廷大学士和尚书侍郎人选之事也开始了。文臣们为了安抚不知厌足的军阀,破例允许勋贵也参加通常荐举朝廷要职的廷推79。刘孔昭提名自己为大学士,使聚集庙堂的群臣大吃一惊。朝臣们告诉他,以勋臣为大学士,无前例可循,于是他提议以马士英来替代80。
6月6日,福王同意即监国位。他起先声称,只想“避难浙东”,无意入居帝位。这可能是出于真心,但是经群臣依例三次“劝进”之后,他终于同意了,在次日正式行监国礼81。仅仅半个月之后(6月19日),便即了皇帝位,以弘光为年号82。监国和即位所颁两次诏书,可说是一张一览表,列举了医治晚明社会政治的弊病,以及纾解社会各阶层人民痛苦的各种办法83。由此可知,当日的政治领袖实际上明了种种问题,并未耗费全副精神于蝇营狗苟的党争之中。但是,官僚系统内部以及政权核心其他成员之间的党争实具有瓦解性的作用,若不能予以扭转,消除各种弊病谈何容易。
由因知果,拟定新政府要员人选时,虽要尽量让“清流”居于多数,同时也得安抚其他人物。在“清流”方面,大学士为史可法、姜曰广;吏部尚书为张慎言;颇有影响力的都御史一职,则给予“清流”老前辈刘宗周;另外几个要职则入于东林与复社的同情者之手。温和派有两位大学士。一位是前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此人正直而且相当能干,在党争中设法保持超然态度;另一位是王铎,一个有文名却有不问公务记录的人。另有一些次要职位给予了不具鲜明党派色彩的人物。作为对军阀的让步,并酬劳拥立福王的“定策之功”,马士英被授予大学士之职,并兼任尚书,加太保衔。但起初他受命继续担任凤阳总督84。由于此一安排,马士英正式被授予和南京首要人物史可法(兼任兵部尚书)平起平坐的地位,同时又居于朝外。
但过了不久,史、马二人便互换了位置。这件事对弘光朝影响巨大。同时有两件事发生。首先,马士英未经许可,自凤阳调大军(1200艘船)至南京,在弘光帝登极时自至内阁。其次,南直隶江北地区各总兵,以刘泽清为首,吵嚷着要史可法亲赴前线,与他们在一起进行协调85。这个逆转的前景使南京的许多人大为震惊,有人做了激烈的公揭,将史比作受屈的昔贤人,马则为奸贼86。然而,史可法也许对于同马士英或者同这个皇帝亲密合作并不太热心,也许觉得自己是作为协调角色的最佳人选,无论如何,他愿任督师,并公开表示,为赎不能救先帝之罪,愿意效命疆场87。
若要了解南方的社会政治领导层对这一变化的负面反应,我们首先需要仔细考察一下史可法与马士英两人的背景。两人对自己的估价可能是相同的,都自视为杰出的文官,适于处理当前的紧急局面,在军事方面也有相当经验。但是两人确有不同。这一不同虽为人所夸大,在当时情形下却是极重要的,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文武之间的适当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两种看法。
史可法接近于全能政治家的典型。他生于传统中国中心地带的河南省,幼年家贫,但所受教育良好,并成为一位因反魏忠贤而殉难的东林领袖的高足。他早年在地方的、中央的政府中从业记录堪称范例。1630年,他奉命到南直隶西南部协助抵御叛军攻击,表现出色,不久便被任命负责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卫。他被誉为尽忠职守,不畏艰险,与士卒同甘苦。他驾驭武人严格而谦和,以身作则,并表示作为上司,与将士上下同心,息息相关。他反对以力服人,除非是对不可饶恕的仇敌。尤为重要的是,他视自己为协调者。他确实是孜孜不倦,一片真诚,努力调停各方冲突,在南朝无人可与之相比88。
马士英则出生于僻远的贵州省,该省位于相对落后的西南地区(他后来从该省擅自调拨了一支狼军做他的卫队)。他并无文才可以夸耀,与显赫的士大夫们亦无交往。别人称他为粗人,他就大为恼火。他在首次地方官任上,被控贪污,革除官职,发配到边疆,而后在南京等待时机,与其他官场上的失意者同病相怜。1642年,他和另一名被“清流”摈斥的人合谋,于是重获官职,任凤阳总督89。虽然他被指控纵容手下士卒劫掠90,但他却是个能干的谋略家,懂得与将军们共处并讨取欢心,在战时和平时都好像彼此不分。
士英即凤,与四镇比。及泽清、得功等来,则益尽其私佞,谨奉之。乃大治具,出女乐侑觞,命其子侍酒,跪起如子侄礼。曰广闻,谓士英:“信有此乎?”士英知情得,踧躇久之,曰:“然。奈何?凡吾所为不惮降意者,处此辈为极难耳。此辈之脸不可破也。……”曰广答曰:“……官各有礼,亦惟大道之是务也。子其大居正以服之,积至诚以动之。用亦有憬于厥志,谁则无良?……”士英则大笑,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也。91
在武人中,对文武之间恰当关系的看法也不一致。武人在战场,对以文统武的传统表示反对或不满,其原因不在于武人的桀骜不驯,而在于他们要在文武关系的格局中有应得的地位,希望文官也尽文官的责任。一旦将士们觉得,百姓和文官非但未能履行其责任,而且阻碍武人发挥其传统的作用,抗命之事便往往会发生。弘光朝的将帅大多持此一态度。但是武人中确有人想分得更多的一杯羹。世袭勋臣野心昭著,这不难理解。但是总兵刘泽清之类,情况更为复杂。
刘泽清在其早期生涯中,显示了两种矛盾的倾向:自命知书达礼,却又残忍好杀。他因残忍好杀,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而后通过武科乡试,官至总兵。他状貌儒雅,想方设法厕身文士之列,而文士们拒绝赏脸,这使他宿愿未遂,甚为伤感92。他在朝会时向皇帝说:
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曹宜束之高阁,俟臣杀贼后,取而拂拭用之,以听其受享可也。今请罢制科勿设便。93
他还要求任命一位名将为辅弼,与首辅分庭抗礼。他自然对大学士姜曰广怀有敌意(有一次皇帝称四镇为“先生”,姜极表反对)。他曾对姜曰广表示,定要杀尽东林党人,因为东林党毁了他父亲的前程94。
另一方面,他自然与马士英颇为投契。
泽清自先朝杀科臣(按:韩如愈)后,人为之寒心。至是入朝,益多侧目之。泽清心知,亦每微自解说。而士英则笑让之曰:“有此一条,燥皮之甚,胡辞让为?”闻者骇之。95
虽然马士英迎合武人,声名欠佳,实际上首先策划并让主要将领分享前所未有的治军大权的却是史可法。身为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史可法自然要迅速提出计划,整顿和加强长江下游的防卫体系,并按照北京的格局重整南京皇城的守军96。除此之外,史可法感到南直隶江北地区将士对险恶的混乱局势颇有忧虑,于是在和其他大学士作了磋商之后提议,让新受封爵的几位有力将领以其半私人的军队组成四镇,以拱卫南京的西北二边(见地图2):
(1)高杰驻徐州,管辖南直隶西北部黄河(按:当时黄河流经山东南部,在淮安西与淮河汇合)与淮河之间地区,并负责河南北部的攻守事宜。(2)刘良佐驻凤阳,管辖南直隶西部与中部淮河以南地区,并负责河南中部与南部的攻守事宜。(3)黄得功驻庐州,管辖南直隶中部长江以北地区,并负责支援北边的刘良佐和高杰(同时防备长江中游的不测之患)。(4)刘泽清驻淮安,管辖淮安府,并负责南直隶东北部和山东南部的攻守事宜(随后设立了重要的第五镇,即左良玉及其散处湖广中部的各色部队)。各镇士卒耕种荒芜田地,粮食自给;兵器、装备及其他物资,则以各镇辖区内各项税收来购买。此外,每镇规定人数为3万(左良玉则为5万),可从中央政府获得钱粮供给,每卒每年银20两。各镇若收复失地,即受其管辖;不论何人,若收复一块地方,即任为该地长官97。
这一计划使南京控制下的一半辖地实际失去了文官的监督。但是该计划原意是:由此而在长江下游北岸恢复某种程度的秩序。当时江北诸军正在互相争夺各主要城市。他们一旦得到这些城市之后,就能取得各种资源、户口以及征调物品来保护他们自己。他们同时也竞相对付顽强抵抗的城市居民。正如被特别派去消弭乱源的万元吉所说:
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在兵素少纪律,在民近更乖张,遂致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死守不容;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猝有寇至,民必至于惊窜,真今日莫大之忧也。98
最惹麻烦的是从其他混乱地区新调来的军队,还有就是大部分由原来的流寇组成的部队。但是,即使那些一段时期以来并未调动的部队,在其他军队蜂拥而入之时,也变得不安起来,从而使正常的给养方式愈来愈受到破坏。仅仅宣布成立四镇并没有立刻解决这些困难。黄得功与高杰有隙,朝廷遣使臣至得功处宣读诏书,当读到令二人和解时,得功跳起来,挥舞双臂,对使臣吼道:“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99总督、巡抚仍执掌各镇辖区内外事务,但是他们和各镇关系紧张,因为这些文官设法维持岁入、保护百姓,而在这样做的时候,要避免和各镇的公开冲突是极不容易的100。就驻节扬州以协调四镇的史可法而言,情况尤其如此。
史可法作为长江以北的统帅,第一难事是如何对付高杰。高杰原为李自成部将,因与李妻私通,两人带部队一起于1635年逃离叛军101。他的部下来自陕西,骁勇善战(李自成军之所以可怕,正由于陕西兵厉害),投入到政府一边后,作战不输于其他官军将士。但他们还是高杰的私人军队,脱不掉恣意劫掠的“流寇”坏名声。尽管如此,在史可法看来,要在北方重建明朝势力,第一得依靠高杰,因而必须使高杰脱离由他所挑起的长江流域的冲突,把他调到黄河前线。可是高杰坚持,在集中全力进行北方战役以前,一定要先进驻富饶美丽的扬州,“安顿家眷”。高杰此举,首先受到其他各镇总兵的反对,这些人都垂涎大运河上这座商业名城。其次受到扬州百姓的反对,他们封闭城门,以牙还牙,反击高杰的兵士。暴力冲突加剧,群情激愤。于是一位进士设法做调解人,却看起来像是袒护高杰。愤怒的百姓当着扬州地方官的面把他剁成了肉酱102。
史可法选择扬州作为驻节之所,部分原因在于平息纷争进行安抚。他抵达时发誓说,高杰所引起的纠纷不解决,便决不入城。高杰却把史可法下达的手令推到一边,轻蔑地问道:“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103史可法撤掉卫队,以示信任,并亲入高杰营帐,住了一个多月(一说实际是软禁),设法以身作则,感化高杰,“如石投水”。虽然不少人称颂史可法以德服人,渲染他的出面使高杰态度大大转变,但是了解内情者认为,高杰对史可法软硬兼施占了上风104。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史可法终于使包括高杰在内的各镇总兵驻守各自的防区,但他为此作出的让步使他不但在各镇总兵间,也在扬州百姓中丧失了威望和影响力105。他从未能在职权范围内充分发挥作用。他未能使四镇就范,相反却受制于四镇,往往不能把自己的人安置到需要的岗位。因此,他自己手下的一些不得志的将领,在危急关头很快投降清军,并随后在清军征服南直隶南部和江西北部的战役中担任要角,也就不足怪了106。
史可法与高杰的关系及其后果,说明了在南明始终存在并愈演愈烈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官坚持道德说教、以理服人,并以此作为驾驭武人的唯一法门。武人若是对这些说教无动于衷,那些文官就以为不能与他们共事,不是摒弃不用,就是置诸闲散;而对于导致武人跋扈的物质上和编制上的问题,则从不动手解决,更想不到在必要时可以诈欺和压力并施。在这个问题上,史可法比起他的同僚和继任者要清醒得多,但他不惜代价,谋求调和,即使劝服无效也不用强制手段。尽管高杰终被史可法感化,表现良好,然而他和其他将领所结宿怨,使他在保卫南方的重要关头,被人谋杀。史可法原来寄希望于高杰的个人人格。高杰军队瓦解了,这一希望也破灭了107。南方军事化愈是彻底,南明军队也越来越多地由宁愿“归正”而不愿降清的前叛军所组成;这时士大夫的那种领导手法因此便更加无效了。
不管史可法在何种程度上制造了他与四镇总兵之间的问题,江南士大夫还是倾向于抨击马士英。他们指责马士英,或暗中指使,或公然示例,鼓励四镇滥用权势,觊觎非分,干涉朝政。7月中旬,颇孚众望的“清流”学者兼哲人刘宗周(他寻求得到皇帝支持的保证之后,才接受都御史之职)接连抗疏言事,对马士英的批评因而大为加剧。刘宗周在上疏中指责一些勋贵、宦官以及政治投机分子,特别抨击马士英和四镇总兵,把他们称作使朝政紊乱的“小人”。他指责说,这班人自命有“定策之功”,于是四镇得以封爵,马士英赖以骄横跋扈,跻身大学士之列。他还敦促将马士英遣回凤阳,“度诸将中仍有不用命者,立以朝廷之大法处之。”108刘宗周这道奏疏得到了一位自负有言责的御史的直接支持。此人当着哗然吃惊的朝臣之面(他对朝臣说要“冒死言之”),历数马士英“十大罪”。皇帝也惊得呆住了,暂时表示考虑接受马士英的辞职109。
但是马士英实在不想辞职。恰好相反,他面临反对,却变得更为强硬,和有理由反对官僚中理想主义者的那些人更加沆瀣一气。他因此而实现了排除异己和巩固权力的短期目标。但是,他也使一些力量脱颖而出,使一些倾向得到促进。对此他无法加以控制。这些力量和倾向不久就削弱了弘光政权,加速了它的灭亡110。下面让我们逐点考察一下马士英“支持因素”的发展进程。
(一)勋贵与各镇总兵彻底政治化,勋贵蛮横要求变革制度,诸如要求经过五军都督府遴选大学士和尚书,而不是经过吏部主持的廷推;要求皇帝在有关文官任命、军事措施以及朝廷规划的所有事情上,都得和勋贵商量111。虽然这些要求没有一项被采纳,但是这班勋贵还是设法以各种消极和扰乱手法来影响文治政府。他们猛烈抨击吏部尚书张慎言,不但在口头上,而且还拔刀相向;指责张慎言只指派职务给文官,忽视了武人;还指责他任命一些他们所不喜欢的人以结成朋党112。别的一批官员争辩说,张慎言有全权任命文官,指派他认为合适的人,而勋贵则无权这样做。皇帝和史可法都敦促解决这一文武间的冲突。尽管如此,这些勋贵,尤其是诚意伯刘孔昭,依然不肯让步。刘孔昭通过他在文官集团中的一个同伙(此人觊觎吏部尚书之职),指控张慎言伙同别人反对勋贵,企图阻挠今上入继大统。不久他成功了,把张慎言赶下了台。这是“清流”方面的首次损失113。
经过了这件事,刘孔昭(在马士英同意之下)终于使皇帝正式打开了“言路”,亦即把弹劾权交给了勋贵。虽然这一授权不久即被取消114,但是武人首领,尤其是各镇总兵,开始指控朝臣,毫无顾忌地就政治问题向皇帝上疏。
黄得功犹婴视朝士,日思所以谁何者。有所噬,奏上,辄云乞付军前正法。115
但是带领向刘宗周反击的是刘泽清。他说,刘宗周劝皇上北向亲征,危及社稷,还谋夺各镇总兵新得封爵,激变军心,因此应予处死116。一个嗜血成性的军阀竟然弹劾超等清流的都御史。这事本身就使士大夫阶层瞠目结舌。皇帝告诫有关各方说:
乃文武之交争,致异同之日盛。……若水火不化,戈矛转兴,天下事不堪再坏。且视朕为何如主?!117
但正如预料,刘宗周针锋相对地说,刘泽清一举破坏了本朝所有的组织原则、法律、规章,并要求将他交付廷议。于是气氛更为紧张118。
然而武人的政治化并不总对马士英有利,尤其是长江上游最有实力的左良玉。他虽然目不识丁(行伍出身的将领多半如此),却在早年生涯中曾在某一积极的东林党人手下服务,从而深受此人人格的影响。因而他自然不喜欢马士英。马士英以牙还牙,迟迟不任命左良玉为第五镇总兵,在其他方面也不予合作,同时又避免和他理应顾忌的这个人公开决裂。而这时左良玉因年老多病,丧失了判断力,容易为周围的人所左右,也容易相信朝廷已被马士英所败坏的说法119。事实上,正是左良玉积极干预朝政的最后决定,促使了马士英的垮台。
(二)热心卷入争端的还有一些宗藩。他们攻击与马士英不和的人,以讨好马士英,从而可得到本来不可能得到的官职。他们被指控为干预中央政府的事务,不由正当途径上疏言事。但是皇帝偏袒宗人,保护他们不受进一步的批评,因为他们毕竟是他的“同宗”。1644年10月,大学士姜曰广去职(在和马士英激烈争吵之后)——这是“清流”方面的第二次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宗藩朱统对姜曰广的攻击120。
(三)不过,最具爆炸性的是马士英重新起用逆党官员的策略。其中大启争端之门的第一起最受非议之事,是马士英推荐列名“阉党”、最受复社憎恨的阮大铖。马、阮二人已结合多年,开始是在1630年代中期。当时二人同在南京,困苦失职。随后,虽然阮大铖本人因在崇祯朝初期列入“逆案”而未能重入政府,却设法使马士英官复原职,当上了凤阳总督。马士英于是对他感恩戴德。而且阮大铖素有军事韬略,还有“任侠”之风,因此马士英便推荐他优于将略121。
阮大铖确实喜欢把游侠剑客聚集在身旁,招摇得很。这刺激了在南京的复社人物。他们于1638年发布《南都防乱公揭》122,在政治清算之外还使阮大铖不容于社会。这加强了阮大铖有朝一日要对这些迫害他的人施加报复的决心。复社活跃分子对阮大铖仇恨之深,是不易解释清楚的。阮大铖在专权宦官魏忠贤得势时与权势人物的关系,既非与众不同,也不炫人眼目,不足以解释清流党人后来对他的辱骂。大体上说,清流人物似乎觉察到,阮大铖咄咄逼人,急于求官,加上为人老谋深算,自私而记仇,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人物。弘光朝诸事件证实了确有理由为此担心;但是阮大铖所受清流党人刺激之深、羞辱之烈,也使他变本加厉。
(阮大铖)譬如困猛虎于井中,环而攻之者,不遗余力。
一旦跳跃而出,有不遭其搏噬者,几人哉123!
马士英最初荐举阮大铖任兵部侍郎是在7月9日。此举所引起的愤怒使他大吃一惊。那位政治上天真的皇帝对此感到莫名其妙,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任命一个人会引起如此纷扰。反对者坚持,这样重要的职位应由廷推决定。马士英因此暂时受挫,因为他不愿采用廷推方式。御史们还击鼓反对违背先帝遗愿,重翻逆案,再度起用阮大铖之流人物124。但是马士英等待时机,于9月下旬重提此事。这次由皇帝的“中旨”批阮大铖任兵部侍郎125。这种绕过九卿会议廷推惯例的方式,曾是极大争端,导致了天启、崇祯二朝的党祸126,而在马士英怂恿下,当今皇上却拒绝废止以“中旨”任官,拒绝禁锢从前列名逆党之人。于是刘宗周辞职——这是“清流”方面又一重大损失。不仅如此,机敏的稳健人物高弘图也在11月初辞去大学士之职。他的去职使马士英得以为所欲为127。
马士英并没有立即清除朝中其他人。但是与“清流”有联系的人物不是厌恶马士英,就是受到他的攻击。这些人都逐渐去职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逆党”的人,与复社有隙的人,以及为个人私利投向马士英的变节分子128。到了1646年春初,朝廷已被所谓马阮集团完全控制了。
如果这是彻底的政治大换班,那么,因领导层变得清一色,朝廷或许会更有效率。但实际远非如此。首先,朋党之争使朝廷要做的事,从最象征性的到最事务性的,全都彻底染上了党派色彩。例如:对于在明朝受冤屈的人(尤其是和南都有关系的那些人),朝廷作了多次表彰,以安慰其亡灵129。这不久成了公开的竞赛,看哪一党能为其死者议复、请谥,同时使对立派的死者被追谪、被夺谥130。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北都百官。他们自然而然地受到怀疑:曾帮助叛军接管北京,至少是不加抵抗。反对那些与叛军合作者的情绪普遍强烈131。于是对这些人采取“强硬路线”成了一种保持同仇敌忾气氛的手段,以期有助于北都的恢复。另一方面,弘光政权需要有能力官员的支持,不论这些人在何方。史可法曾冷静地提醒人们,对崇祯帝殉难负有罪责的不仅是偶然身陷北京的那些人132。而且当时消息传来,不少人已在北京转而为满洲效力。因此,明智的办法应是:对叛迹昭彰者宣布严惩,而对大多数则开启自新之路133。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作出个案处理(通常缺乏确凿证据),虽在平时也相当困难。在党争之际,事情更大为扭曲了。许多人在北都的所作所为,无可宽恕,但是到了南都,却平安无事;其中有些人甚至在政府中重新任职。而当局对另一些人,则予以无情的迫害,株连其家人、亲戚、朋友134。这种乖张的态度,使人们切齿于弘光政权更甚于痛恨叛军,而对于遏阻与清朝合作之风,则毫无效果。
此外,马阮一党的兴起,使复仇之风趋于极端。马士英和武臣领袖对这种风气并没有完全宽纵。其实“马阮”一词也不确切,因为自从马士英使阮大铖任职之后,二人在事实上并未紧密合作。相反,马士英发现,必须制止阮大铖的清算计划,甚至必须制止阮大铖与自己争权的野心。于是两人之间产生了敌意135。
除阮大铖之外,大学士蔡奕琛、吏部尚书张捷、都御史杨维垣之流,追究真的或假想的敌人的行径,到了愚不可及的地步。他们为了固位,大量授人官职,而得官者的主要资格则是有能力纳“资”136。尤其是杨维垣,在满朝文武秩序都在崩解的情形下,如得狂疾,坚持重颁《三朝要典》(此书是反东林的“白皮书”,在魏忠贤授意下初颁于1626年)137。于是马士英当然被认为应替这伙人的行为负责:
如士英者本无意于误社禝,而社稷虚;本无心于敛贿赂,而路门大启;本无心于剪清流,而清流尽逐,……谓非天下罪人,安可得哉?138
(四)弘光朝宦官情形与明代一般宦官状况亦无不同:官僚系统内各派领袖都设法和宦官首领结盟。外朝政治于是和内廷宦官结下了不解之缘。宦官势力与皇帝及大学士有力与否成反比例,此消彼长139。
南京司礼太监韩赞周,长期以来与阮大铖相得甚欢。1644年,北京陷落,太监们逃到南京。据说也是阮大铖特别出力,做了他们的东道主,阮大铖的目的是利用这些人以及韩赞周在南都皇上前为自己美言几句,并向这些人传授党争之事140。但是长期任司礼监的韩赞周通情达礼,处事有方,并“知本分”,更受“清流”中人的青睐。不久,他和皇帝自己的宦臣之间便有了裂痕。皇帝还在河南当藩王时,这些宦官就跟随他。他们对朝廷典章一无所知,而且还怂恿皇帝沉缅酒色,纵情歌舞。韩赞周终于因此而辞职141。
更坏的是不顾多数官员的反对而恢复东厂。这是内廷的宦官机构,类似秘密警察,可以不由正常司法渠道监禁、审讯、拷打官员142。弘光一朝,各种政治迫害愈演愈烈。恢复东厂这一可怖可恨的机构只是其前奏。马士英或许欢迎宦官把皇帝的注意力从朝政上移开,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他同意宦官扩张权力,干预审讯之事。
(五)朱由崧做皇帝是错误的时刻、错误的地点的错误人选。他对于入承大统,曾颇费踌躇,自有其充分的理由。他锦衣玉食,一直被严禁过问国事。那个时代所需要的元首应是性格坚强、遇事果断、通晓国政。这些长处他却一无所有。不过,他既然被他人的野心推到了国家机器的顶端,在即位的头几个月内却也尽力履行皇帝职责,坦率承认需要能干的大学士对他作指导与协助。与一般看法相反,马士英起初并不受宠幸。姜曰广以及皇帝最喜欢的高弘图因政争而被逐之后,这名皇帝像孩子一般,感到恐惧和绝望;他所以依赖马士英,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143。当马士英受到刘宗周和御史黄澍二人的弹劾而请求辞职时,曾上密疏给皇帝:
“上之得位,由臣及四镇力。其余诸臣皆意戴潞藩。今日弹臣去,明日且拥立潞藩矣。”上信其言,为雨泣久之。以后一切朝事,俱委士英;惟狂走宫苑中如失心状144。
马士英颇知利用皇帝孤立无助、无能为力而岌岌不安的心理。当“清流”人物鼓励皇帝乾纲独断,以睿知辨别贤奸,北上亲征以鼓舞百姓,并在其他方面做帝王表率时,皇帝的这种心理愈益加深。马士英于是“密陈国本大计”:
圣心安而后庶务举,根本定而后敌忾振。
马士英由此认定,首要之事在于安圣心,他采取如下途径:(1)从河南救出太后(皇帝继母);(2)皇帝本生父为叛军所杀,应追上尊号;(3)将皇帝本生父遗骸移至南京,妥善安葬;(4)选淑女以充后宫妃嫔;(5)对其他亲王的活动与交往严加控制145。
马士英为获取皇帝信任而筹划的短期目标确实不错。但是他并无必要讨好皇帝,也无必要煞费心机使皇帝相信东林与复社的坏处。同这位万历帝的裔孙在一起,只要等待就够了,而且也不必等得太久。这位皇帝对于明朝的制度、朝章以及官僚体系内的党争情势知之甚少。这种无知一直使他感到困惑和沮丧,因为他感到,大臣们不是对他失望,就是对他欺瞒。他秉性优柔寡断,现在突然被要求对一切重大问题作出决定,这使他深感痛苦:他只是被人有礼貌地告知,有些决定因与先例违背而不能作。人人希望他能解决朝臣之间的狺狺争执,但是他对此颜赧气结,束手无策。至于以前谁拥戴他父亲入继大统,谁反对入继;还有现在谁支持、谁反对他本人登极,他气量宽宏,或不予注意。但是现在这些问题一再提出,使他甚感不快;却也没有坚强的意志去制止争端。这些刺激,加上“清流”人物的道德训诫,只能使他迫不及待地躲进深宫146。
到了仲秋,弘光帝便与外朝隔绝,对那班朝臣浊乱国是,概不与闻147。朝仪不是被取消,就是由大臣代为主持。虽然有关他沉湎女色的传闻不可尽信148,他似乎在这年冬天和来年春天,确实全神贯注于选女充后宫,筹划大婚典礼,与宦官、伶人作长夜之饮149。在南京、杭州广搜淑女的轻率行径引起了民间的极大苦难150;内廷的挥霍无度以及大婚使国库空虚151;皇帝一度因纵欲过度而虚脱,几乎丧生152。后来,当清兵离南京只有几天路程时,这位皇帝对于迫在眉睫之事,半是懵然,半是拒闻。这当然对马士英有利,因为他可以大权独揽。但是皇帝如此放弃责任,使民众对马士英集团的支持逐渐减退,最终完全丧失。在通晓大学士制度史的“清流”人物看来,这是悲剧的最后一幕。
1645年春,在前述党争中占上风的政治联盟陷于孤立,却对朝内政敌仍作困兽之斗。这种困兽之斗,加上民众的激动不靖,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三疑案”中表露无遗。每个疑案本来都可依据明智尽快妥善予以解决,但结果却导致了弘光集团内部的最终瓦解。因为这些疑案迟迟未予解决,首先使党争各方得以据此来损害对方,困扰对方;其次,谁能给这个不得人心的集团制造麻烦,谁就受到公众的拥戴(愈引人注目,愈浪漫,就愈好)。对于明显的证据,则几乎无人给予注意。历史记载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件疑案是1月12日在南京逮捕的一个法名大悲的和尚。此人被控自称崇祯帝附体。随即对他作了秘密审讯。据官府记载,大悲先如中风状,自称某亲王,继而又称另一亲王,“状类风颠,言同梦呓”。该记载说,所有这些自称显为诈语。但是另有人以为,此人所知有关福王之事,当权者不愿公之于众。无论如何,不管大悲真是狂人还是装疯售奸,刑部尚书以及其他办理此案的官员仍然尽量使此案悄悄地从速了结。但是阮大铖希望利用此案。他开列了一张以“十八罗汉”为首的143人的黑名单,称这些人试图拥戴潞王,怂恿大悲倾覆朝廷。不过,在这件事上他为马士英所阻止,案件便以3月27日“妖僧”公开处决而告终153。
就在同一天,南明朝廷的噩梦真的出现了。有人启奏皇帝,在浙江发现了一个年轻人,自称崇祯帝的太子。弘光朝自建立以来,或将谣传的太子死讯作为真相而予以公布,或是追尊太子谥号,一直设法消除太子还在人间的印象154,但是民间还是认为太子尚在人世。因此,这位年轻人刚被带到南京时颇受礼遇。随后对他作了几次审讯,先由官员作公开审讯,而后在臭名昭著的锦衣卫监管下审讯。在太子理当认识的人中间,这个年轻人也认识几名,还有几名却不认识;关于太子的经历,他对几个问题回答正确,而另外几个却不然。虽然每次审讯都有几位官员宣称已成定谳,但是还是有人不满意。熟悉太子体貌特点的宦官应该可以作证,却看来从未要他们这样做。最有权过问审讯过程的人不久便宣称,这个年轻人供认名叫王之明,系某驸马侄孙。但是其他人说,这供认是捏造的,那个年轻人虽受尽凌辱,却始终坚称是真太子。
无论如何,皇帝在其近臣的压力之下,接受了假冒太子这一定案,尽管他先前曾对太子出现表示欢迎。有谣传说,太子受到朝中歹人的诽谤和虐待。前线各总兵得知后,大为震惊,上疏皇帝。皇帝在批答中一再表示,相信太子是假冒的。据称有三个人唆使“王之明”假冒太子。于是把这三人拿来严刑拷问,试图发现反对朝廷者的大阴谋。这样一来,谣言更甚155。
还有一件事,使真太子命运这一历史问题更形复杂,也使当时人心更为困惑。那就是,三个月之前,北方也出现了一个人,自称崇祯太子;而清廷对此案的处理,也和南明疑案一样微妙莫测,充满政治玄机。满洲朝廷最终把北方那个自称太子的人杀了156;但是南方内部更为不稳定,不能照此办理。尽管并无坚强证据,南方一般人还是认为,这个“假太子”是真的。这种看法不仅普遍,还常常颇为狂热。南明朝廷害怕某些总兵或是南京百姓举行暴乱,因此不敢把已经“证实”假冒太子的人处死;不少“清流”中人,虽然未必相信这是真太子,却也乐于见到此人不死,成为“逆党”方面的肉中刺。
甚至在假太子一案正在审理之时,自称弘光帝旧妃的童氏,从河南被护送到南京。不料到了南京,这位童氏被直接带到刑部狱,因为皇帝曾怒气冲冲,直言无忌地宣布,童氏所言是假,并拒绝再听取此案报告,甚至连马士英的话也听不进去。虽然有记载说,有关她和福王从前的关系,童氏所写所说,颇为动人;但另有记载说,她不久转而宣称,她的夫婿不是福王,而是周王,她误信周王已在南京登极。不管怎样,这位“假王妃”受尽虐待,被诬与谋害朝廷的人有不正当关系,因而瘐毙狱中。皇帝对这位童氏的冷漠无情,使他更不得人心,甚至激起了这样的怀疑:他本人也是假冒的157。
1644至1645年间,上述所有的一切以及其他事态愈趋恶化,部分原因是形势不允许弘光政权制定明确的战略目标以对付北方。这个政权在发动收复中原之战以前,确实需要时间来组织和建立起它的力量。如果这些时间用于实现明确的目标,用于应付人人易见的单一威胁,那么团结可能形成,并保持下去,也不会有那么多无谓的白费时间之事。但是这一年的时间不是用于积极的准备,而是被动的等待,等待北方局势澄清,而后南方可针对确切目标以使用其力量。这种不确定状态对武臣、文官系统、皇帝以及民众都产生了有害的心理影响,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是毁灭性的。
弘光政权在其成立的第一个月之内,十分迅速地把陪都及其主要由闲职官员组成的政府骨架,变成了像明朝初元那样的国家神经中枢158。新政权必须重建北京政府的全部机构,包括禁卫系统;调整漕运,使钱粮解往南方;重新安排行政区划;重建或整修旧皇宫内废弃不用的殿堂、庙宇、寝宫159。考虑到当时的混乱情形,所有这一切可说都完成得十分迅速。附近的高皇帝陵寝意义重大,使人对明朝的成就和基本制度重新产生自豪感。
但是这个重建的政府以谁为敌?北方的叛军在做什么,计划做什么?辽东军队在吴三桂统领下是否采取了行动?要是有所行动,满洲人的反应如何?四川叛军首领张献忠情形又如何?他要留在四川还是想再度侵入长江流域?号召立即讨伐叛军、恢复北京九鼎的那些人,大多是毫无军事经验的“清流”党中文臣160。但是向叛军复仇的热忱并不限于“清流”,主张谨慎和渐进(通常被讥为“偏安”)的也不限于“逆党”分子。1644年5月,史可法要求,一俟军队组成,立即“勤王”;但是到了6月,他的看法更为谨慎,他主张,四镇应先在各自辖区站稳脚跟,以便在适当时机规划全面进取。多数文臣持有相同的看法161。各镇总兵显然愿意作长期规划。例如刘泽清就认为,南方军队做好准备,需要一二年时间162。
文官和武将都提出过一厢情愿的解决办法,不过颇有不同。文官们主张“打出旗号”,以为一旦激起北方人民的忠义之气,恢复便易如反掌。而武臣主张“给予诱饵”,认为那些主要的投敌将领,只要饵之以利、诱之以爵,便会投顺明朝163。他们都忽视了虽困难却无可避免的组织问题。只有文武之间通力合作,这些组织问题才能解决。
然而总的说来,在弘光朝最初几个月内,仇恨主要针对李自成统领下的北方叛军。崇祯帝之死、北京皇宫之受污辱、南明朝廷之当前困境,毕竟都应由那些叛军任其咎。进逼淮河流域各地的,是大顺政权的军队。他们最初给予的威胁远比满洲人的威胁要明显164。即使在南京得知李自成已被吴三桂击败并被赶回陕西以及后来北京和北直隶大部被满洲人占领以后,情况依然如此。满洲人的宣传开始于6月初(一个月后南京方面才知道),明白表示了要统治中国本土165。但是马士英以及其他南方领袖从未认真考虑过,满洲人确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们还是抱着数百年来有关“北虏”、“夷狄”的老想法:这些人愚昧无知,却在其内心深处“知礼”,认为应当臣服中国;因此,他们信誓旦旦地说,要惩罚叛军对大明犯下的滔天之罪,或许是出于真心;即使不是出于真心,也可进行安抚或收买;即使安抚收买无效,满洲人及其战马决不会喜欢江南水乡,因而他们不久就会无意进犯而离去。无论如何,南明需要时间,因此可取之道是,不管是叛军还是满洲,暂时都不要与之开仗,让他们自相残杀,然后对付削弱的一方,以收渔翁之利166。
下一个问题是:满洲人和叛军是否会互相残杀?其中一方是否会率先进攻南方?两方是否会联合进攻南方?清军是否会进攻李自成军,把他们赶到长江流域?由于这种种不确定因素,还有中国的政治地理,弘光政权必须防守通往江南(按:1667年以前,“江南”为省名,即明朝的南直隶省。尔后该省分为今江苏、浙江二省)的五条通道,因而感到进退维艰。满洲人可能:(1)经由山东南部,沿大运河两岸夹道而下,进攻徐州、宿迁或淮安;(2)经由北直隶南端狭长地带以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攻击洛阳、开封、归德。李自成军则可能:(3)越过河南中部,进入淮上洪泽湖区域;(4)直接南犯,过淮河入湖广北部,进攻武昌。而张献忠可能:(5)重沿长江而下,过荆州,进入洞庭湖区域167。就南明而言,要在情报不足的情况下安排轻重缓急,并以有限资源制订一切应变计划,确是一件棘手的事。最后,南京面临的是敌人同时攻击山东、河南和湖广。它遭到的惨败,当然和轻重缓急安排不当有关;但是,在上述以及其他困难形势之下,南明的防御失败可能到头来在所难免。
满洲人首次对南方的晓谕公布之后,南京的一些官员开始认为,应与满洲通款。于是计划遣使,声称其目的为:(1)使崇祯帝与其他宗藩得以妥善安葬;(2)予吴三桂封爵铁券等;(3)因满洲有逐叛军出北都之功,谢以金帛(即赔款);(4)给满洲山海关外悉数土地及岁币10万两,以诱使其撤退168。
但是一直拖到夏末秋初,才得以遣使成行;部分原因是,要找到愿意出使的人殊为不易。这时,清军已在山东南部取代了大顺军,对淮河以北诸城镇日益构成威胁,而且南明也知道吴三桂确已投清,于是越发担心,假若不能以武力制止满洲的攻势,假若不派遣使臣去确认满洲地位,那么,满洲人将更有讨价还价的本钱,日后对付他们将更为困难169。
于是数次敦促业已选定的三位使臣当即出发。这三人是奇怪的组合:前科臣左懋第为复社成员,其母最近死于天津。他志愿服丧出使,以便沿途克尽孝思。他对满洲人的态度至为傲慢,视满洲为臣属,以为决不能与11世纪时宋辽关系相提并论。他似乎一心要以身殉职,而不是要完成使命170。而且他也反对前职方司员外马绍愉为使臣,认为马绍愉在崇祯朝与满洲人讲和时私下与满人交好171。武臣使节是前总兵陈洪范,为刘泽清与高杰所举荐,而清朝亦想借助他为说客来劝降南方将领。左懋第与此人也不能相得172。
8月22日,使臣们迟迟疑疑地出发了。供给和运输颇有问题(河道上空荡荡的,役夫早已逃散),在明朝控制的淮安和清朝控制的济宁之间的无人地带,又碰上了盗贼,因此,使臣们沿大运河慢吞吞北上,直到10月5日才抵达济宁。他们在清朝地界,所受款待极差,既乏供应,又受诸多限制。愈近北京,限制愈多。清朝将这些使臣视为属国上贡之臣,而不是对等的使节。最后,他们实际上成了鸿胪寺的囚虏,想会见吴三桂,也不蒙准许,满洲大学士刚林两次接见了他们,严厉训斥这些使臣以及南明政府的拖沓作风,没收了他们所携带的礼物,并不准他们祭奠崇祯帝,更不用说重新安葬了。而且刚林直截了当地说,清军已向南方进攻,和议已无意义。11月25日,使臣们终于获准离开北京,但不久清朝派人追执了左懋第和马绍愉。陈洪范这时肯定已与清朝勾结,因而被允许南归,或许还负有秘密使命。12月底,他回到南明地界;1645年1月中旬,向朝廷作了奏报173。
整整半年时间就这样浪费了,空等出使结果,一无所获。在此期间,清朝则大大增强了在山东南部的兵力,并向南直隶北部各要地进逼174。史可法这时正尽力从清军手中夺回宿迁等地,得知左懋第和议不成,立即慷慨上疏,吁请朝廷不可再麻木不仁。他警告说,满洲人正在南下,而朝廷还是“文恬武嬉”;还说,淮河全不设防,更遑论向陕西的李自成军进逼了,朝廷举措如此,宜为敌人所笑,若不立即集中全力以御清,仍是无所事事,必将受害。“人心犹可鼓,天意犹可回”175。但是马士英依然以为满洲人侧面受李自成军掣肘,而且无论如何,从历史上看,像满洲人那样来自东北边远地区的民族(如女真金人),其军力不会持久,容易进行遏阻176。
面对北方的这种等待和迟疑不决,其后果之一,就是让武人得便集中精力自相残杀,干预朝政。江北、湖广各镇总兵的例证已如上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军队不那么集中的全国经济最发达区域,即江南的苏松与浙北的三角地带。冲突不仅发生在兵士与市民之间以及来自各地的正规部队之间,也发生在正规军与民丁民兵之间。在南明政权后期,这一问题愈趋严重。更由于南直隶南部与浙江中部是东林与复社的积极活动之区,这些冲突极易成为政治问题。最后,弘光政权中的马阮集团总是怀疑,他们的政敌对于这些地区的军事活动,不是幕后支持,就是准备予以操纵,从而试图威胁朝廷,乃至接管朝政。
下面是朋党之争影响军事的一个绝好例证。在浙江东阳县一位名叫许都的金华府学生组织了一支义军。此人以热衷军事闻名,他的活动和地方官发生了冲突,于是在1644年初被处死177。北京陷落之后,许都部下继续组织同类义军,他们无疑是受到了浙江重要“忠义”领袖的鼓励。这些人要求观望逡巡的地方官也组织义军178。于是在1644年9月,以前负责处理许都义军事件的复社领袖左光先受到弹劾,被指控试图掩盖事实真相。左光先此时已是浙江巡抚,因此免职,最后被逮入狱179。
对当前南都防御影响更严重的,是发生在镇江和京口的诸多问题。镇江是大运河由南往北注入长江之处,而附近的京口则是防守运河水闸的驻军所在地。这一地区是从下游渡长江的要冲,也是防卫或进攻南京的必争之地。该地明军首先要阻止江北将领,尤其是高杰,从瓜洲渡江,在富庶的江南取得立足点。其次,有两支军队在该地交哄。一支由史可法调来,颇不得民心。另一支由浙江移驻,稍具社会责任感。更次,从闽浙二地调到京口的水师和当地船夫也发生了冲突180。弘光政权中马阮集团对这后二种冲突尤感恐惧。他们担心,这些从浙江,甚至从福建调来的军队,可能是“清流”图谋推翻自己的计划的一部分181。于是刘宗周弟子、巡抚祁彪佳被迫去职,因为他的辖区包括镇江。防守镇江之责因此落入了马阮集团成员之手。这些人因艺术名世,而不是以战绩著称182。因此,当1645年夏,清兵大举渡江,镇江防御一触即溃,也就毫不足怪了。
一般百姓也与武人一样,没有外敌当前之感,而把怒气发泄到内敌身上。他们对于有投顺叛军嫌疑的人及其家属财产,不但在口头上,也在行动上,施加攻击。这些攻击,可能有一大部分确是出于爱国义愤,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指控他人通敌,可能只是一个借口,以便于清算旧账,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夺取任人宰割的流人的财物,乃至赤裸裸的劫掠。朝廷虽曾颁布禁令,不准以“勤王”为名组织武装团伙,交哄互斗,但是各种事件还是层出不穷,遍及整个南直隶南部183。
在南京,并无紧迫之感,群趋奔竞,追求封官晋爵,连最无实权的官衔都有人争夺,因为随之而来的是特权。风雨飘摇的弘光政权力求获得支持,讨好每一个人。于是一心向上爬的人有了可乘之机。最先对此混乱局面大声疾呼的,恰恰是带头反对社会中坚力量的那些人,即勋贵与宗藩。他们惊呼,伪造证据来冒充他们爵位的人太多,有损官爵的尊严,破坏了有关服饰以及禁止奢侈的法令;这些作伪者还利用业已提高的地位来谋取官职,以求一逞,向别人报复。“宗室满街走”的怨言使朝廷颁布禁令,宗室不得求官,甚至不得入南京。将军以下的武官则不准坐轿,只可乘马;不过此禁令并不起作用184。这是朝廷需要“破格”的时候,即不拘于惯常标准,权宜进用才略之士,以应付危难局面。但是这一看法反被人利用,把次要官职滥授给大批平庸之辈。朝廷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求制止此一趋势,觅取有用之才,派到受敌威胁的地区,但是鲜有效果185。于是大家忧心忡忡,谋求自保。而且江南充满着从北方的家中或是任上逃难出来的官员,他们不惜代价,设法取得新职或保持旧衔,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机会挪用公款,领取一份微薄俸禄,得到社会尊重,略有人身安全的保障。情况正如民谣所说:
中书随地有,翰林满街走。
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
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
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186。
以贿得官是如此公然无忌,简直人人趋而行之。情况坏到如此,更是因为政府仿照先例(以前陷于困境的中国政府颇多此例),出卖官衔、科名,从官员和拥有科名者那里获取大小不等的报酬,以此手段来增加岁入187。南京户部从未大规模清理过财政。在晚明,户部岁入,包括白银和实物,只有大约140万两;1643—1644年间,更是严重亏空188。尽管现在弘光朝作了调整,想使南京取代北京,成为帝国的财政中心,但是无法使收支平衡。1644—1645年冬春之际,朝廷观望,军队“坐食”,情况更为恶化。
长江下游确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但是必得依赖其他地区。明朝后半叶,江南经济的商业化尤为迅速。商业化的结果,是愈来愈多的土地用于手工业所需的作物以及特种作物,而不是种植基本谷物稻米。于是江南严重依赖其他地区,尤其是湖广,以为大宗稻米的来源;依赖地区之间,尤其是南北之间的自由贸易往来,以为生计189。而现在,维持江南经济健康的这两大运输通道都已切断。长江和大运河都已成了防御区域,所有的商船不是常常停运,就是因军事目的而易被征用。这种情况,使重要的盐贸易以及其他商品交易大受阻碍。湖广也受到了叛军的破坏,连供养左良玉大军都不够,更不用说输出粮食到江南了。江南取得重要地位的首要原因,是从南方输出货物到北京以及其他北方城市,而现在已无此可能190。此外,虽然江南经济繁荣,税收异乎寻常的高,因而成了全国政府的财政支柱,但是长久以来,因地理和政治的原因,江南地区的征税一向特别困难,以逋欠而闻名191。现在,由于形势不定,地方官和纳税者都想迟纳税银。他们都像大旱之望云霓。这话虽带嘲讽,却是实情,因为1644年这一年,除其他灾祸之外,江南遇到了持续的大旱,从6月到12月,未见滴雨。这不仅累及收成,也使水道变浅,贸易更为受阻192。
这些经济和财政问题,随时光流逝,自然更趋恶化。弘光政权对收支的估计表明,它对收入的预期不幸过高,对支出的预期则太低。史可法原来希望,朝廷若能在其他方面撙节,可以维持每年600余万两的军费开支,但是工科给事中李清的看法要来得悲观:岁入最多不超出600万两,而支出仅军费一项,就不少于700万两。事实是,亏空甚至比李清预料的还要严重193。首先,军队因谋生无路者的投入而人数大增;他们缺乏粮饷,不是挨饿,就是反叛。同时,朝臣对皇帝的挥霍无度也不能加以限制194。
朝廷以各种方法增加岁入,虽于国库有补,却削弱了政府的力量,得不偿失。除了出卖官职、科名、爵位之外,还可纳银免科举考试,免某几种刑罚。并新设和增加了多种杂税,征收对象包括国内和对外贸易、酒类、渔产品、珍珠、盐、沿岸芦苇等195。朝廷不顾群臣反对,派遣宦官“催”解各项税银至南京;尤其是“金花银”,直接流入了皇帝的内库196。弘光朝建立之初,万历至崇祯各朝为应付叛军及满洲人而征收的额外税收,一概取消;为争取民心,部分受叛乱之害地区的税收,亦大量予以蠲免。但在弘光政权治下的地区,这一政策先是逐渐不予推行,继而是适得其反197。朝廷还听任各镇总兵自便,榨取各自辖区的脂膏,极大地扰乱了这些地区人民的生计198。另有一些人,利用这种财政把戏与混乱局面以谋取非法的私利,或是在衙门桌下悄悄获得,或是在诚惶诚恐的百姓家门口吵吵闹闹地攫取。
所有这一切,使弘光政权迅速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人民于是极易相信有关马、阮以及弘光帝的种种邪僻放荡的传闻。更有甚者,朝廷不仅完全放弃了对各镇总兵的财务和行政控制,而且不得不背弃承诺,不向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钱粮,于是引起将士的普遍不满。这些因素,加上害怕李自成军会从陕西南部袭击武昌,终于激起了左良玉军的叛变。
左良玉的部下使他相信,应当发动一场“东征”,以“清君侧”。于是在1645年4月,左军自九江沿江而下,一路上横冲直撞,烧杀掳掠,直到荻港附近才被挡住199。由于这场兵变,在清军逼近淮河之际,马士英把军队调往西边。因此要阻止清军挺进,可能性是更小了200。
第二章 首次失败:清朝征服长江流域
这一阶段,清朝领袖面临的战略问题,与明朝领袖所面临的适成对照,即李自成军能做什么,会做什么?南明朝廷是否怀抱敌意,会采取何种行动?双方所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虽然1644年初,满洲摄政王多尔衮曾试图在与李自成接触中讨论组成反明联盟之事201,但是现在满洲人的形象是拯救大明子民、为崇祯帝向流寇复仇,加强这一形象明显地对他们有利。但是南京至少必须表示决心,要收复北方;而清朝对于是否要征服南方,起初似乎游移不定。
自17世纪初叶以来,满洲人显然抱有占领中原地区的愿望,也就是想进入山海关以内202。到了1643—1644年间,当李自成在陕西、山西二省展开军事行动时,满洲人对于李自成的胜利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机会,心中一清二楚。北京陷落18天以后,清朝便确实授予多尔衮全权,以进取“中原”(按:指黄河以北地区);不过,这时下距接到吴三桂的合作建议还有7天。当时清廷臣下的其他建议,也提到“河北”、“中原”,或笼统而言“内地”203。吴三桂请求援助,随后在压力之下愿意与清廷结盟,实在是清廷的一大收获。就吴三桂而言,压倒一切的愿望是击败叛军,因为他们不但杀死了他的“君父”,还将他父亲严刑拷打,并加以杀害。由于吴三桂此举,在5月27日李自成军大败于山海关仅数天之后,清军便把李自成及其主力部队逐出北京及北直隶204。
6月6日(恰巧是福王在南京同意监国之日),摄政王多尔衮乘御辇,拥卤簿,进入了北京。惊慌失措而又精疲力尽的明朝在京官员所准备的御辇,原来是迎候明朝太子的。多尔衮的侄子、年仅七龄的顺治帝此时已在沈阳即皇帝位,多尔衮代表其侄“定天下”205。约略与此同时,他晓谕南朝官绅军民人等:
曩者我国欲与尔大明和好,永享太平,屡致书不答,以致四次深入,期尔朝悔悟耳,岂意坚持不从。今被流寇所灭,事属既往,不必论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予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尽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干功名立业之秋。如有失信,将何服天下乎?206
但是“天下”有其自己的看法,并不想屈服于此一晓谕或其他晓谕。6月7日,清朝下令,所有中国男子依满洲式样剃发蓄辫。满洲人诸如此类的行为激起了民众的暴动。因此,20天之后,剃发令取消207。有一件事应当记住:虽然满洲的社会政治组织基本上是准军事化的,而且其士兵可能是当时东亚首屈一指的斗士,但是满洲人跟他们想统治的汉族相比,人数微不足道。而且满洲之地,经济状况艰苦,清军(其中满洲各旗人数不足三分之一,其余是同盟的蒙古人及辽东汉人)并未处于最佳战斗状态208。当时北直隶的清军,包括吴三桂部队,总数大约为28万209。而在南方,即便是弘光朝直接供养的军队,据保守的估计,已达35万(河南西部、四川、广东以及其他边缘地区,军队更是难计其数)210。至于李自成的军队,虽然其人数连大略估计都不易,但肯定很厉害,尤其是在陕西的根据地211。上述以及其他的不利情形使得多尔衮对于投清的中国文武官员持续不断地敦促,不立即予以回复。这些官员似乎比满洲人更热衷于征服整个中原地区。因此,多尔衮在7月中旬由信使传递到南方的正式晓谕中,更为谨慎小心,抱试探的态度。他一开头就大大称颂明太祖与崇祯帝,而后严厉斥责叛军,并列举清朝礼葬崇祯帝及其后妃的功德,接着又说:
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清万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咨尔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扬。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敦睦邻之谊。其有谅力不敌,北面归顺者,当各剿勍旅,佐我西征;或削平所属余贼,用以自效。无不开怀延纳,乐共功名……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或假立愚弱,实肆跋扈之邪谋;或阳附本朝,阴行草窃之奸宄;斯皆民之蟊贼,国之寇仇,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师南讨,等彼鲸鲵,必无遗种。212
此一晓谕表明,满洲人在7月中旬决定:定都北京,迎清帝至北京临朝,而后先击败陕西的李自成军(或许更进一步击败四川的张献忠军),然后逐渐绥靖东南213。这晓谕也表明,满洲人对付南方,在实力上并无确切把握,暂时不愿招致南方的敌意214。他们声称,对清朝统治北方之意,应予尊重;并威胁说,只要南方政权表现不信(即不合作)或不贤(即无能),他们便要南侵。
当时,位于南北二都中间的山东省,一片扰攘,使南北之间消息隔阂。大顺军残部在不少地区掌权,但是渐渐地,他们不是被地方军队击败,就是被驱逐。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武装争夺控制权的斗争215。“流寇”、乡绅武装,以及明朝正规军的散兵游勇,互相攻击,使山东省陷于混乱(弘光朝所遣的使节留滞道途,这也是一个原因)。清朝必须尽快在山东立足,不仅是为了一旦其主力挺进西南时,防备叛军攻击其东南翼,也是为了弄清南明在山东的影响如何,并阻挡南明经由山东的任何进攻。于是在7月下旬,清军开始协力向前,进入了山东北部;到了10月底,已经沿着山东南部边界以及河南省黄河北岸,建立了一道薄弱的防线216。
这是一次次要攻击,是防御性、试探性的,进行策划的文武官员几乎清一色是汉人。清朝已将满洲部队保存起来,或已把他们转移到更为重要的西线(即陕西东、北二边)。这些汉人文武官员的任务既乏光彩,又有危险,令人有挫折感。李自成军活跃在他们的后方;数目可观的明朝军队不是离开不远,就是企图从海上包抄他们;沿着北纬35度线,则满布着骑墙观望的武人217。降清明将急于向清朝邀功,纷纷劝诱南明将领叛变。他们为此派出密探,并作了许多乐观估计218。但是,不论是派出密探的人,还是积极响应的人,都不为清朝所信任。清朝虽然需要中间人,但是在此进行征服的早期,则并不希望新降的明将与南明将领接触太多。弘光使节在清朝地界受到隔离,部分原因即在于此219。
但是多尔衮喜欢在最高一级进行个人外交。1644年8月,他移书史可法。这份书信可以看作是清朝方面争取明朝官员的标准函件,内容包括:颂扬对方的成就与声誉,列举对方的亲戚、朋友、同僚中已投顺清朝者的名字,声称清朝对“前明”的敬意,用中国经史中类似例子以为暗示(不论这些暗示多么不确切),举例证明明朝宗室勋戚以及与对方同等地位者降清后所受礼遇。多尔衮在此移书中,还以南明未能对叛军有所行动来刺激史可法:
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乎?
多尔衮接着敦促南明福王放弃帝号,还就藩位,可以备极尊荣,长享富贵。
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220。
由此可见,到了8月下旬,清朝已不再允许南明在南京建立朝廷,但是他们仍然希望,可以不必全面进攻,而用恐吓手段使南明承认清朝的优势地位。
10月15日,史可法作答书,对多尔衮移书的内容和口气表示惊讶。他解释说,使臣已就道,在其使命达成之前,他个人不宜有私交。他婉转地告诉多尔衮,移书中对南方官员的看法与评价均属错误,并指出,弘光帝即位不仅合法,而且万众拥戴。
忽传我大将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成,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
为报满洲人的功德,明朝使臣携带礼物,而且愿意作出安排,与满洲联兵进讨叛军。史可法建议(与首席使臣左懋第的看法截然相反),效法宋、辽,建立和谐关系。其含义是,辽满足于占据东北一角之地,岁受金帛,愿助中国,但不垂涎全部中国土地。
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窥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为贼人所窃笑也。贵国岂其然乎221?
史可法以此设法冲淡满洲人在北方的成就,向多尔衮强调派遣使臣的重要,并说,清朝若是如自称的那样为大明复仇,就不应如此行事。
满洲人所得到的有关南方情形的第一份情报,使他们相信,应当谨慎222,采取守势。但是自10月25日起,清朝官员和弘光朝主要武臣使节陈洪范有了接触,多尔衮于是开始得知形势发展情况。南明使臣亲见了清军实力之后,应当如何调整出使目标呢?陈洪范和主要文臣使节左懋第对此意见不合223。随后的一个月后,清朝方面态度改变。到了11月20日,多尔衮之弟多铎受命准备立即进军江南224。这场战役分三阶段进行(见地图3):
(一)清军首先需要完成正在陕西进行的对大顺军之战225。到11月初,他们完成了西进的第一个目标,夺取了山西全省226。11月17日,多尔衮之兄阿济格被任为大将军,率军由陕北的延安进攻,以摧毁李自成在陕南的据点。11月25日,多铎离开北京,即时南下227,可能是通过河南。但是清军不久获报,大顺军已出了陕晋豫三省交界处的战略要地潼关,在河南省西北部颇为活跃,令人不安,可能使两个战役都难以成功。多铎然后接到命令,首先消灭河南西北的大顺军,然后与当地清军会合,进攻潼关,于是便能和阿济格一起,对大顺首都西安形成钳形攻势。若是两位大将军终能击败大顺军,便须等待下一步的命令,而后向西南或东南进发228。
1645年1、2两月,清军的这一计划得以实施。一支仅五六千人的精锐部队,在多铎率领下,在洛阳直北的孟津渡过黄河,击破西边的大顺军,并在南边和东边接受了半独立的寨堡守军以及明朝将领的投顺。多铎随后率全军进击潼关。经过一周的激战,潼关于2月8日攻破。阿济格从北面进逼西安,李自成于是放弃了陕西南部,率领人数依然众多的溃军向东南方越过武关,朝湖广西北端的郧阳和襄阳逃去229。
与此同时,清军不顾山东境内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向南直隶与河南东北的南明北部防线增加压力230。史可法以及南明前线各总兵把这次行动看成很大的威胁,作出了相当的努力来重新部署南明部队以应付攻势231。但是就清军方面而言,这似乎只是声东击西的战术,用以“软化”明军防御,为而后真正的大军攻势预做准备。开封、归德、徐州以北地区的清军统帅受令不得渡过黄河。这一任务留给一支新来的部队,这支部队于2月9日自北京出发,近月底抵达232。
(二)此一阶段,清军要征服的是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战场有两个,相距颇远。在西边,阿济格追逐李自成,自汉水河谷而下,进入了湖广中部的北段。到了这里,李军不顾一切,四散逃生。3月末,武昌得知败军自北而至233。正是这股败军狂潮,促使左良玉军发动了上述“东征”,沿长江而下,直逼南京。李自成本人则在武昌与岳州中途的某一地点渡过长江,进入了通山附近湖广、江西交界的山区。(指瑕:李自成在武昌与岳州中途的某一地点渡过长江,这一点不假,但并不是就进入了山区,而是向东北折向武昌,并占领了武昌,但随即遭到尾随而来的阿济格大军围攻,只得放弃武昌顺流而下,一路又接连被阿济格部击败,大将刘宗敏被俘,他只得在九江附近折向瑞昌,过武宁,辗转来到通山。)他几乎是单骑匹马,只有一小支斥堠部队,据说在此山区为农民所杀,时间可能是1645年6月初234。但是,阿济格正在攻占备受破坏的武昌和九江,追赶散处湖广中部的二十万李军,相当一段时间,并不知道李自成已死。阿济格还派出几支清军,协助攻占河南和江南235,不过,对那些地区的主要战役并不起决定作用。
多铎扫清了西安附近与潼关外围之后,在3月11日过后不久,接到了命令,按原计划进军江南236。2月初,高杰在睢州为明军将领许定国所杀。许定国与清朝方面通款,已有相当时日,对高杰的邪恶凶残,更是早就怀恨在心237。高杰之死这一突发事件使多铎进军大为容易。高杰军由睢州奔回扬州,沿路劫掠。江北诸镇总兵和许定国一样,都对高杰有宿怨,因此无人能整编高杰部下。高军中有几支完全失去控制的部队,在过了扬州抵达瓜洲时被镇江来的炮火阻止,因而未能渡江到南岸238。
许定国投降清朝,并愿意效力;明朝方面最精锐的部队土崩瓦解。这些事情对满洲人来说,是意外收获,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发展。无论如何,他们的计划已有相当进展。清军惯于三头并进,这次也是如此。1645年4月1日始,清军分兵三路,同时进入河南东部。其中有两路分别经由洛阳以东的虎牢关和龙关,另一路在兰阳渡河,越过开封以东。4月下半月,清军主力在归德会合,同时派遣几支小部队越过河南东部广阔的灌溉地带,攻占各寨堡、城镇239。4月30日,多铎再次率军,三路进发,试图在临淮、盱眙、淮安三地渡淮。各路军势如破竹。明军不是投降、瓦解,就是闻风而逃240。
这时左良玉虽已死于九江,他的部下继续沿江劫掠,直逼南京。马士英恐惧左军甚于恐惧清军,他突然抽调各镇总兵离开北部防线,去阻止左军东进。史可法正忙于调兵北上,到徐州抵御清军,此时也接到弘光朝西上之命。他像其他人一样,竭力表示反对,“不知士英何以蒙蔽至此!”但是他不能违背上谕241。正如史可法所预料,沿江各镇应付组织涣散的左军本是绰绰有余,而清军则未经抵抗,已在临淮与盱眙渡过淮河了242。
史可法冒雨涉泥,马不停蹄,自浦口驰回扬州。仅仅4天之后,即5月12日,清军先头部队也抵达了扬州243。史可法麾下大部分部队,最近忽而北上,忽而西进,散处各地。前来扬州与统帅会合的军官中,有几人想强迫史可法一同逃离扬州。史可法拒绝了,但是他并不去阻止那些军官离开。许多扬州百姓也逃走了。留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有守城经验的人。但是这些人嫌恶明军,尤是憎恨最近再度蹂躏扬州的高杰部队;他们也不喜欢史可法允许能征惯战的高杰之妻及其亲军在扬州安顿244。因此,虽然扬州百姓建立了抵抗清军的坚强防御,但是极少有明朝正规军参加,内部也很少有团聚力。
当清军渐渐包围扬州时,多铎一再致书史可法,敦促投降,但毫无效果。5月19日,清军开始用大炮轰击一面城墙,次日城破,满洲兵涌入。随后史可法下落如何?有关记载是传闻多于事实。但是最为可能的是:他自杀未遂而被执,带到了多铎面前,拒绝投降,因而被杀245,在屠城中尸骨不知去向。
扬州是江南顽强抵抗清军的第一座城,也可能满洲人想杀一儆百,于是下令屠城,破坏持续了十天以上。一位幸存的扬州居民记下了这段可怖的经历:
城中四周火起,近者十余处,远者不计其数。赤光相映如雷电,辟卜声轰耳不绝。又隐隐闻击楚声,哀顾断续,惨不可状。
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
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余人。
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
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姿容俊爽。随从一人,衣黄背甲,貌亦魁梧……红衣者熟视予,曰:“……明日王爷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幸勿自毙。”246
在此期间,清东路军在满洲贵族准塔率领下,从徐州向淮安缓慢前进,沿途遇到刘泽清部的有力抵抗。但是当准塔逼近淮安时,刘泽清和在淮安的漕运总督乘船撤至海上,其他官员则举城投降。这支清军继续在运河以东攻城略地,而多铎的主力部队则进至瓜洲地区,并于5月30日在该地部署,准备渡江247。
(三)下一目标是夺取南京和南直隶。在京口的水师以及在镇江的陆军暂时阻止了清军渡江;但是这些军队是最近从闽、浙暂时调来,因而情绪不稳,而且如上文所述,由于政治原因,指挥也未能前后一贯。因此,清军终能在6月1日的雾气迷蒙之夜,以声东击西的战术,使一支极小的部队渡江到了南岸。明军士兵发现清军近在眉睫,当即陷于一片混乱248。
在长江对岸驻扎着中国军队,人数甚多,他们脱下的靴子就可建成一道壁垒,使鞑靼骑兵匹骑难越。但是要在战场上获胜,靠的是决心和勇气,而不是人数;因为鞑靼人甫一上船,中国军队犹如羊见了狼,一齐奔逃,留下的是一整片无人防守的江岸。249
当明军望风溃逃,一路破坏时,清军则从容占领了镇江,南下至句容,计划从东面和东南面进逼南京250。
弘光朝最近正在大肆庆祝击败左良玉,得知清军云集长江,则举棋不定,陷于瘫痪。是守还是逃,没有人愿意带头提出;只有一种气氛笼罩着,即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上召对,君臣俱无言。上曰:“外人云朕欲出幸。”王铎请其语何自,上指一小阉。铎正色语阉曰:“外语不足传也。”因请讲期。上曰:“过午日。”
于是就回内廷享乐去了251。事实是,不少官员正偷偷逃离京城,留在京城的则在策划和满洲人做交易:不是投降就是赔款252。6月3日夜间,皇帝既不告诉马士英,也不告诉皇太后,带了一帮太监和一千名骑兵从通济门而出,想到别处找一个避难之地。次日清晨,马士英也带着家丁和皇太后,向西南方而去,不过不是为了追赶皇帝,而是为了逃命253。
接着,皇宫遭洗劫,尤其是不得人心的官员,住宅和家人都遭到愤怒市民的攻击。同时,有两个权威中心在互相竞争,设法取得城内居民的拥戴:“假太子”被狂热群众释放出狱,又被一群市民拥入大内“登极”,于是开始临朝,并向百姓发布上谕;提督京营忻城伯赵之龙也自其官署下令,试图维持城内秩序,静待清军对他提议的答复(看来他的提议可能是交出全城,维持安定,以换取宽大对待)。6月6日,赵之龙获得了所希望的答复,于是就取消了那位可笑的“太子”朝廷254。
次日,清军先头部队抵达皇宫正南的城门外;6月8日,一群乌合的明朝文武官员站在倾盆大雨之中,卑屈地迎候多铎。多铎在城外驻扎了7天,信心十足,接受了更多人的投降,确知城内一切平静,并得到了赵之龙的盛情款待255。赵之龙不仅自己晓谕南京百姓,指斥弘光帝与群臣,还代发多尔衮对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的晓谕。多尔衮的晓谕责备南明朝廷对流寇不发一兵,“如鼠藏穴”,却过早拥立新君,文武事务处置乖方,自生反侧,以启兵端;还说,抗拒不顺者,自身遭戮,妻、子为奴,不过,若是自愿投顺,则予以宽恕,各升一级,即便是福王,也一体优待,因此普通百姓不必惊慌256。
此外,多铎还下令:所有投顺的明朝武人必须依满洲式样剃头蓄辫257。投清的前明文武官员也发布晓谕,表示拥护:
自辽金元以来,由朔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代无道,靡不弃好而构隙,问罪以兴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夺义、逐我中国不共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自古未有王师以仁以礼、雍容揖让如大清者也。助信佐顺,天与人归。渡大江而风伯效灵,入金陵而天日开朗。千兵万马,寂然无声;儿童聚观,朝市不变。三代之师,于今复见258。
6月16日,多铎进城,拥全副仪仗,骑马由洪武门而入;而后询访清军攻占南京期间南明方面殉节者的姓名,共得28人259。弘光帝先是逃到芜湖东南黄得功军营。6月中旬,黄得功在战事中被他以前的同袍刘良佐杀死。弘光帝随之被俘260。6月18日,刘良佐和他新的满洲袍泽把弘光帝(现在又成了福王)带回南京。一路上福王遭到愤怒百姓的唾骂,清朝方面设酒,命福王坐在他拒绝承认的“太子”下首。席间,他更受恶言相待。(不过,多铎暂时还是尊重太子,以收取南京民心。)这位废天子在回答多铎咄咄逼人的问题时,俯首帖耳,说话支吾,汗出沾背,但在此时还是能免受皮肉之苦261。
随后,多铎遣贝勒博洛率领另一支军队远征,沿大运河向东南进发,协助平定苏松地区,以夺取杭州。7月1日,弘光朝残余的文武官员及皇太后劝潞王在杭州监国,潞王勉就。这位监国只是派了一位常年做调解人的陈洪范与清军谈判,其他政治措施一无所有。7月6日,博洛军逼近杭州,监国、巡抚和百姓都不战而降。事实上,百姓们很乐于从此摆脱漫无纪律的明军之害。这些明军从长江溃散下来以后,一直成群结队,在杭州四周流窜262。命运作弄,潞王、福王、“太子”三位在1645年秋一同解往北京。其后,三人中无一能苟延性命263。
所有这些事情中最令人刮目的,是清朝压倒一切的军事优势。这不仅表现在战斗力上,还表现在军队一旦不再对敌作战时,如何加以约束上。与此同时,是长江以北几乎所有的明军将领都闻风而降,并积极合作264。清军抵达南京时,归降的有总兵23员,副将47员,参将、游击共86员,马步兵共238-300人265。这些数字还不包括略作抵抗就投降的左良玉和刘泽清的主力部队266。在南明历史的最紧要关头,职业武人所走的道路,明显是在从内部破坏国家政权。他们认为,这个政权对待他们不公,而清朝则可能给他们以成功的机遇,因而对之有好感,甚至甘做“贰臣”。
清朝以军事手段平定江南,取得如此成就之后,现在转向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清朝之所以能在其征服事业的而后各阶段获致成功,取得江南被视为根本原因。清朝官员深信不疑,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巨大粮仓,能纾解北直隶的持续粮荒,因此他们一直集中精力于恢复大运河的通航。运河几乎废弃不用,已有二年,和黄河堤岸一样,也亟需维修267。清朝为了象征性的原因,也为了财政的需要,尽管人手有限,还是尽速派遣官员到各府各县,去收集土地和税收册籍。
清朝另一件必须注意的事,是在明朝称为“南都”的南方大都会恢复某种形式的文治政府。清廷不久决定,在这方面不循明朝旧例,而把南京改为“江宁”,作为江南省(即前南直隶)首府所在地。(按:本书始终使用“南京”与“南直隶”二名,以求前后一致,也是为了遵守明朝惯例。)于是南京的官僚系统必须因革裁并。到了8月底,多铎已举荐了372名汉人在江南省一级任职,还在清朝的军事系统内安置了374名前明勋贵与武官268。此外,在8月初,才能出众、一心与清朝合作的洪承畴,被任为清朝控制下南方各地区的总督,可在其南京督署经略一切政治、组织与后勤事务269。此一任命标志着清朝的一个重大转折,即在其“大业”的社会政治与军事诸方面更为注重平衡。
民众更为关切的,是北京所颁布6月24日起须在南方实施的38项政策,类似政策上一年已在北方公布,包括:大赦;蠲免一切明季加派、分外科敛、加耗重收,以及由此而来的积欠;严惩官吏枉法受赃;减免正粮,归顺地方尤须减免;酌量推用投诚归顺的文武贤才,并征聘前朝文武官绅、勋臣以及怀才抱德的山林隐逸;振兴贸易;抚安穷民,使父母妻子得以团聚;为地方豪强所夺财物归还原主,逃避他乡者可重返家园;重建各地儒学,恢复科举考试;以及旨在争取清朝统治下民心的其他措施。清廷对于尚未归顺之敌,则诱之以利:叛乱者投诚,一概免究;明朝文武大臣曾抗拒者,若能来归,照旧委任,官阶、爵位、俸禄不减;明朝藩王若能奉表来归,一体优待,乃至待以殊礼,恩赡有加270。
但是其中有一项与清朝以前的政策截然不同。清廷6月28日在北京,7月21日在南京敕令:成年男子,凡非僧道中人,必须剃发易服,以示归顺清朝。清廷大体上承认,人人按高领、窄袖、下摆开襟的满洲式样改换或重制服装,确实需要相当时日;但是剃发(即在脑后留一小片头发,剃为圆形,梳成辫子,被讥为“金钱鼠尾”)就不同了:各地自此令到达之日,限于10日之内,尽使剃发,违者处死271。
如前文所述,满洲人曾在北方取消了此一命令,攻占南京后,更是清楚表明,只有武人才从满俗,据说其理由是战场中易于辨别敌我272。从表面看,满洲人在取得明朝南北二都之后,以为自己已居于强有力的地位(或许是过早了),可以再次坚持“君臣一体”了。但是从多尔衮日记可知,就在北京下剃发易服令两天之前,有些汉人声称:依照“礼乐制度”,不宜剃发;多尔衮大怒,反驳说,满洲人也有其社会与礼仪制度,决不能视为低于汉人。
若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犹自有理。若谆谆言礼乐制度,此不通之说。予一向怜爱群臣,听其自便,不愿剃头者不强。今既纷纷如此说,便该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273
不论这是出于冷静的权衡还是一时的愤激,或二者兼而有之,突然强行下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情绪,其作用超过任何其他的因素。
在长江流域,南直隶江南地区、江西中部,以及湖广中部与东北部这三大区域内,抵抗蜂起。虽然这三个区域情形各不相同(每一区域内各地情形亦不同),但在明人抗清的这一阶段,彼此之间还是有若干共通之处。首先,各地的明朝正规军事组织已土崩瓦解,只在零星地区还有官军的指挥。因此,动员武装抵抗之举互不相关,颇为狂热,地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协调,邻近各地的首领之间也没有多少联系。
其次,明朝方面这一根本弱点因下述各方之间的不能合作以及互相冲突而更形恶化:(1)文人:包括明朝文官以及他们个人指挥下的军队(不论是募兵还是民兵);地方上拥有科名者和其他显要人物,以及靠他们的财产和地方服务召集而来的半私人武装;由当地百姓组成的志愿募兵。(2)职业军人:包括水陆诸师中的总兵官以及参将、游击。(3)草莽人物:包括大股流寇部队的残余、土匪、海盗,以及其他非法武装组织,如帮会之类。对于抗清悲剧中的人物来说,分野当然不像以上所说的那样清楚。抗清活动犬牙交错,就具体的人而言,属于何种类型是游移难定、界限不清的。例如,此时的职业军人,大部分是由以前的流寇所组成,包括其普通兵士及杰出首领。这使得约束这部分军队大成问题。甚至志愿兵士,一旦迫于生计,也会干起盗贼勾当。但是,若是将南明历史看作一个整体,并在此框架内把握长江流域抗清活动的全貌,上述分类法似有其用处。
声名最著的抗清活动发生在南直隶南部,其中最为激烈的,是东部的苏、常二府以及西部的徽州府这样的经济最发达地区。在苏、常地区,军事当局因苏州巡抚祁彪佳的免职而力量削弱;随后,清军自瓜洲渡江,击溃了集中在镇江的守军,该地区的指挥系统也就瓦解了。新任巡抚抵达苏州不久,就带着卫队撤退到浙江南部,来自各省的军队则纷纷逃回原驻地;苏松水师总兵官于是实力顿弱,只能带着余部退往太湖东岸,在湖盗和水上自卫武装之间苟延残喘274。在南直隶西南部,先是左良玉军的攻掠,而后是阿济格率领满洲兵抵达,在九江的总督袁继咸因而动弹不得,安庆与南京之间沿江各镇的总兵也都仓皇后撤,不少人一直撤到了海上。黄得功死于芜湖附近,更使这一地区失掉了协调各军的最后可能性。
此外,当弘光朝瓦解,南京沦陷,清廷派员四出收取官府册籍,接管各衙门时,南直隶几乎所有的南明府县官都弃职而去。这些官员既感到清朝的威胁,又惧怕社会上日益增多的大胆妄为之徒——设法废弃契约并向主人报复的奴婢,要求平反的秘密宗教组织,现在可以肆无忌惮地从事“保镖”和勒索的绿林团体,地方豪强所招募、试图夺取公款公物的私人武装,诸如此类275。这表明,不仅省、府当局的权威消失,即使是基层政权,对于遍地组织起来的自卫武力也不能加以控制。接着是抢山头、争位次的可怕竞赛:各类武装团体设法消灭当地的对手,争夺对衙门的控制权。
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当剃发易服令激起民众愤怒之时,忠明之士挺身而出,试图制止朝廷权威的彻底瓦解,在其家乡或是任地方官之处恢复朝廷的号令。这些人多半是有科名的缙绅、前朝廷命官,被清朝赶下台的前地方长官,以及因长官逃亡而负责衙门事务的下层地方官员。这类抗清力量以文人为主,他们当机立断,着手把当地分散各处的武装以及邻近各镇水陆军残部集合起来,组成了可以作战的防卫武力。但是他们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军事经验,因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控制这类不稳定的联合力量。最后,他们甚至丧失了地方乡绅的支持。乡绅们尽管与那些忠臣声气相通,但他们所希望的主要是避免战事和恢复社会秩序。要是在代表明朝的人物领导之下,战事能够避免,秩序能够恢复,那当然更好(不管怎样,明朝这一象征仍然可以引起各阶层人民的呼应)。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若要做到这一点,似乎最好是跟代表清朝的人物合作。这些人也是汉族,只要忠明的抵抗力量被压制下去,他们也许就可以使满洲骑兵不入地方。由于这种缘故,地方社会的中坚分子,往往会不再支持忠明之士276。(以下所述,参看地图4。)
南直隶的反抗始于7月底8月初,发生在苏州、常州二府最早接到剃发易服令的江阴、嘉定、昆山、松江等地。但是这些地区除了众多水道使骑兵炮兵行动不便之外,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在清军炮火之下,城门城墙成了齑粉。以竹竿对马刀,以掷便壶对弓箭,如此的反抗只能以惨剧收场。顽强抵抗的各城像扬州一样,成为清军俎上之肉,主要的“屠夫”则是在徐州投降的原史可法部将李成栋277。
稍后,西边的徽州、宁国、池州各府也发生了公开的反抗,持续时间稍长,部分原因是大队清军需要更多时间方能抵达,以及徽州抗清领袖金声才能出众,不过,最主要原因可能是宁国到休宁间有一道山间天然屏障。尽管抵抗激烈,清军对此一地区的镇压并不像在长江三角洲那样野蛮。这多亏提督总兵张天禄(另一位前史可法部将)的更为宽厚的政策278。虽然次年春天,反抗事件仍有发生,尤其是在南京西南方279,但是到了1645年12月初,在南直隶南部,大部分陆上的公开抵抗活动已被粉碎。
清军实力主要在于骑兵,此时他们感到最棘手的,是长江口的崇明岛以及三角洲中部太湖区域的忠明之士,这些人与湖寇、海盗、渔民以及明水师残部联合,应付不易。常州的抵抗军向崇明求援,太湖抗清之士则向东、西、南三方出击,以支持苏州、吴江、湖州、长兴、宜兴等地的同志。1645年冬初,李成栋在崇明确立了(颇为微弱)清朝的统治,从而完成了他的镇压行动,但是,直到1646年5月,清苏松水师提督总兵吴胜兆才完全击败太湖区域抗清主力280。(以下所述,参看地图6。)
江西北部早在北京陷落前即遭到张献忠流寇部队的劫掠,因而军事指挥系统力量削弱,地位动摇,在左良玉军持续过境以及清军自武昌出发进行追击之时,则几乎完全瓦解,和南直隶南部情形相似。总督袁继咸在九江附近被俘,江西巡抚则自南昌南逃。在万安的叛离明军的副将,其手下兵士奸淫掳掠,引起市民与民兵奋起反击,使他大为不满,于是逮住巡抚,献给清朝,作为投降的贽见礼281。
此时,清朝在南昌与九江的当权人物几乎都是金声桓的下属。此人也是史可法部将,后被派去辅助左良玉。当左军向清朝投诚时,金声桓已收编了散处湖广的部分李自成军,并迅速行动,于6月底7月初夺取了鄱阳湖地区,企图占领江西全省,献给清朝,以求恩宠282。
由于上述诸事件,江西北部金声桓辖区内的零星抵抗活动变得无足轻重,该省抗清前线也因此从一开始就移到了中部庐溪、建昌、临江、袁州一线。(批瑕:江西无庐溪县,按照文义理解,应为泸溪(今资溪),这应该是译者的错误。)但是事实上,统一的抗清前线可说并不存在。在赣江东岸,建昌和抚州等主要城市几经易手,终为清军所得。该地区最著名的抗清领袖是几个明朝小宗藩,由此可见这一地区明宗室人数的众多。有关这些人的抗清活动,所知甚少,只晓得他们尽管既少经验,又乏粮饷,还是坚持零星的抵抗283。
他们的特点是目光局于一隅,既无能力,也无意愿与其东邻西境的抗清力量建立联系,协力合作。这些小宗藩及其支持者所求助的,主要是江西、福建、广东三省边区声名狼藉的土兵与山贼284。要重建江西的军力基础,这些土兵山贼实在没有什么用处。这一地区抗清活动之所以能持续,部分是由于金声桓营垒内部的纠纷(见第五章),部分则由于东面邻近山区,可资隐蔽,另一不能忽视的原因是福建各总兵前来救援(尽管受到挫折,同时也难以协调)285。
1640年代,江西东北部的破坏尤为严重,其影响持续多年,尽管清朝已在该地区建立了名义上的统治。迟至1654年,一位商人经过江西此一地区时,还是甚感惊讶,他写道:
予自江右入浙,过鄱阳湖,进舟上饶江,所历安仁、贵溪、弋阳、广信、玉山诸郡县。入其城,大都不过数十家,而江中行舟竟日罕见。惟一徽人舟,行泊相依,因言康镇将者,河南人,日率健儿入村落,系乡民以归,指为山贼,屠掠殆遍。广信一府,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余以业盐,持引穿横卒而过,无敢呵者。入贵家大族,皆闭户团坐待死,得吾升粟撮盐,则大喜唯吾所欲而不较。予闻此言也,掩耳急去。286
赣江以西,抗清活动更有组织,成功的因素也更多。多数地方官依然在位,并得到原籍江西的崇祯、弘光二朝名宦的支持。此外,两年前,特别从云南、广东招募了大量官军兵士。当他们抵达江西西部时,得知南京陷落。现在,这些人士气很高。
广兵跣足,跳山谷如飞,滇兵甲械尤犀利,标铳连弩,洞胸穿札。287
但是成功的各因素未能结合在一起,因为负责的文官未能控制“主”、“客”兵之间的冲突以及兵民之间的冲突;在民这一方面,更是到处发生奴变。一位向福建求援的监军这样说道:
将与将战,而又与吏战;兵与兵战,而又与民战。……虽有愚恳道臣……亦止终日劳劳和事而止此。无怪督臣李茂永之呼天出血也。今为虔计,皇上不宜再设兵,止宜设治兵之臣。设兵,是乱丝而益以丝也。不若设督抚以为治丝者。288
虽然有这些问题(此外,部分原因是金声桓方面出了麻烦),忠明之士依然能从西南方向前推进,于1645年秋末收复了吉安289。但此时总督的权力给了前弘光朝太仆少卿万元吉,他军事经验丰富,不过和“外兵”似乎没有建立起良好关系。
[初,临江乡绅、加大学士督师杨]廷麟待[滇营兵]以客礼,滇将赵印选、胡一青亦德之,奋勇建功,颇多斩获。……元吉与诸将讲体统,申约束,诸将稍稍不乐。
万元吉后来对待客兵甚至更为傲慢,还想依靠临时招抚来的土寇计日出山区下东南。但是清军新添生力军先到,万元吉的防御瓦解,吉安再陷290。此事发生在1646年5月,当时清军另外还在江西东北隅平息最后的主要抗清活动291。自此以后,江西民众的反抗大致限于南端的赣州府。
在湖广中部,明军的抵抗也是在混乱状况中展开,其混乱甚至更甚于南直隶与江西。但是,几位杰出的官员作了艰苦努力,而清朝在湖广的地位原来就最为薄弱,增援也最为困难,因此有组织的抗清活动得以坚持下去,时间要长得多。1643年,张献忠军曾广泛占领湖广的中心地带,该省当局的军事控制首次遭到了破坏292。在此期间,一些明军将领退往南部山区周围,从而免遭毁灭。他们活了下来,并以各种手段聚集残部。在张献忠放弃湖广进入四川之后,他们小心翼翼,保持独立,再也不愿完全受武昌方面的指挥调度了293。此外,左良玉兵变时,湖广总督何腾蛟被劫持,沿江而下,带往江西,好不容易才只身脱逃。当他最终回到湖广时,省级文武机构已一切荡然,只能在长沙白手重建294。
使明清双方都感到棘手的,是李自成军与左良玉军的余部。这些部队散处在整个长江中游区域,从荆州直到九江。其中大多数,或是先伪降清朝,而后只要环境许可,即与清朝断绝;或是假意作态,表示愿降295——大家都在疯狂争夺粮饷(此时湖广地区已极度缺粮)及更为安全的阵地,至少要求得短暂的喘息,以便从以往数月中令人精疲力尽的行军中恢复过来。左良玉的几位部将溯江而归,在岳州为何腾蛟效力。李自成残部最大的两支则因失去了最高统帅而向长沙、湘阴地区的何腾蛟及常德附近新任湖广巡抚堵胤锡接洽,要求归顺明朝296。何腾蛟起先连哪些是叛军都不知道,并不认为这次合并是一大收获,因为他身为总督,必须对成千上万各式军队的驻扎和给养负责,而湖广这一残破省份实际上只供养得起其中一小部分。因此,何腾蛟虽向这些军帅各授官职,但对于他们为求生存而恣意掳掠、流动,也只能默许,别无他术(参看地图5)297。
荆州和武昌的清朝官员也有理由感到焦虑沮丧,因为他们觉得受到无形之敌的包围,这个敌人既危险,又令人难测,而他们自己却没有足够的兵士和给养来应付这一局面。他们向南京和北京凄切求助,反应却很慢,因为靠得住的清军为数有限,却又深深卷入别处的战事之中。此外,清朝夺得江南之后,也遇到了弘光朝面对湖广的基本问题,即江南、湖广的粮食贸易已发生逆转,现在是江南倒过来要向湖广供应粮食。还有,长江三角洲的粮食储备亦已锐减,其中相当一部分又要用于缓解北直隶的长期不足298。清廷与弘光朝一样,也发觉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境地:一方面减免正粮绝不能太多,已取消的科敛亦应恢复;另一方面又意识到广大农民嗷嗷待哺,为恢复生产必得有某些减免299。在此情形下,满洲平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勒克德浑直至1646年2月底才抵达武昌,负责攻剿事宜300。
何腾蛟不久发现,左良玉军中的“盗贼”不可信赖;他还发现,前大顺军有其自己的紧迫需要以及指挥习惯,即使是湖广的明朝官兵,其军帅实际也是独立的,只有他们感到方便时才服从命令。因此,何腾蛟采纳其杰出的僚属章旷(南明罕见的几个文武全才之一)之议,重建了总督军权,主要统辖的是滇军。这些军队后来一直效忠于他(何腾蛟本人也是原籍西南)。何、章二人以无休止的整顿、谋划以及对湖广南部资源的刻剥,终能在岳州以南不远保持一条坚固的抗清防线,有时还能出击。他们甚至还能派兵援助江西西北部,自1645年初冬起直至1647年初秋,为时一年以上301。不过,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将沉重的负担转接给了民众。
骤加派义饷,兼预征一年,民田税每亩至六倍以上。不足则开饷官饷生之例,郡邑长吏皆以赀为进退。又不足,则开募奸人告密,讦殷富罚饷,倾其产,分诸营坐饷。……湖南民展转蔓延,死亡过半。302
甚至在勒克德浑的先头部队抵达之后,清军还是不能集中力量对付湖广的明军防线;只有在消除了他们后方的一些特殊的麻烦以后,才得以采取行动。在大别山区(这条山脉把湖广东北部的武昌、黄州同北方的河南省分隔开来),布满了成百上千的壁垒。特别是满洲人在湖广首次颁布剃发易服令以后,拒绝归顺清朝的普通百姓和各式军官聚集到这些寨堡,进行猛烈的抵抗。在多数情况下,各寨之间建立了联防,有证据表明,这些抵抗活动的领袖与西南方长江以南的何腾蛟也有联络。但是未能形成一个可对武昌造成严重威胁的地区指挥中心,寨堡守军英勇顽强,孤军奋战,体现了这一阶段全面的民众抗清的努力。1646年,清军以骁勇善战的副将徐勇为先锋,逐寨进攻,终于渐渐击败了守军303。同时,勒克德浑集中力量对付仍在威胁西北部的岳州和汉水中游的李自成余部,不是把他们击溃,就是驱逐304。
到1646年底,清朝确信,无法说降何腾蛟;同时也认为,在武昌东北和西北二边对李自成余部的战役已告完成305,于是在1646年9月底,任命了一名大将军和两名提督总兵,再往南发动新攻势。这三人就是著名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位封王的降将306。1647年3月底,三人合力在岳州以南进攻何腾蛟军。何军通讯不良,内部又有怨愤(特别是何腾蛟自己的官军,对左良玉、李自成余部军纪不良的“蛮子”不满),一触即溃。清军随后夺取了长沙,何腾蛟和章旷退到衡州以南307。这时,整个长江流域看来已在清朝的牢固掌握之中,但是在湖广,则是混乱多于秩序。正如清湖南巡按在首先巡视后的揭帖中所说:
自壬午以来,无岁不被焚杀,无地不为战场。加以今春奇荒,骼胔盈道,蓬蒿满城。职自岳至长……村不见一庐舍,路不见一行人。惨目骇心,无图可绘。长沙为群逆盘踞数年,剥民已尽脂膏。临遁,复行焚杀。城中房舍皆无,民皆弃家远遁。然山岩河澨,犹自有民,可以徐为招徠……衡州除连年兵寇杀掳之外,上岁颗粒无收,春夏米价腾涌,百姓饿死大半。308
从上述情势明显可见,明清之间的长期争斗,与其说是两国间直接交争,还不如说是双方的一场竞赛,看谁先制服第三方,或是先为第三方所击败。这第三方就是17世纪中叶逐一吞噬各地的社会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在南明存在的整整18年中,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与清朝争夺地方控制权的敌手是明朝陷于危机前即已控制地方的明朝文武势力。在这一片面积仅次于大洲的土地上,有众多的道府州县。就明朝而言,问题是如何保持对它们的控制;就清朝而言,则是重建控制。大体说来,在这场竞赛中,明朝的失败比清朝的得胜来得更快。
第三章 第二次抵抗:鲁监国与隆武政权
在杭州未能支撑起一个监国政权之后,浙东和福建二地差不多同时建立了南明朝廷。这两个朝廷都鼓动长江流域抵抗清军占领(多半是象征性的,但也有一些实质意义)。虽然两个政权在若干方面都不一样,各有其特点,两者之间有争执,但是他们在军事行动及最高决策方面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整个南明时期的特征。
1645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满洲贝勒博洛夺取了杭州;同时,清军很快越过钱塘江口(按:严格说来,这条江水只有在分隔杭州、绍兴二府的下游一段才以“钱塘”为名。但本书为方便起见,将自杭州西南直过衢州的整条江水都称为钱塘江)。进入了浙江最富庶的两个府:杭州湾南岸的绍兴和宁波。两地的明朝官员也是闻风弃职而逃,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形一样。清朝官员接管了两府以及几个县的衙门,当即受到当地某些耆宿的欢迎,其他居民甚至还来不及组织任何抵抗活动309。但是也和以前的情形一样,清朝的剃发易服令在该地区一经颁布,民众的反抗怒火立即爆发。7月31日,余姚首先发生了反抗清朝官员的暴动,然后迅速波及会稽、鄞县、慈溪310。数天之内,清朝在浙东的薄弱统治已被去除。“礼乐之邦”的浙东,其人民一向以直道传统而自豪。与南直隶南部的情况相比,浙东的士大夫不久就表现了高度的社会凝聚力以及有效的领导才能。
各类明朝官员和社会领袖看到了这一自发的抵抗潮流,于是设法觅得逃离了山东的王庄、被命徙居浙江台州的鲁王(朱以海)。他们请求鲁王出山,使这一地区的复明运动有明朝帝室以资号召。鲁王答应了,他立刻被送往绍兴府城,于8月底或9月初称鲁监国311。早在鲁王未到之前,募兵、义兵、官兵水陆各军的将帅已在四处奔波,围绕浙东建立起一条弧形防线,从钱塘江中部的严州府起,直至位于宁波附近定海的水军据点,在桐庐和临山之间,营垒最密。(本章所述,见地图6)忠明之士希望,构筑了这样一道壁垒,在富阳和海宁的对岸还有进攻的据点,他们就可以和浙西和南直隶南部的同胞连成一气,使清军难以防守杭州312。
另有一位明朝藩王,原来的王庄在河南,新近指定他住在广西某地,此时他正途经浙江。这位就是唐王(朱聿键)。当首次有官员请他即监国位时,他推尊其从父辈的潞王。但是潞王政权一旦瓦解,已抵达钱塘江中游的唐王就接受了前弘光朝礼部尚书黄道周的正式“三劝”,于7月10日在衢州宣布,愿为下任监国313。总兵郑鸿逵放弃了在镇江的长江防区,此时正匆忙移师回原籍福建,因奉唐王离衢州,过仙霞关入闽314。
唐王沿路在每一站——浦城、建宁、水口,行为得体,俨若明主,让百姓看来确像他们的贤君。他称赞福建第一有实力的武人南安伯郑芝龙(郑鸿逵之兄)准备周到,使这一政权得以成立。7月26日,唐王抵达省府福州城外,当即(甚至在他正式即监国位前即已)任命一批大学士、尚书、侍郎及其他各类官员,并说明新朝廷各项原则。三天后,唐王入福州城,称监国,威严赫奕,俨若帝王。8月18日,即皇帝位,建元隆武,定福州为临时国都,以其弟嗣唐王位315。
新皇帝立即下令,将登极诏颁布到江西、南直隶徽州地区及浙江西南部,并向那些地区内他隐约觉得可能成为复明领袖的著名人士,颁发大量的征聘和任命诏书。他原想立即自西北方出关,举行“亲征”,以阻止清军的推进。即位仅7天之后,即有人劝阻,不可仓促行事316。于是隆武帝多少定下心来,着手在福州建立朝廷,进行更充分的军事准备,但是仍表示要及早“出关”。
不过,鲁王与隆武朝廷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随后就发生了一系列南明史上最痛心之事。1645年10月初某日,隆武政权得知,在浙江也有一个与之匹敌的朝廷,于是立即遣使者赍隆武登极诏前往绍兴。使者抵达后,鲁政权官员深感为难,各人看法不一。鲁王起先愿意下台,以成全其在福建的“皇叔父”(论辈分,论年纪,唐王都要早一世),几位德高望重之士也敦促绍兴朝廷,要以大局为重317。但是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国维情绪激愤,申述反对的理由:福州路远,“恐鞭长不及”;而浙东的抗清运动本甚脆弱(尽管英勇),一旦监国撤销,即会瓦解,在此关头,若移忠于他人,君臣之间的信任便会出现裂痕。鲁王为此说辞所动,其他官员也感到必须团结一致,拒绝隆武的登极诏书,于是使节被遣回,所获的答复一如张国维意旨318。最后,虽然鲁王手下不少文武官员私下要求或接受隆武的职位、官衔,鲁王的朝廷却没有正式谋求两方面作实际的协调,于是彼此间的“水火”关系加深了。
1646年2月,隆武帝向“皇太侄”发了一封私人长信,情辞恳挚,对于鲁王拒不认他为皇帝,深表不满,声称他之所以更有权当皇帝,决不出于利己之心;并央求鲁王戮力同心,共图恢复;至于计划在鲁王境内采取军事行动,他说那是出于战略原因,不得不如此,保证不会向鲁开仗319。但是,这封信是否曾到达绍兴,现在还不清楚。这一年的暮春,隆武帝派遣一位御史携带大量白银,去犒劳驻扎在钱塘江畔的军队。但这位御史并没有受到鲁政权的保护,终为骄兵所杀,凶手也未绳之以法320。夏初,隆武帝拘禁了一位鲁王遣闽使臣,并予处死,其可能的原因是:此人被疑为与郑芝龙勾结,图谋不轨321。
这两个朝廷都真心谋求复明,却不能合作。对这事的解释揭示了中国东南部的某种地理因素,更重要的是暴露了明朝方面的一些长期弊病。首先是地缘政治因素:几条大山脉阻碍了浙闽二省人口稠密地区的直接交通,即使在最好的时期,福州和绍兴之间也不可能有快速的通讯联络。福建虽以海上贸易闻名,对邻近省份的交通却极为不便。不过,在鲁与隆武的对抗中,不能说福建更为排他。浙东的抗清情绪特别高涨,与他处不同。在鲁政权被迫离开大陆避往海岛以后很久,该政权小小的领导核心(每人都来自“清流”重镇的浙东)比南明政权其他领导层更为团结一致,更愿献身于共同事业。要把满洲这条狼拒于门外,浙东没有丰富的物质资源以为凭借,也并不实施严密的组织纪律,确实可以依靠的只有其人民抵抗“胡虏”的同仇敌忾之气。因此,考虑到福州的地缘政治因素以及绍兴的社会心理因素,张国维之类官员不愿接受隆武阵营的号令就不足为奇了。对浙东抗清运动而言,不受隆武号令虽有危害,但在开始时,若与突然取消鲁王的合法地位相比,毕竟为害较轻。
但福建和浙江终究是大明帝国的姊妹省份。为什么现在对这一原则只是口头说说而已?简单说来,没有一个占优势的力量中心能以武力实行这一原则,不论是真用武力还是引而不发;没有这样一个力量中心,中国的政治传统对于力求彼此以敌体相待的同样合法的政权,很难给予指导。隆武帝深知,福州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另一个南京或北京。他尽量设法离开闽江流域,试图把江西、两广、湖广乃至四川的文武官员置于他的统辖之下,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由于下面所说的原因,他无法出兵北上,即使仅是越过北纬29度也不行。尽管在老百姓心目中,大明还是很有号召力,但是没有了采取军事行动以及维持秩序的能力,号召力并不能带来实际的效果。
闽浙之所以不能合作,双方君主的个性亦应考虑在内。两人都是出于个性而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各自的个性相反。考察一下两人不同的领导方式,还可以看到一个共通处,即贯彻明朝始终的辅佐皇帝问题。
鲁王体弱多病(尤其有气喘病),他的朝廷靠近为恢复明室而战的前线,但是在当时及以后数年,他决不因恐怕危及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而撤离。他的为人宁静、仁慈、温和,他的作用大体局限于循规蹈矩地主持朝仪,一切谋划决策,则放手让文武臣僚去做322。他并没有超凡的眼光、智力与领袖才能,但是与人相处时非常热情诚挚,能和跟随他的人结成亲密关系,而又不失体面。这些特点使文臣对他颇有好感,但是无助于果断的决策,也无助于控制武人。
鲁王在居于绍兴的一年中,任命了几位大学士,但是其中多数在前线各岗位,仅有一二人在鲁王身旁处理文书323。张国维肯定是大学士中最重要而且最具影响力的一人。但是他几乎未像以前的首辅那样发挥丞相的作用。与此相似,尚书、侍郎等官虽已指定,各部机构实际并未建立。总之,浙东文臣领袖精诚合作,鲁王也不专断,但是鲁政权缺乏组织结构。当来自隆武朝廷的挑战升高之际,尽管鲁王不能拒绝他的热情支持者的央求,但很难说他们达成了一致看法,也不能说在此问题上政府已有决定——显然,没有任何决定自始至终执行过。鲁王只是默许各人对此问题可凭良心行事。最后,问题堆积,内斗加剧,质疑他人是否忠心成了积怨之府,并被任意利用,以诋毁某些能臣324。
与此相对照,唐王是明季宗藩中真正与众不同之人——生活刻苦,体魄强健,精神旺盛,果决有为,受过治国之道的良好教育,关心公共事务。这些特点使他在崇祯朝成了一个惹是生非的藩王,那时他坚持鼓吹扩大宗藩在政府和国家防卫中的作用,但是现在这些同样的特点使他看来几乎是一个理想的君主。此外,他在早年曾经受过特殊的磨炼,因此足以担负复明皇帝的艰难重任。
唐王的大部分生活的确是在狱中度过的。他从3岁到28岁,与其父亲一起被监禁在唐藩王庄的私狱之内,因为其父失宠于其祖父,即当时的唐王。当朱聿键从监禁中获释,并被允准承袭其父被不正当剥夺的爵位之时,河南正受到“流寇”的威胁,北京则受到剽悍的满洲人的逼迫。他试图应付危机,在其王庄建立了防御体系,并在1636年出师“勤王”。这些举措破坏了明朝对宗藩的禁令,他于是再次入狱。这次共9年,被锢于凤阳的高墙(这是为行为不轨的宗人所设的监狱)。在这次监禁中,他受到了非人的对待,能够活下来,靠的是贤妻的自我牺牲以及河南几位有关官员的斡旋325。最后,弘光朝廷实行大赦,他才以庶人身份自凤阳高墙获释,被安置到南方远处326。他如今在福建,饱受挫折的自尊心和潜在能力似乎已在皇帝这一职务中找到了最后的表达和实行的机会。
唐王把全副精力用于如何当好皇帝,他发誓要步武太祖,把北虏驱逐出去。他把政府的不振归咎于贪酷的官吏。有几位颇得人心的福建官员,被外来人士指为贪污。他就把这些人处决了。此事可能是过于仓促了。他希望为官僚和民众树立一个清廉的榜样,衣着朴素,饮食简单,拒绝建宫殿,不准为他准备豪华的别院,宫内执役的人也很少。此外,他只有一位仍无子嗣的曾后,却拒纳任何妃嫔。曾后也受过良好教育,在内外事务上,都是皇帝信赖的最亲近顾问。不过,若是贡献有价值的书籍,他乐于接受,视同珍宝,尤其是历史和治道之书;甚至在“亲征”时,都要载运数千卷书327。
唐王相信,能拯救明朝的,正是他这位藩王,因此不能设想,他会放弃帝位,让给另一个人,尤其是这另一人是他的晚辈,又只是一个监国,而他自己则是皇帝,而且即位时间也更早。当然,为了外交和战略的原因,他致书鲁王是很客气的。但是他对“皇太侄”的态度并不宽宏大量,而且心存不良。这种态度后来更为明显,还发泄到不够机警、不知对隆武明确表示效忠的鲁王使者和其他人身上。隆武帝虽然过去一直维护宗室的利益,现在也公开保证,要为成了孤儿或流落在外的所有次一级的宗藩恢复爵禄,但是他对于和自己一样显露领袖才干的宗藩(例如在赣东北领导抗清的那些人),则小心提防,并心存轻蔑328。有一位不幸的靖江王,不知有鲁,也不知有隆武,在遥远的广西省自称监国,形同儿戏,以失败告终。此人被戴上镣铐,从桂林一路押解到福州。他的主要支持者在福州被处死,他本人也受到审讯,爵位被夺,瘐毙狱中。唐王以此儆戒其他宗藩329。
隆武帝虽对宗藩中的潜在对手心存疑惧,对其他人却大度包容,急于吸引才略之士为其服务。他授人官位时,不太蹈常规,也不太循资格。想博得一官半职的庸才,常会上一些鼓舞人心的奏疏。隆武帝易为所动,对这些人加以赏识。皇帝的这一性格,一方面使隆武政权任用的人遍及好几个省籍,因而比鲁监国政权更有全国性的规模;另一方面,则导致冗员过多,许多人不能称职330。最著之例是隆武的内阁。隆武帝总共任命30余人为大学士,虽然其中有些人没有到任,另一些人被派往战场,但是还有许多才智杰出之士伴随皇帝,无所事事。这些人之所以无所事事,在于皇帝本人处事果决,又有文学长才,亲自撰写差不多所有的诏书和晓谕,极少垂询那一群他自己搜罗来的大学士331。
这当然是人才和人力的浪费。更为可悲的是,皇帝虽然精明,还是需要一二位机敏的政治家以备顾问,也即需要类似宰相那样的人,不仅程序上应如此,制度上亦为合法。隆武帝确有许多顾问,却没有真正的顾问。他基本上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他的思想往往忽而如此,忽而又如彼,因各种可能的情况而异。因此,他的许多上谕和诏书,常常彼此牴牾,自相矛盾332。不消说,那个时代本身的特征就是动荡不安,即使是最稳健、头脑最清晰的人来担当隆武帝的角色,也不可能不感到困惑,不引起混乱。在弘光朝,谋求权势的大学士行使“体制上”所不允许的全权;在鲁与隆武朝,则是不作决策的人物来到君主身旁。不论是哪一种情况,由于明朝体制缺少宰相职务,本来就极困难的局势更为恶化了。
隆武帝在战略问题上最为反复无常。部分原因是:他一接到来自与他竞争的那些省份(浙江、江西、湖广)的消息,不论是好是坏,就感到不安,要采取行动,在没有充分权衡是否可行以前,便发布命令。但是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福建的战略地位甚为复杂;另一个是有关福建境外发生的事,很难获得迅速而准确的情报。相形之下,鲁政权的情况则颇为简单:不是敌人来,就是我们去;不是渡过钱塘江,就是越过杭州湾;而且浙西和长江三角洲(与鲁政权真正有关的仅有的两个地区)的形势发展很容易辨认清楚。但是隆武帝若要把政府所在地从福州移往易于进攻的地点,就需要长远的筹划。移徙时首先应到何处,而后又是何处,需要考虑的诸因素尽管并非不可捉摸,却也是游移不定的:从湖广到南直隶的各个战场,清军和明朝抵抗力量的相对实力,内部团结及进展情况如何;这些地区内忠明军队“迎驾”的能力怎样;鲁王政权在杭州阻拦清军的潜力,干扰隆武军队推进的潜力又如何;闽军若是长途跋涉,进入陌生地区,所需军队人数、训练程度、给养多少,以及士气情况等又怎样,诸如此类。
隆武帝的第一个目的是沿着原路返回,也就是通过仙霞关,经由江西东北部,沿钱塘江而下,收复杭州,然后从杭州进逼南京。但是有几件事立刻使这一战略的吸引力大减。他得知,在宁国、徽州地区以及这条路线西北方的天目山区,清军兵力强大,咄咄逼人333。另外,钱塘江沿岸实力最强的两位明军将帅朱大典和方国安,虽然保证既忠于鲁王也忠于隆武,却彼此憎恨,不可调和,在战事中不能指望他们的合作334。第三,尽管隆武帝提出请求,鲁王的朝廷拒不对他作正式的承认,因此后者动向难测。还有,水师总兵黄斌卿原来已受封爵,并受命大张旗鼓地进入杭州湾,与原定沿钱塘江而下的官军形成钳形攻势;现在他却在舟山群岛停了下来,不肯再前进335。一旦没有了海上策应,要向杭州或南京进攻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1645—1646年冬明军在江西和湖广抗清的胜利(见第二章),使隆武帝考虑进军“湖东”的第二个计划,也就是一旦越过仙霞关或分水关,即折向西北,在鄱阳湖东岸,与从江西南部经由赣江,以及从湖广中部经由长江而来的两支明军会合。然后这支联合的水陆部队可在南昌、九江击败或接收金声桓部,进而沿长江直下,向南京发动一场水上进攻336。
隆武帝希望尽量扩大其统治范围,对于江西、湖广各抗清首领,迅速地封官进爵。福建朝廷任命万元吉为驻吉安的南赣总督即为一例。隆武帝还派遣闽军越过仙霞关和杉关,以此尽力增援江西东北部组织薄弱的抗清力量。这次行动中执行最力、收效最大的领袖人物是监军张家玉337。此外,湖广的何腾蛟、堵胤锡以及名义上在他们手下的明军将帅,隆武帝承认其官职,并予以提升;不仅如此,大顺将帅如李锦、高一功、郝摇旗诸人,也获得了爵位、高级军衔,乃至皇帝起的名字338。部分湖广军队出境援助江西西部的抗清军,主要也是由于奉隆武帝的征召。隆武帝曾一度希望,在鄱阳湖地区进行一次协同作战,以加强三省之间目前仍脆弱的合作。但是1646年春,清军在江西采取了几次军事行动,把现存的明军抵抗力量限制在南端的赣州地区。而对何腾蛟来说,湖广局势仍很危急,也不可能考虑出省作战。
隆武帝渐渐地更为注意南赣,即赣州道。他一开始就和南赣的领袖联系密切,派遣几位最得力的官员前往南赣协调彼此的事务,并从广东方面予以援助339。当清军在江西向南扩张势力时,隆武帝愈益担心,一旦赣州也失守,进入福建(也包括自福建退出)的所有陆上通道都会被堵死。但是,他能否前往赣州,何时前往,抵达后又往何处去,都是未定之数。如果江西局势好转,他可能沿赣江而下发动攻势,以恢复明朝对江西全省的控制。他也可能以湖广的长沙为“行在”,从长沙谋取河南,准备将来进攻北京!但是另有一些人担心,赣州可能是(或看来是)退往广东的一个中间站340。
此外,随明朝的危机而来的严重社会动乱,使得穿过福建西南部甚为危险。福建、江西、广东三省交界地区,一向难以统治,如今大股盗匪再度猖獗,人数也大增。其中有些人和江西的明军领袖虚与委蛇,另一些人则对广东惠州、潮州二府以及毗邻的福建汀州府各地大肆劫掠。这类劫掠行为和汀州其他地区激烈的农民暴动有关,暴动的成因则是当地“土豪”长期来用大斗收取佃户田租以行欺诈341。1645—1646年间,各种社会抗争和目无法纪现象遍布福建全省,上述一切只是其中规模最大和最剧烈的而已。福建局势是如此不稳,隆武帝有鉴于此,既怕离开,又想离开,进退维谷。
隆武帝要考虑的情况是如此错综复杂,因此,他对自己的行动和准备采取的行动总是举棋不定。1645年9月初,他在福建登极还不久,即被劝说不要北上。而后他决意要在10月7日“出关亲征”。但是以后一再延期,直到次年1月22日才得以出征。他又在溪水上游的建宁“驻跸”,迁延观望。到了3月,才折回到靠近西南通道的延平。在这期间,他关于亲征的下一目标的种种指示中,只有一个指示是始终一贯的,即决不会再回到福州342。
福建财源有限,难以支持大规模的战事。隆武帝因此颇费踌躇。社会不安也因此加剧。隆武朝初期确曾估计到,要在1645—1646年冬为各主要关口及其他一百多个可能进入福建的通道配置足够兵力,并在来春向江西和浙东发动进攻,所需兵员为20万,所需支出为福建及两广岁入总和的两倍以上343。无论就人力还是就岁入而言,都是没法办到的。后来又有一个更冷静的估计:扼守主要关口,维持内部治安,需要4万兵力,最低限度的给养则每年要耗费86.2万两。但是一旦发动进攻,武器、盔甲、马匹、营帐、运输等开支总数就要高达156万两344。隆武帝即位伊始就指示,所有收入应当首先满足军事需要。一位官员声称,福建每年税入应当有120万两用于军费345,但是实际税入本身看来也远远达不到此数。零星的记载表明,隆武朝廷向广东、广西至少征收了16.36万两,另外有26万两则来自福建的捐助。但是当军费宣布为156万两时,隆武帝悲叹道,三省现有财源加在一起,也不能达到此数346。此外,在隆武旗号下不时向其他省派兵作战所需的费用,还不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
不消说,因不断的征税,福建经济的每一角落都被搜括到了。百姓弄得一贫如洗。一心想行仁政的隆武帝不愿正式提高基本税率,他甚至以为,受盗贼蹂躏地区的赋税非宣布蠲免不可。但是租税常常强制“预借”,人民受到高压不能不“捐助”,实际税率因而大为提高347。官职也是按级论价,与弘光朝如出一辙;官衔、功名事实上可以售予任何人,尽管这种做法受到皇帝的谴责。
于是倡优厮隶,尽列冠裳。……其黠者倩轩盖,雇仆役,拜谒官府,鞭挞里邻。……然犹苦饷不足348。
各县仓谷发充兵饷以济急。各府、县库银,乃至“恤民库”银,则成了方便的财源349。这类库存本是公共积累供备荒之用的,人民希望国家予以看管,而现在却被国家挪用。此外,最沉重的负担落在以闽江为中心、包括福州和建宁的福建“上游”地区。晚明时代,对外贸易扩展,因而这一地区,与以九龙江为中心、包括漳州的“下游”地区相比,在商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公共财富方面,差得很远。陆上运输并没有多少进展。使人员和物资能通过西北部各关口的各种设施,若要输送大军,则不堪负荷350。
不过,若要更为全面地了解隆武时期的后勤问题,必须对大学士黄道周和南安伯郑芝龙二人所起的作用与形象作一考察与比较。这两个人是隆武朝最重要的官员,他们之间的冲突以及异同之处,充分反映了明季文武之间的不协调。要使文武双方和衷共济,连皇帝本人也觉得没有指望。
16世纪末17世纪初,中日贸易蓬勃发展,尽管双方政府都予以限制。郑芝龙的早年生涯,就是在这冒险犯难、相互竞争的中日贸易中充当一名伙计及知晓多种语言的通译。他首先以巨盗著名,特别善于把手下人组织起来,号令严明,看来颇能发挥社会领袖的作用,还不时表示愿与政府当局合作。1628年,福建的明朝官员用以海盗制海盗之术,使郑芝龙投顺。其后他在明朝军事机构的卵翼下,一路升迁,像其弟鸿逵一样,官至总兵。在这几年里,他逐渐成了中国东南各港口及沿岸水域的霸主。他是那时代一位传奇人物,与其子日后的情形相似351。
隆武帝得到这样一位实力人物的支持,起初大为高兴,满怀感激之情。早在弘光朝,郑芝龙就被封为南安伯,隆武帝不久又加封他为平彝侯,以表彰他翼戴福建新朝廷之功。隆武还破格准许郑芝龙使用非正式的“勋辅”称号,表示他与大学士同列。郑芝龙是武臣,而户、兵、工三部尚书皆为文官,但是隆武帝出于上述同一心情,授芝龙以全权,处理三部有关当前军事的事务352。当时福建朝廷的事务,几乎都和军事有关,因此,虽然三部名义上由文官掌管,但事实上事务都受郑芝龙节制。郑芝龙不仅是重要的将帅,还是一个显赫家族之长,以及一个势力庞大的政治—贸易组织的首领。隆武帝因此在开始时让郑氏家族及徒党占据了大量文武职位。没有子嗣的隆武,甚至象征性地收芝龙长子、一表人才的郑森为义子,赐国姓朱,赐名成功,并以驸马体统行事,外加许多特权和职掌353。(见第四、七章)
当然,不可能人人都像隆武那样喜欢郑芝龙。文官们反对这位盗贼出身的将帅扩张势力,社会领袖则指责他常强行征收钱粮,弄得许多人甚至连正税都拒缴354。随时光的流逝,皇帝本人也对依赖郑芝龙感到后悔,甚至怀疑到他的忠诚。首先,隆武离开福州(后来是建宁)“亲征”的计划一再延迟,因为在郑氏节制之下,军事准备似乎永无完成之日355。其次,隆武帝最初曾任命郑氏组织中两名最有实力的次级领袖郑鸿逵及其族侄郑彩为前锋“左右翼”,为而后在浙江西南及江西东北的亲征扫清道路。但是这两人行动拖沓,从未远出仙霞、分水、杉诸关之外356。
三位郑氏将帅的因循与怯懦似乎与日俱增,隆武帝对此也愈感不快。这时有一位官员指出,郑氏长处在于海战,不在陆战,派遣郑氏军队深入内陆,对付精锐的清军骑兵,“是犹驱羊而御狼也”。而郑氏的海上力量是北人(指清军)无法匹敌的,因而较明智的办法是派遣这股海上力量去占领舟山、崇明各岛,并从海上攻击长江三角洲地区357。这一说法或许是正确的,不过,郑氏显然从来就不愿意使用其海上力量为隆武的大业而战。要是有谁从海上进逼南直隶,郑芝龙反而常加以破坏358。
因此,隆武帝的大愿原来是“出关”,现在仍想“出关”,但原因却变成急于摆脱福建财源的限制,摆脱郑氏的固执态度。他不能直接向郑芝龙发怒,就把怒气发泄到跟郑芝龙关系密切的那些人身上,不时粗暴对待他们。这种愤怒心情使隆武到了真假莫辨的地步,特别在处死陈谦这件事上。陈谦是鲁监国派来的最后一位使臣,郑芝龙和他一向有交情。隆武不分青红皂白,把他杀了。这类事件表明,隆武帝怀疑郑芝龙有叛逃意向,可能也是出于想当然359。
传统的历史著作对郑芝龙偏见太深,很难作出客观的评价。在一定范围内,郑芝龙的为人当然是干练狡黠,雄心勃勃,性格强悍。他当然希望,支持了隆武帝,他自己在福建的势力便能范围更广,影响更深。但是,他的海上力量来之不易,获利甚多,他显然不愿意为了使朝廷迁往另一个省而发动一场战役,把自己的力量消耗掉或牺牲掉。他未能及时把隆武的战争机器用于战场,可能确实是有困难。但是他的虚与委蛇一定另有原因,即他自己的利益和皇帝的目标在根本上不能调和。无论如何,那时的明朝皇帝严重依赖这位武人的非正规军队和半私人组织,其代价是惨重的。
隆武朝最受尊敬的文官是黄道周,他的看法和郑芝龙截然相反,但是最后两人所为都没有多少实效。他原籍闽南漳州府,在天启、崇祯二朝是东林党的领袖、“清流”大业的中流砥柱,因而很早就誉满全国。他的仕途自然并不顺利,有一段时间,甚至因敢言而入狱。但是他在闲居期间到东南的书院讲授经典与哲学,一大批文官领袖和社会领袖都是他的学生360。他在弘光朝接受了一个不重要的官职,但在1645年春借故离去。同年夏,南京陷落,他正巧在浙江。7月底,他劝唐王就监国位。其后短期内仍留滞浙江,直至8月26日才抵达福州;但抵达后立即担负了他自己所谓隆武朝“司晨鸡”的角色361。361
杭州成立短命的监国政权时,黄道周给潞王上了一道奏章,从中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一个中兴政府应是怎样的。他当时以为,南京的陷落完全是由于文官的优柔寡断,以致人民信心丧失,而不是由于各驻防地的将士不愿作战或是放松警惕。因此他建议,10天之内应采取7项行动,“使(满洲)闻之,以为圣人复出;江南父老见之,以为礼乐复兴;而后天下事事可为也”:(一)召集各地官员调查民间情况,监国并亲往杭州各处召问百姓,蠲除其苛政;(二)监国亲临郡学,赐耆老以帛、米、肉;(三)召集各郡县教官,询问考试选举事,并亲自召问其特达自著者;(四)召集南京逃回的各文武官员,询问弘光帝的确实消息,禀告先帝,并宣布祸国诸臣的罪状;(五)征集附近诸郡耆宿臣僚,听邻近各省抚按推荐叙用;(六)亲率百官阅视杭州各军,其小弁有技勇者予以赏赐,并命掌兵大僚分汛阨塞北面各要害之处362。这就是博洛军离杭州只有10天路程之时黄道周所提出的各项要务!
浙江的经验显然使黄道周增强了军务紧急之感,他在福州也就不再提及理想的圣贤举措。相反,他一抵达就上疏隆武帝,自请率军出征,耀旌旗于西北边的关外,以安定人心,不使天下人以为,朝廷将偏处福建,碌碌苟安363。此时黄道周年已60,从无带兵经验,而且也无兵可带,身边仅有4500两白银供军需之用。他抢在隆武帝亲征计划之前,于9月14日(抵达后仅两周半)离开福州,溯江而上。但是他深信,凭他在百姓中的令誉,一路上可以聚集足够的兵员和给养,或许还可能在一个月之内直接攻击南京。
臣只手赤身,无大兵重饷。又以迂阔,为此间巧佞者所轻,维陛下宽其前途,宏其刚愎,同此如水臆,共此文章灵,臣诵之起舞,感叹再四也364。
但是“识者早知时势之难,一出必不返矣”365。
犹如一幕悲剧的最初几场,黄道周的愿望多少是实现了。他从福州带出的银两,有一半以上为同情的官员所捐助,在延平、建宁与崇安,他又从予以合作的地方官员的府库中“借支”了5000余两,当地士绅则捐助了1450两。此外,他漳州家乡的亲朋子弟率当地义勇和他会合,组成了12营,约4600人。他从未自兵部(亦即郑芝龙)得到一兵一将之助,也从未自兵部得到后勤支援。他明白,他在崇安时已得到的10890两,已耗尽了这“上游”的余润,而率领这样一支军队出关,从事两个月的战事,还需要此数之半。而且当时又下着大雨,他的兵士在泥泞中行进维艰;而后他允许士兵喝暴涨的河水,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病倒,有些甚至死亡366。
黄道周有鉴于如此情形,不忍把这些未经多少训练的兵士带入更为艰险的境地。因此,当他终于推进到广信府(这是进入江西东北部、南直隶的徽州府及浙江西南部的交界处)时,只能满怀失望地在闽江上游停了下来,直到11月中旬。从该地看来,形势更为险恶。他原来寄希望于一些抗清中心,而现在不论是从这些地方传来消息还是音信杳然,都是凶兆。虽然有位史家说,黄道周在广信募集了一万余人,纯属自愿,道周又亲笔书写教谕以为赏赐,在他们看来,这比皇上诰命更为珍贵367;但是黄道周本人抱怨说,当地人既吝啬又无决心,士绅募集的奴仆和慕义者不足3000人,未经训练,装备极差。
若仅以四千病卒,半月之粮,亦未敢径趣金陵之下;若与诸达官贵人苟且夷犹,阻江自守,则臣有所不忍为也368。
黄道周于是深感力不从心,然仍希望依靠江西“穷巷孤村”的“处处团结”以及浙江忠臣义士之气。他派遣诸营进入邻近各地,并于11月底首次试图夺取婺源。他帐下只有1200人(虽然他曾告诉朝廷,这次攻势若要成功,至少需要36000人)369,与大占优势之敌几次遭遇之后,兵力愈益削弱,士兵愈益不振,终于他本人在1646年2月9日或10日被俘,4月在南京被害,一同被害的还有几位忠心的部属370。
黄道周际此艰困境地,一直哀叹,自己缺乏治军长才,和他一起救援徽州忠义之士的诸臣,也是“各贵介,不知兵,以兔搏虎,不足为怪”371。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尊重武人,经常斥责他们无能、怯懦、投机取巧。凡叙及黄道周在隆武政权中所起作用的记载,鲜有不提到下述一事的:一次,隆武帝赐宴大臣,黄道周与郑芝龙发生了争执,一个是南安伯,一个是大学士,谁应居上座,黄道周援引祖训,终于获胜372。南明这一幕戏剧以后所展现的种种场面,都有此题材。黄道周本人的话可能更为说明问题。他说,真“豪杰”投奔广信,想在他帐下投军,而他授予这些人的官职不过赞画、守把、游击;他们见此,投劄于地,说自己从朝廷取得的官职,可以高至参将或副总兵。但是黄道周考虑,这样做是否会越出他自己在疆场的职权,而且他也不愿意这些无功之人利用他处境的艰难以获取高爵373。他的这一态度表明,在南明时期,“清流”与反对职业军人这二者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虽然隆武帝坚决不想让自己的朝廷像弘光朝一样,为“清流”与“阉党”双方余孽的冲突所左右,但是他无法调和文武,也无法打破“清流”即文、“逆党”即武的想法374。
隆武帝登极初便已强调,文武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二者必须协调。他还表示,愿亲自体现文武一致,不可或缺。他一面聚集煌煌典籍,撰写琅琅上口的上谕,以炫耀自己的学问,同时又像理想的将帅一样刻苦自砺,精神焕发地尽力效法中国历史上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尤其是公元1世纪为中兴汉室而东征西讨的光武帝。但是随时间的流逝,他对武人越来越感到失望,指责他们既贪婪,又桀骜不驯375。当时,整个社会正在彻底军事化,隆武帝不幸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不顾各种艰难危险,也不顾郑芝龙的反对,坚持要在福州实行科举考试,试图以此来阻止这一社会趋势,但只是徒劳376。在南明历史中,实现文武平衡的最适当人物非隆武莫属,但是此一平衡不能仅由皇帝一人所作的姿态而达成,不论他是何等的真诚。
鲁王治下的浙东,文官领袖与武人之间也有冲突,形式略有不同,但同样严重。鲁王的军队开始时约有20余万377,成分复杂,甚难协调。文官统辖下的,有民兵、义勇以及富室支持的各营义师;在武人麾下,则是清军攻入南直隶南部后南逃或退回浙江原驻地的各支官军。文官方面的领袖是:鄞县钱肃乐,复社成员,前刑部员外郎;余姚孙嘉绩、熊汝霖,二人都是活跃的“清流”党人,一为前兵备佥事,一为前户科给事中;绍兴于颖,前知府,现任宁绍道台,曾与刘宗周紧密合作378。武人方面的领袖是:方国安,弘光朝长江中游的总兵官(现在在其辖区卵翼马士英、阮大铖);王之仁,定海水军总兵;郑遵谦,武科出身,后为军官,原来聚集在许都周围的“侠义”人物(见第一章)现在受他统辖379。1645—1646年间,清军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水上抵抗力量已逐步占了上风,此时从北方又来了原明水军残部,搅乱了上述两方面南明守军的阵脚380。但是,如果鲁王军事组织内部的问题得以解决,而不是任其恶化,清军的入侵是可以制止的。
且不说互相冲突的各人性格所引起的紧张,在战略战术方面看法也不能一致。不过,在文武双方阵营的内部都有这种情况。唯一显著的例外是熊汝霖及另外几位“清流”志士他们事先既无多少准备,也无多少协调,却一直不断地投入战斗,绝不考虑伤亡381。更为严重的是下述情况:当具有“逆党”背景的人被授命负责后勤时,“清流”中的东林党人就对他们猛烈抨击,武人领袖则予以反击,指责这些文人阻挠军事382。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件事,更具有破坏性,即“分饷分地之议”。浙东资源有限,不敷所需,此一冲突因而更为严重。
如上所述,鲁王政权的组织并不很健全;中枢亦从未设立户部,这与明朝财政和军需方面非中央集权化的一般趋势是一致的。展开军事行动所依据的是下述并不严格的原则:官军驻在哪一府,就从该府的税入得到供给;募兵、义勇来自哪一县,就依靠该县的捐助。职业军人对这样的安排特别感到不满,要求所有为战事而积聚的银钱物资由他们掌管,至少兵部手中的财物要由他们掌管,然后按战略需要进行分配。“义勇”(按:为某一大业而战即是“义”。这里所说的“义”还有一层意思:士兵所跟随的,若是与晚明政治中“清流”有关的人,亦即是“义”)领袖对此中央集权却表示反对。他们不信任武人;恐怕武人垄断一切,排挤文官领袖,将所有兵士置于官军领导之下,从而破坏浙东特有的抗清精神。他们还担心,若是自己和家乡士绅的个人联系因此切断,捐助便会枯竭,全局便会受累。有几位文官甚至建议,文官与武将的指挥彻底分开。而后的情况是:官军和义勇的各支部队互相争夺各自驻地附近府县的正供、捐助和征派,井然有序的后勤计划绝无可能实行383。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消说,要纠正鲁王政权各支部队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的局面,很少有可能。1645—1646年冬,这种无秩序状况更变为一片混乱,同时,日益严重的物资匮乏,使官兵窃取原定供应义勇的粮饷。以后鲁王军队普遍饥荒,许多“义勇”部队被遣散归里,官军则靠劫掠勒索为生384。这就是1646年春末满洲人决定继续南进时南明前线的形势。
第四章 第二次失败:清朝对东南与华南的初期征服
清军在杭州一直取守势。1645年秋,鲁王军队试图从富阳和海宁的据点推进到钱塘江以“西”,但被阻止,未能从东面或西面对杭州城形成严重威胁,或予以包围。1646年初,鲁王军队受到逼迫,战线退至杭州湾与钱塘江之间的水域(这些水域因浙江的持续干旱而变浅,淤泥充塞,颇不利防守)。但是该地区清总督接到指示,不得发起大规模攻势,原因可能在于,南直隶南部清军后方的忠明抵抗力量尚未完全荡平385。然而到了春末,太湖地区、徽州府及江西东北部的局势好转,清军发动另一次全面攻势的时机显然已趋成熟386。于是在4月13日,博洛被任命为征南大将军;6月30日,率满洲援军回杭州387。而后清军着手征服东南与华南,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7月中旬,几支清军协力一致,渡过钱塘江,攻占浙江东南部与福建之役(见地图7)于是开始。满洲人最初计划从杭州城以南的堤岸上船;但是当时钱塘江水位极低,在上游某处江水中洗澡的人发现,人、马可以轻易涉水而过,而且该处从战略上看,距绍兴并不太远。于是满洲人制订了一个分两阶段的渡江计划。7月10日,清军骑兵在桐庐附近渡江,方国安部土崩瓦解,败兵争先恐后地逃往绍兴,清军穷追不舍。7月13日,这支清军追兵在绍兴附近,同从杭州渡过钱塘江口的另一支清军按原计划会合。沿河明军悉数溃散,绍兴几乎未经抵抗便投降了388。
鲁王得知方国安部败兵蜂拥而至,就逃出了绍兴。显然,他不是惧怕败兵的破坏,就是担心落入方国安之手,成为向清军接洽投降时讨价还价的筹码。他送家人上船,前往定海,自己则迅速从陆路退往台州,希望能在该地固守。但是在台州险遭方国安手下绑架,脱险后便从海门出海,不久获得了一位水军将领的保护,此人护送他到了舟山群岛389。方国安最后被清军逼得走投无路,经不起引诱,在黄岩投降。随后,他以自己所知道的明军防御情况,引导清军血腥镇压了宿仇朱大典所领导的金华抗清力量390。不过除方国安外,鲁王的积极支持者中很少有人投降,大多数不是壮烈殉国,就是逃往四明山区或沿海地带坚持抵抗391。清军并不立即追赶鲁王及其从亡诸臣,反而从浙江的衢州和江西的广信向前推进,经仙霞关和分水关进入了福建。这两个关口在郑芝龙命令下,事先已为明军所放弃392。
隆武帝当时在延平,7月底8月初获悉了浙东所发生的紧急情况393。他虽然也派出了一些援军,但当时朝廷充满失败情绪,军队渐渐退入关内,自山区撤至沿海。他对自己军队这样的后撤都无法制止,更不用说有效增援他人了。9月4日,他作了一次重大努力来唤起其拥护者的忠贞之气:他在朝堂上拿出了截获的200多封手下官员的乞降信,然后告诫在场的人,应革面洗心,同时把这些信件都付之一炬,并不发示其中的姓名394。这次表演特别动人,使隆武更为人称颂,但是并不能阻止他的政府解体。
隆武一段时期来一直筹划往赣州“亲征”,当消息传来,敌军已进入仙霞关时,他认定,出走时机确已到来,尽管夏日的炎热持续不退,令人困倦。9月29日和30日,隆武一行,从容整齐地离开了延平,但是两天后抵达顺昌时,获悉满洲人已到延平,这一行人立刻慌作一团,不少人逃散了,另一些人则设法追随带着一小支禁军驰往汀州的皇帝。皇帝到了汀州,为清军一支前锋部队俘获,随即在10月6日与皇后一起被杀395。
10月26日和27日,清军未经抵抗,就进入了几乎已成一座空城的福州。城内凡有能力离开的居民,都逃到了乡下,随身带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棺材(这些棺材往往在实际派上用处之前多年即已预购)。因此相传有“留发不留人,留棺不留屋”之语396。郑芝龙借口对付海寇入犯,已从延平撤回。这时他毁掉了在福州的军火库,再撤到在安海的老据点。他与清朝方面接触,可能已有相当时日,但是投降条件一直未能确定。而现在清朝愿意让他出任这个地区最高文职,即闽粤总督。于是他不顾部下主要将帅的反对,也不顾他长子的泣谏,仅带了500人,于11月21日向福州的清军输诚。然而,不久他的手下人即被遣散,他本人也被带往北京“面(新)君”。而后在北京虽然居处安适,事实上却是软禁。至于其他隆武朝的文武降臣,清军从汀州和福州出发以夺取“下游”时,准许他们为进攻广东而效力,以赎前罪397。
(二)与此同时,清军征服赣州府之役进展比较缓慢。聚集在南赣的各支明军,总数已达四万余,明总督万元吉,尽管是一位热诚的爱国者,领导军务却是独断独行的,与各军将帅不能相得。而这些军队本是乌合之众,包括如下成分:明朝官军,其中多数新近自南方各省征集而来;土著募兵,来自贵州和赣东;以前的湖盗;前述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土匪。各色军队之间,因粮饷匮乏而起的争端、哗变常有发生。不过,南赣人民饱受土匪折磨,因而擅长战斗,尤其善用火器。为此,他们很容易结合成有效的自卫民团。清军面对如此情形,尽管其将帅之间颇有问题,士气也不高,但在1646年5月初拿下吉安(见第二章)之后,还是把在江西的指挥部移到了赣州城的出击范围之内,不过,并不打算马上向前推进。双方有过几次小规模战斗,但不能定全局的胜负,于是陷入了僵持状态398。
随后在万元吉领导下,吉安所发生的事重演。他照样轻侮明朝官军,为了削弱官军的地位而借助绿林力量,举措实在不智。这次他依靠的,是主要由江盗所组成的水军。这支水军原定从南安附近的上游前来救援赣州,但是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在做准备。在此期间,明朝官军斗志丧失,清军则重整了士气。最后,当这支水军船队于10月1日临近赣州时,清军来了一次夜袭,把它彻底摧毁。就赣州的指挥部而言,几个月是白等了,一切化为乌有。这次人员和物资的损失是如此巨大,上游清军的力量又是如此强大,大部分明朝官军惊慌了。而且他们对万元吉的态度傲慢及举措乖方深感厌恶,不久纷纷逃离南赣。万元吉对这些人也同样感到厌恶,见此结果甚至说摆脱他们是好事。他随后把未逃离的官军也遣散了,发誓要率领仅剩的五六千人死守赣州城399。
到1646年11月初,赣州城已坚守了6个月,城内开始精疲力尽了。11月9日夜,一名降卒带领清军越过城墙,次日城陷。总督万元吉,以及隆武朝兵部尚书杨廷麟和吏部尚书郭维经自尽。全城居民不是被杀,就是没入为奴,明朝文臣有一百余人丧生,而未战死的武将全部投降400。
(三)清朝开始了对广东的初期占领。入侵分两路进行:一路自福建最南端的诏安出发,另一路自梅关外的南安府沿江西与广东东北部的边界前进。要说明他们后来的行动,首先必须对两广的忠明之士在此之前的活动有所了解。
1645年,弘光帝死讯传到岭南,许多官员属意朱。(指瑕:1645年弘光帝被俘,押往北京,但一时保住了性命,并未有被杀之讯传出。次年,弘光帝才被清廷以谋反的拙劣借口杀害。)他是新近去世的桂王常瀛的长子,按出生讲,福王之后应由他入承大统。1643年,张献忠侵入湖广南部,由与其父常瀛逃离衡州王庄,到广西梧州避难,1644年常瀛死于其地。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以为,唐王是一个骄横的暴发户,他的称帝打乱了帝位继承原则;但是他们承认,唐王当皇帝已是既成事实。此外,由袭封桂王之后不久即去世,于是常瀛的后嗣中仅剩幼子永明王由榔。在他22岁的生涯中,大部分时间养尊处优,不为人知。张献忠叛军蜂拥而至,他才陷入悽惶恐怖之中,先逃亡,后被掳,还被威胁要处死。他好不容易才从湖广西南部逃入广西,随后得到了两广总督丁魁楚的保护,住在广东的总督衙门。现在,由于他兄长一辈的迅速凋谢零落,这位永明王忽然成了万历帝唯一嫡孙,依照世系,此时明朝皇帝应由他做401。
福建传来不祥的消息时,两广官员已在试探永明王是否愿意即皇帝位,但是他的母亲王氏坚决拒绝。王氏未育,是常瀛诸妻妾中硕果仅存者,因而常瀛唯一活着的儿子之事,现在就由她掌管。她反对的理由是:永明王太年轻,没有经验,性格柔弱,在此混乱时期不足以担当大任,而且现在广东缺乏足够的官员,甚至一支像样的军队也没有,怎能建立朝廷并加以保卫。这些看法事后证明相当正确402。但隆武帝已死的确讯传来时,事情就迫在眉睫了。瞿式耜与丁魁楚强调明朝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终于说动永明王在肇庆称监国。瞿、丁二人成了新朝廷的大学士,总督何腾蛟、湖广巡抚堵胤锡诸人授予各部尚书、侍郎之职,西南各省数十名将帅则分别担任军事机构中各种职务,得将军印信,并获封爵403。但是除此之外,当时的政府并未采取任何行动。
广东大部分组织良好的军队,已派去协助防守南赣,剩下的只是一些经常哗变的小股地方部队,用以对付多如牛毛的土寇、海盗(有时就和他们沆瀣一气)。1644年北京陷落后,这些盗贼在广东愈益猖獗。因此,当11月底肇庆得知,南赣的抗清志士已为清军的优势所压倒时,这位监国新君及其家人自然感到不安全,于是在11月24日离开肇庆,西往梧州。他们觉得,梧州远离清军威胁,距广西的可靠部队也较近404。他们没有料到,来自明朝方面的另一个威胁正在临近,这是地方势力与隆武朝残余联手的顽固坚持独立的力量。
此时,曾直接在隆武帝手下任职的一批文臣陆续抵达广东省城广州附近,其中最著名的三位大学士,都是广州府人。这批文臣中有几位曾与拥护永明王的人有过接触,但是对永明集团很是冷漠。其中有些人感到被永明集团轻视、排斥,以及觉得肇庆从未与广州方面磋商。另一些人则因为感到,新朝廷最令人艳羡的职位,自己已没有份;或许还由于肇庆的领袖人物对隆武帝及其朝廷心存偏见。这些文臣以及在广州的其他人,对新监国没有信心,尤其是在危险刚一出现他就轻易放弃广东之后405。总之,隆武帝之弟朱聿(隆武出发“亲征”时,他曾在福州为监国,执掌朝政)于12月5日自海路抵达广州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被寄予厚望。7天之后,他在广州接皇帝位,年号绍武依据的是兄终弟及之制。首辅苏观生及其他要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广州人406。
梧州的监国党不久就获悉广州集团的活动,但起初并不知道登极典礼已经举行。因此,梧州方面决定,永明王应立即返回肇庆,赶在朱聿有任何动作之前即皇帝位,希望因永明所任诸臣声望更高、基础更广而对民众更具吸引力,使民众最终只效忠于永明朝廷。于是1646年12月14日在肇庆,永明监国成了永历皇帝。然后,永历帝得知绍武亦已登极,便匆忙建立防御,准备阻挡来自广州的攻击407。永历朝廷曾试图与对方谈判,但是使臣被苏观生处死,此一尝试不幸终止,于是双方的武装冲突不可避免了。绍武军队主要由山寇、河盗所组成,这些人虽被劝诱在官军旗号下作战,仍是不可信赖的。尽管如此,绍武军力还是较永历方面为强。因此,1647年1月初双方在广州三角洲地区交战两次,结果是永历舰队几乎全军覆灭408。
双方朝廷将注意力集中于自相残杀,耗竭了宝贵的军事力量,共同敌人却置之不顾。这一形势,固然更为短视,更多怨毒,但与以前鲁与隆武的互相雄长并无明显的不同。在这两种情况下所见到的,不仅是众多藩王转徙各地所引起的后果,另外还有一件事,即全国政府各机构摇摇欲坠之际,依赖地方上的团结是何等的重要。总之,这就是1647年1月中旬清军开始侵入广东时该省中部地区的形势。(阅读下文时,请参看地图8、9)
1月20日,绍武帝正在庆贺击败永历军的胜利。突然间,一小支清军骑兵攻入广州城,城内惊慌失措,只有零星的抵抗。清军一路上经过潮州、惠州二府,绍武领导层毫无觉察。首先,清军利用缴获的粤东各府官员印信,发布一切平安的假消息;另一原因是,确实试图警告苏观生的信使,被怀疑为肇庆派来的间谍,予以处死。此外,清军最后逼近时,被当成只是花山的绿林,而这些桀骜不驯的江湖人马现在则是绍武朝的盟军。这时再要抵抗已不可能,于是苏观生自尽,他的大多数同僚却投降了。绍武帝想逃走,但被俘获,随后因拒不合作而被处死。聚集在广州的大批藩王亦因不合作而被杀409。
此一大难的消息传到肇庆时,永历朝廷起初根本不相信——这肯定是绍武集团为瓦解永历阵营而设的骗局。但是接二连三的报告驱除了这种错觉,1月下旬,永历帝慌忙放弃肇庆,2月5日,再度抵达梧州410,不久又从梧州抵达桂林。他这种只是模糊感到危险就仓惶逃走的做法树立了一个榜样,在相当长时期内,使西南各省的抗清事业得不到基层社会真正的支持,并在一开始就永远疏离了广东的百姓。
辽东汉人纪律严明,忠心耿耿,早就认同于清朝。自从清军入关以来,明军将帅已率领了大批军队投降,这些士兵不大可靠,纪律也差。清军能如此迅速占领广州,正是这两种因素结合的典型。这次战役,辽东汉人由佟养甲率领。他生于满洲人统治时期,曾在皇太极和顺治两朝入直内廷理事,最近又协助博洛征服浙江和福建411。明朝降兵由上文提到的李成栋率领。他为清朝血腥镇压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反抗,而后又随军出征,一路通过福建。
广州占领之后,佟养甲仅率领数百人留守。李成栋继续出击,轻易夺取了粤西各据点的战略枢纽肇庆,再从肇庆分兵三路:第一路沿北江而上,与自赣州南下的另一支清军会合;第二路向南穿过雷州半岛,很容易就到达广东西南端,然后渡海占领海南岛;第三路沿西江而上,一路追赶永历帝一行,直至梧州,3月5日李成栋本人率大军亦抵达梧州。虽然他奉命不要越过梧州,但还是派出搜索部队进入广西中部,更为重要的是,还派军向西北逼近桂林。4月15日,一小支清军突袭桂林,险些把它攻占412。
清军征服各地,每次在初期总是进展过甚。佟养甲与李成栋以惊人速度攻陷广东全省和广西的一半,正是一个显例。许多明军将帅不抵抗就投降了。明朝政府的正式的物化装饰,如官印、衙门、城墙、岗哨等,也轻易被夺取;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这些东西对明朝而言已失去其效用了。佟养甲最初对于自己的军队如此顺利地建立表面的控制颇为得意。但是他不久就发现,正如其他地方的清朝官员所遇到的情况一样,在业已占领的各衙门以外,要恢复社会秩序绝不容易。特别是各种破坏性因素,与明朝忠臣义士相结合以抵抗入侵者,从而披上了合法外衣之时,事情尤其如此。许多乡里社会为了保卫自己,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杀死一切来犯的人,满人、北兵、抗清民团、明朝官军、土匪、海盗,不管是谁,一概格杀勿论。佟养甲很快认识到,要使广东真有安定,就必须恢复自广州往北经由湖广、江西直达长江流域的贸易通道,使现在以打家劫舍为生的大量难以抚绥的广东人重新获得正当的谋生手段。但在这方面,他手下没有足够的人来全面完成这一任务413。
(四)清军对湖广南部的挺进还在持续,但也遇到同样的挫折。湖广的清军统帅所要猎获的目标跟广西东部的李成栋一样,也是自称明朝皇帝的人。李成栋是功亏一篑,湖广方面更是眼看猎获物就要到手,终于失去。
桂林是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瞿式耜的总部所在地,永历帝一行不愿在此坚持抵抗,转徙到了广西、湖广之间的主要隘口全州。他们在全州惊魂稍定,考虑到哪一省最为安全414。6月27日,清军第二次进攻桂林,却大出意料,为瞿式耜及总兵焦琏所击退,但此时永历帝已到了湖广西南深山中的武冈,依靠当地明将刘承胤。岷王封于该地,1643年,当地民众发动了反岷王的起义,为刘承胤所镇压。从此他的势力壮大,现在则自命为明朝帝室的特别保护者415。
从此以后永历朝廷被一个又一个的野心武人所控制,现在只是这一慢性病态的开始。此外,永历帝也显示了一种双重性格,那也是永历朝自始至终的性格。一方面,他不喜欢瞿式耜等正直文人的主张。这些人勇往直前,目光远大,对战略形势有乐观的估计,以为只要打出皇帝旗号,人民就会挺身而起,坚持抵抗,前景是看好的。而永历帝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人很容易把他置于危险的境地。另一方面,任何武人,只要看来能为他及其家人提供人身安全的保障,他就会感激,愿受保护,但这些人无一例外地会对他施加诸种限制,这又使他恼怒。
长期以来,湖广的明军将领往往不完全接受总督何腾蛟的节制(见第二章),刘承胤是其中最桀骜不驯的一个。他是多数军人对他们在晚明所处地位不满的一个标本。多年以来,凡有官员来往于湖广与西南诸省地区,他都予以款待。他虽目不识丁,却通晓礼义,举止得体,谈吐带有书卷气。来往官员都对此印象深刻。此外,他虽人称“铁棍”,喜欢率大军打硬仗,对于玉器、绸缎之类物品却也有雅兴。现在,永历帝一行已入于他的掌握之中。他
尝于所亲问曰:“何为九锡?”又尝指冠翅,竖其二指曰:“如此便好了。”又尝曰:“国公亦不好。只带个五品衔,死也甘心。”谓东阁大学士也。
他自己虽然没有弄到手,却对皇帝施加压力,要将此职授予他心目中的人。于是一位来自他家乡贵州的老朋友就当上了东阁大学士。这人和他有共同看法,即长期以来西南各省将帅的功绩根本未获重视416。
刘承胤在武冈实际上已将皇室置于严密监视之下,凡不属刘氏集团的官员,都不能和皇室成员接触。于是永历帝不得不向驻在湖南某地的何腾蛟及驻在桂林的瞿式耜秘密求援,但是何、瞿二人亟需防范清军自南北二方发起进攻,而且对于名义上在他们麾下的明军将帅也不能有效控制,当然无法对刘承胤在武冈的地位进行挑战417。因此,永历帝最后从这种监管处境获得解脱,靠的不是明军,而是清军。
清军对湖南的进攻由孔有德指挥,开始于岳州,自从1647年3月中旬以来,一直没有遇到多少有组织的抵抗,跟广东的情况如出一辙。原因是,清军大队人马逼近时,各自为政的明军大都已溃散了。因此,堵胤锡及其统辖下的前大顺军被逐向西北,逃入了长江出川后那段流域的崎岖山地,而何腾蛟和章旷被迫溯湘江而上,退到永州府(位于通往全州和桂林的航道上)。章旷后来因胃出血死于永州418。同时,孔有德接连攻陷长沙、湘潭、衡州,一路前进,直指广西,而后是广东,以求完成清军对整个华南的两路攻势。但是孔有德和何腾蛟一样,也发现湖广形势复杂,令人丧气:半独立的武人朝三暮四,粮饷又严重匮乏。凡此种种,使明朝方面大感苦恼,同样也使孔有德受阻。等到孔有德得知永历帝现在何处,已是9月中旬;直到那时,他才能率军穿过宝庆,攻向武冈419。
刘承胤和清军,为争夺武冈外围防御工事打了一仗,几天之后,清军的胜利看来迫在眉睫,他就准备投降了。于是在9月23日,默许永历帝及其家人逃跑,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永历帝便带着一小批人拼命奔逃,一路上随行人数迅速减少。他们向西南方迂回逃去,通过山区的土司辖地,备尝艰难困苦,还受到土司和逃兵的骚扰,直到11月才抵达广西中部的柳州420。永历帝在该地与大批明朝官员会合,并得到了一位勋臣陈邦傅的保护。几个月来,从广东过来的清军已被逐出广西东部,陈邦傅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然后大家决定,两位皇太后、皇后以及皇室其他女眷应再往西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南宁去。皇帝则接受了瞿式耜亲临前线、鼓舞将士的请求,于12月30日到桂林421。
9个月来,永历帝长途跋涉,备受惊吓,兜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处。几支明军从湖南败回,在广西东北角挤在一起,于是就产生了许多“主”“客”之间的摩擦。因此,当1648年3月,衡州清军统帅重新开始向西南挺进时,防守从全州到衡州一段狭长地带的明军将帅互不合作,桂林被前大顺将领郝摇旗的部队劫掠一空,郝摇旗更挟永历帝退回广西中部。于是皇帝在南宁与家人再度团聚,拯救桂林之责再次留给了瞿式耜。4月14日,他成功地击退了清军对桂林的第三次进攻,而后得何腾蛟之助,把战线拉得太长的清军进攻部队逐出广西东北部,赶回湖广腹地,又一次创造了奇迹422。于是形势转而对清军不利,以上所说是这一大转折的一部分。更为全面的讨论见第五章。
清军入侵华南和东南,抵抗最烈的有两个地区:东南沿海和广东中部。忠明之士的公开活动,在最东南端和西南之间开始一分为二。虽然他们几次设法把两地联系起来,但并没有取得有实际意义的效果。在清军压力之下,两地的抗清中心逐渐愈离愈远。虽然许多不愿屈服的鲁与隆武的官员,已逃入了浙东与福建的遥远山区,但幸存者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人走遍沿海地区,寻求既统陆军又辖水军的各将帅的协助。张名振是浙江沿海这类将帅中最强的一位,他以石浦和南田为据点423。在福建沿海,这类人则为现已分崩离析的郑芝龙集团的统兵者,大多数是他的家人亲戚,但也包括周鹤芝之类部属424。其根据地是泉州与漳州之间的沿海地区,包括厦门与金门各岛。沿海的武装力量不止于此,还有大量海盗。事实上,这些统兵将帅及其部属中,有许多人早年都是海盗。现在,浙江和福建朝政府解体,沿海形势因而更为不稳,这些武人之间的竞争也更为普遍,互相争夺好水手、安全的基地、贸易的便利、粮食、燃料及作战物资的可靠来源。无可否认,其中有些人确是对明朝赤胆忠心,但是沿海方兴未艾的军阀割据倾向,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鲁王的海上抗清活动,而且这种军阀倾向与拥护鲁王的士大夫的理想主义,虽已结合,却颇勉强。
湖广的何腾蛟试图重建统一指挥,但湖南边缘山区半独立的明军将帅从中作梗,使他的计划受挫。在东南沿海,日渐壮大的各土皇帝也在做同样的事,最显著的例子是黄斌卿。1645年,隆武帝命令他协调杭州湾地区的反攻作战,此时他已认真着手在舟山岛建立一个货真价实的私人属地。然后,他虽与其他明水军将帅有所协力,但处处提防,只有于自己有利或于对手不利时才予以合作。不久他就博得了这样的名声:宁愿削弱、制服,乃至消灭同类,而不愿攻击清军425。
有两件事都与黄斌卿有关,充分说明了两类人物利害关系的不同。一类人想在沿海岛屿营建窟穴,如有可能,最好在明朝的庇护之下。另一类人是明朝忠臣,需要水军的支持以恢复明朝对沿海主要城市的控制。第一件事发生在1647年春,当时苏州东南松江的清水军总兵吴胜兆计划归顺明朝。苏州地区的各城市及众多的湖泊水道,都有地下复明运动。有些人所共知与地下运动关系密切的人,长期以来被吴胜兆收容在他的部队中。现在吴胜兆图谋叛清,黄斌卿因而受命提供水上外援,成全吴的行动。他表示拒绝,于是这一任务落到了张名振一人肩上。不幸的是,当张名振的船队于5月中旬抵达崇明水道时,忽遇飓风,船只飘散,因缺乏后续舰队支援,受到沿岸清守军的攻击后,几乎全军覆没。吴胜兆营内“清流”志士的领袖,与营中更为谨慎的官军将领一向有抵触。现在水军虽已失利,这些“清流”领袖却并不想把原计划搁置起来,依然策划在5月20日发动兵变,但未成功426。
煽动反清的,有三方面的人:“湖寇”、苏松将士中的通敌者、沿海忠于鲁王的人士。清朝方面采取了特别措施,打破了这三方面的结合,随后又清除文武两方面的谋叛者,诛戮甚广。同年12月,黄斌卿勉强同意参加一项计划,以倾覆附近宁波城内的清朝统治。他命舰队溯甬江而上,等待忠明之士的行动。但因事机不密(这是典型的一例),“清流”密谋者被人向清朝当局告密。黄斌卿不愿首先采取行动,也不愿在不利条件下作战,又撤回到海上427。这两次事件之后,他再也没有卷入到攻击大陆的行动中去。
黄斌卿的为人既是如此,当1646年夏末鲁王从台州逃入海时,他不允许鲁王在舟山重建监国朝廷,也就毫不足怪了。鲁王的船队因此只能在舟山周围各小岛寻找临时避难所。直到这年冬天,郑彩来到,才把鲁王护送到略为安全的郑氏在福建的基地428。
虽然清朝对郑芝龙食言,并把他调离福建,不过还没有破坏郑氏家族在安平的老家。这样做,和清朝对投降的要人给予礼遇的原则是一致的。但是清朝也感到,只要郑芝龙还活着,并与清朝合作,就有可能通过他使郑氏其他人投降,从而无须对他们进行讨伐。这样的讨伐将会旷日持久,开支浩大,而且胜负也难料。因此,在隆武政权覆灭后的一段时间内,郑氏依然能在大陆沿海泉州、漳州一带保持强有力的地位,也能在厦门和金门发展根据地,同时家族内新的领导体制也形成了。接替家长郑芝龙来有效领导这个业已不稳定的郑氏集团的,有三个主要候选者:年长的郑鸿逵和郑彩,还有刚满22岁的郑成功。
郑成功和隆武帝有特别亲密的私人关系(见第三章),因此他一度象征性地继续使用隆武年号。因为他死去的君父过去不承认鲁王的监国地位,所以他现在也不承认,将来也不愿承认。另一方面,郑彩似乎希望在鲁王朝廷扮演一个角色,同郑芝龙以前在隆武朝的角色相仿,亦即充当皇帝的主要资助者和保护者,同时也充当皇帝威权的主要分享者。总之,1646年12月,监国鲁王被带到了在厦门的中左所。郑彩虽然未与其族侄作战,但两人间互相竞争,因此郑成功更有理由不理睬这位监国。不过,他终究不能和他那族中长辈决绝,因此他不想把监国驱逐出去429。
1647年春、夏,郑彩支援其族人对漳州和泉州的清军据点进行首次攻击;他还和周鹤芝等人一起从厦门北征,特别集中攻击福州府各战略要点。9月,鲁王本人也已迁到了长垣群岛(按:长垣为群岛名,其中最大的岛即今日的马祖。参看盛成《沈光文〉一文51—52页),以激励夺得闽安的文臣武将。该地是扼守福州出海水道的要塞。在鲁王旗帜下,福州周围的全部民众确实都动员起来了,福州城则在包围之下陷于饥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次年夏清军增援部队抵达之时430。从这时起,鲁王军队出福州府向西北,转战进入了浙江;同时,郑成功从泉州府往西南,攻入了广东的最东端。
只要鲁王政权还存在,双方的这种分离就一直存在。这不应看作是过去鲁与隆武两个朝廷对抗的继续。郑成功始终拒不承认鲁王为监国,在前隆武诸臣中是一个异数。聚集在鲁王麾下的诸人中,有许多曾出仕隆武朝,原籍福建,或曾在福建为官431。因此,这一分裂其实是存在于新的鲁王政权与经过重组、最终为郑成功所控制的郑氏集团之间。更为重要的是,分裂双方中的一方仍然为士大夫与武人间的仇恨所困扰;而在另一方,这不再成为问题。
11月,鲁王在长垣再次广泛任命大学士、尚书、都御史等,以重建表面像样的合法朝廷。昔日的鲁与隆武诸臣和衷共济,通力合作;继福州旗开得胜之后,在福州东北的福宁府再度获胜,朝廷士气颇为昂扬。(有关这一点及以后的讨论,参看地图10。)鲁王在沿海的进攻,得到了福建山区忠明之士的纷纷响应,更是令人鼓舞。1647年八九月之交,建宁发生暴动,反击清军,不久扩展到福建北部中央区域几乎每一个县432。不过,鲁王政权虽已收复部分沿海地区,却无法巩固对这些地方的控制,也无法与内地抗清运动取得联络,实行合作。部分原因是:普遍缺乏兵力,及一直太过依赖水军力量。另一原因则是:闽西民众抗清运动,多半是由佃农、契约奴、运输工人、矿工、铁匠,乃至无所不在的土寇所发动;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上层阶级控制,不论是明朝、清朝,还是其他什么政权433。此外,当时鲁王政权的主要武人领袖是郑彩,而朝中那些有士大夫背景的人,又像在浙东时一样,想出来掌管军务,于是双方的敌意日益增加。因此,鲁王政权对明朝忠臣义士的活动,就很难作有效的指导。
举例来说,为明朝收复福建东北部最有功的一人,是原籍福宁的前隆武朝兵科给事中刘中藻。他与郑彩的不和,起因于下面的一件事:大批已降清的士兵又投向鲁王的官员,希望重新加入明军。刘中藻认为这些人是叛贼,立即把他们处死;但郑彩坚决反对杀降,因而痛恨中藻此举(另一原因是,他自己派去联络的人,也有一个被杀)。后来刘中藻在福宁得不到所需的支援,孤立无助,终于在1649年春战败后自杀。他败亡的部分原因,正在于与郑彩的怨恨434。此外,鲁监国政权的两大支柱是来自浙东的熊汝霖与郑遵谦,一人与郑彩联姻,一人与他互攀宗亲,想以此来加强团结;不过后来双方还是逐渐有了冲突。熊汝霖指责郑彩任命自己手下人(而不是御史)为监军;而且他还是像在浙江时一样,让下属恣意攻击,而不是服从军务与战略的大政方针。郑遵谦则背叛其“同姓兄”郑彩,侵吞他的粮饷,挟着他的两艘满载货物的商船潜逃(所依据的理由可能是:所有物资都是为共同事业服务的)。因此,到了1648年2月,郑彩有理由认为,熊汝霖、郑遵谦二人正在共谋陷害他。熊汝霖死于几个歹徒之手,郑遵谦则被禁闭在船上,因而自杀;这些都可能是郑彩在暗中策划的435。
熊、郑二人之死极大地震撼了鲁王政权的领导层,随后是几个重要人物的出走,其中有大学士钱肃乐436。
至此而风虎云龙之想,竟转而为珠沉玉碎之悲。
只有一小部分大臣留下来伴随监国437。大部分由于这个原因,鲁王政权在闽北所收复的3府27县,其中大部分自1648年暮春起又被清军夺回,一年之后,甚至福宁的几个最坚固据点也投降了438。在此情况下,郑彩对扶助鲁王政权失去了兴趣。他回到厦门,希望和郑成功重修旧好。鲁王则留滞海崖,处境艰险,直到上次护送他出海的忠诚不懈的浙江水军总兵张名振再度前来救援,才脱离困境。1649年7月,张名振为明朝收复了海岸前哨健跳所,使鲁王得以在该地重建朝廷439。于是鲁王抗清事业新一轮的浙江时期开始了。
在浙江,同情复明大业的情绪依然高涨,健跳所的鲁监国朝廷,正巧位于两个能提供最好军事支援的地区之间:西面是四明山和天台山,东面是舟山群岛。在这两个地区正中间的,是南田附近张名振的根据地。他本来大可以有效协调山区的忠明部队和海岛的水军,从而把鲁王控制区域扩大到浙江东南部。但是他未能如此做,反而让清军把这两方面分隔开,各个击破。个中原因,不仅在于浙江的清朝官员颇有能耐,也相当顽强;与文武冲突更有关系的是,张名振无法使自己的领导权获得充分承认,尽管他对于明朝抗清大业的贡献,是毋庸质疑的440。
张名振,和在他之前政治地位显赫的南明将帅一样,也受到诸文臣,尤其是“清流”人物的批评,被指为逾越职权,视官位作私产,这些人还指责他无视固有的资格,声称被他授予高位的人,善于夸耀自己所作所为在政治上何等重要,而究其实,只是利己;至于公而忘私,效力朝廷,却实在乏善可陈441。此外,义勇与官军指挥部之间的老摩擦,又再度出现。
四明山寨的守将中,力量最强、办事最认真的是王翊。这位武人既有魄力,又极自信,通过“游侠”与“清流”之间的典型联姻,和不屈不挠的抗清领袖、复社志士冯京第一直合作无间442。这些人虽在1648年春因清军攻势而受挫,但还是重建了抗清运动,四明县郊及其邻近的所有农村地区又一次完全落入了他们之手。但是鲁王抵达健跳所之后,王翊却迟迟不接受鲁王朝廷的武职,因为他若接受,就会屈居于张名振等人之下443。因此,鲁王朝廷和各山寨守将之间就不能建立起作战上的联系。此外,各寨将的作战能力还受到冯京第领导方式的限制,他“自负经济,然欲以承平体统待其士卒,雅不为人所亲附,故往往致败”。444
在海岛方面,张名振愈来愈为沿海地区逐渐滋长的军阀倾向所困扰。军阀作风的最明显例子是舟山的黄斌卿。张、黄二家有亲戚关系,为此之故,张名振被允在黄斌卿辖区附近保持基地,进行活动;但是,甚至在健跳所饥馑愈趋严重时,张名振还是无法使黄斌卿接济粮食,更不用说使他在军事上支持鲁王的事业了。因此,张名振也采取了军阀式的反击手法,联合了对黄斌卿心怀不满的其他几位水军总兵(还有海盗),以推翻黄斌卿,夺取舟山,让鲁王朝廷有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可去。1649年10月29日,黄斌卿战败,在舟山自尽;11月,鲁王朝廷移到了舟山445。鲁王一行原在大陆局促一隅,受清军逼迫及饥馑交困,现在这一切都解脱了,但从此以后,这个朝廷就完全处于守势了,所关心只是如何苟延岁月。
清军的战略是,一方面建立自己的远海舰队,以海门、定海(按:当时的定海为今日的镇海,舟山岛上的舟山城则是今天的定海)、崇明为基地;另一方面则有条不紊地镇压钱塘江东西两岸各山寨守军。1650年10月,清军对四明山区的抗清武装发动了一次协调一致的攻击,摧毁了王翊的组织,使王翊和冯京第二人从此流窜各地446。然后在1651年3月,张名振刺杀了一个和他共谋倾覆黄斌卿的总兵;于是又像南明军队中一再发生过的那样,牢骚满腹的部属投向了清朝,提供有关舟山的情报。因此,到了秋天,清军已略有把握,准备进攻舟山,尤其是捕获了王翊并在定海军阵前把他处决以鼓舞士气之后447。
10月4日至15日,清军向舟山发动攻势,原定三路同时进攻。南路军从海门出发,北路军从吴淞出发,一路上都遇到抵抗,不是被击退,就是受阻448。因此,进攻任务由定海出发的一支清军单独承担。多半由于凑巧,明朝方面最勇敢的将领冷不防被这支清军发现,他的舰队在舟山与大陆间的海上通道被摧毁,他本人也阵亡。当清军开始包围顽强防守的舟山城时,鲁王和张名振同在出海的船上。10天后,舟山城墙终于被炮火攻破,城内与附近的鲁王亲属及百官全部壮烈殉难,其中有许多自焚身亡449。
张名振于是带着鲁王沿海岸线往南,随行的还有几位鲁王朝臣中的幸存者。大约在1652年1月,这一行人抵达了厦门的郑成功大本营。自从鲁王上次到中左所以来已有6年,郑成功的势力在这些年内稳步扩大,而跟随鲁王的文臣现在几乎全部殉难,支持他的武人也实力大减,因而很愿意以郑成功为最高统帅,实行合并。在这段时间,郑成功亦已与两广的永历朝廷建立了联系,永历朝授予他一个武职勋衔。此后他得到了一连串这样的勋衔而且愈授愈高。1648年秋,郑成功更将所奉的年号由隆武改为永历450。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可能郑成功(或朱成功,因已被隆武帝赐姓朱)接待朱以海尽管优礼有加,却不是把他看作鲁监国,而是看作明朝宗室前辈的鲁王。总之,这位藩王被郑成功安置在附近的金门岛上。1653年初,他放弃了监国称号451。
因此,复明大业虽已在浙江东南部遭到严重打击,沿海的抗清运动却以两种方式形成了新的统一。首先,鲁王与郑成功之间的分裂已获解决,现在所有的忠明之士已在同一旗帜下作战。其次,沿海抗清运动中的明朝文臣集团实际上已被消灭。残存的少数几位坚定的士大夫,也像郑成功一样,接受了永历朝廷的虚衔。不过,他们现在若想有效做事,就必须在郑成功的组织机构内服务。此一组织完全是郑氏私人的,而且是彻底军事性质的(尽管有其商业的一方面)。因此,在此一特殊地域,明朝方面长期以来的文武之间的分歧消失了,辅佐皇帝问题也消失了。(有关这两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第六章。)
郑成功在幼年曾受过良好的经、史、文学的传统教育。但是时代已不允许他沿着科举考试的途径进入士大夫行列。清军侵入福建以后,他毅然弃文习武,全副精神用于建立及操纵一架军事机器452。随后他成了郑氏集团无可争辩的领袖,此一过程分如下三个阶段:(一)1646年初,他在厦门诸岛中的一个小岛上着手训练他的核心部队,开始时仅有数百人,不久从较大的南澳岛招募到数千人。1647—1648年,他率领这些部队,与诸从父及其他族中长辈攻击漳州和泉州的清军据点,从而首次获得了海陆两栖作战的经验。1647年春,清军为此采取了第一次报复行动。郑氏家族在安平的根据地受到袭击,成功母自尽,其子因而与清朝结下不共戴天之仇453。(二)1648—1649年,福建发生饥荒,迫使郑成功攻入广东潮州府,主要目的是获取粮食,同时也想利用潮州的混乱形势,因为当地数十名土豪、寨将已是“不清不明”454。他以后经常采用的作战方式,主要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形成的。经过这次战役,他的地位增强了,终于能在1650年9月回到厦门,并从其长辈手中夺取了控制权455。(三)次年春,他亲自率军援助广东中部的永历朝廷。这次战役,即便并未增强他的战斗力,至少使他的威望提高了。他的舰队在广东东部沿海,就像在别处常遇到的一样,碰上了恶劣天气,无法完成其任务456。更坏的是,清军利用郑成功不在闽南的机会袭击厦门,造成极大破坏,成功临行时留下两位叔父防守厦门,但二人作战不力,未能有效反击清军。1651年5月,成功回到厦门,大怒,立即将一位叔父斩首。另一位叔父郑鸿逵则被迫交出兵权,辞去职务457。在此情况下,新的统一从逆境中产生了。尤其是次年冬郑成功收编了鲁王的残余军队之后,更能随心所欲,放手指挥东南沿海的抗清运动了。清朝自认为已征服福建,殊不知此以后这位27岁的英雄却要给他们造成大量的麻烦。
如前所述,当明朝失去北方时,没有能够依靠组织良好的南方军队。现在沿海各省又遭受入侵,明朝若想依靠组织良好的水军,更没有什么希望,因为明朝自早期以来,大体上从不重视海洋。水军将领招募海盗商人,与他们联合,其所作所为和他们也没有什么两样。这并非只因明末对沿海的统治削弱而起。水军将帅中许多人(郑芝龙仅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而已),原来都是海盗商人,一直保有其旧日的联系,也一直未脱海盗习气。即使并非海盗出身者,为了不遭淘汰,也不得不去实地学习,以应付风涛险恶、竞争剧烈的海上环境。他们全都熟悉获利丰厚的海上贸易。当时这种贸易在澳门、马尼拉、长崎等口岸颇为兴盛,一路上要停靠台湾和琉球群岛各站,然后沿曲折的中国东南海岸线航行——尽管中国官方规定,在朝贡制度之外,不准与日本有贸易往来,而日本不参加朝贡贸易已有百年之久458。
日本一向需要并向往中国货物,而明朝政府一直不准与日本自由贸易。当时东亚的海上贸易,普遍具有海盗与走私性质,海盗中也颇有日本人。这些事肯定与上述日中贸易的情况有很大关系。此外,在16世纪末与17世纪初的日本,战国时代临近结束,德川幕府正在建立,兼并战争为其时代特征。这些战争使一些日本浪人(无主武士)和其他自由武士进入了东亚的商船队459。于是日本武士以其骁勇善战在沿海地区家喻户晓,即使是从未到过日本的人都知道。
明乎此,下述情况就毫不足怪了:首先,自16世纪所谓倭寇的首次侵袭浪潮以来460,现在又出现了臭名昭著的海盗渊薮,这次是隆武朝、鲁监国政权及郑成功沿海抗清运动的海岸据点和新兵招募地;其次,各类不同的人物,几次设法从日本获得兵员、船只、粮饷及其他作战物资的援助461。观察一下从事这类行为的究竟为何等人,对于沿海地区抗清运动的一般组成情况便可了然。这基本上和内陆情形一样,也颇复杂,包括:(一)理想主义的儒家士大夫与科举中得功名者,他们感到,必须依据为国尽忠的原则行事(例如著名的流亡海外人士朱之瑜462);(二)豪杰型的武人(此处指好勇斗狠的船长),至少,他们或多或少遵循荣誉和社会良心的标准,而且同情失败一方的事业;(三)官军建制(此处指水军)的残余成分,他们现在和下面一类人难以区别;(四)亡命之徒、盗匪、叛党(此处指海盗与走私者)。如同大陆各地的抗清情况一样,这样的联盟是极易产生摩擦的;要靠这类联合来及时形成明朝方面的反击力量以挫败清军,希望是很渺茫的,这类联合所促使的,在内地,是收编李自成、张献忠大部队中的现成作战单位;在沿海,则是不断设法向日本借兵。
日本西南部的诸侯(大名)和官员,或直接掌管中日贸易,或从中得益,郑芝龙之类人物和他们关系密切。事实上,郑芝龙从出生到六七岁,(指瑕:译者误将“郑成功”译作“郑芝龙”,顾诚在其著的《南明史》中已经指出。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县(今福建南安)人,抗荷英雄,郑成功之父。)一直在平户,他的母亲则是松浦家族的家臣之女463。不过,当时涉足西南海外贸易最深的是萨摩岛的岛津家族,他们从位于该岛的封邑控制了通过琉球群岛的贸易464。与中国的贸易一向获利丰厚,德川幕府也很有兴趣继续这一贸易。它指定长崎为对外贸易口岸,从该地对中日贸易小心监管465。1590年代,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但未获成功;1630年代,日本制定了严格限制海上联系的排外政策,其目的主要在于隔离欧洲船只,以免传播基督教。在此之后,中日间官方关系即告中止。尽管如此,德川幕府对中日贸易的兴趣并未减弱466。
因此,由日中贸易巨头郑芝龙首先出面,向日本借兵以援助南明,也就不足怪了。1645年12月,郑芝龙的代表出现于长崎,当时郑芝龙本人已是隆武朝廷的军事支柱。随后,在1646年1月,周鹤芝又向日本要求兵士和甲胄。他是郑芝龙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当时奉隆武帝之命去援助舟山的黄斌卿。但是日本当局拒绝了这些最初的请求,所援引的理由是:明朝与日本关系已破裂,以及日本禁止武器出口467。
不过,在江户的幕府,亦即将军德川家光及其顾问,对第二批隆武使臣的请求,予以更认真的考虑。1646年10月16日,黄征明抵达长崎,再度请日本派出精锐部队援助南明。当时他有双重身份,既是郑芝龙的私人代表,又是隆武朝的官方使节。这一次,幕府的答复虽是否定的,但不是绝对的否定。日本的领导层显然在考虑,是否要采取某种军事行动,介入明清之战。但是关于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需要更多的情报。不过,在答复未送到之前,江户方面得知明朝已失福建,郑芝龙也已降清,于是江户不再考虑一切军事援助之议,并把这一决定通知各大名468。
1647年春,周鹤芝再次提议遣使,于是鲁监国诸臣也开始正式向日本乞师。这次的使臣是周鹤芝的义子,还有一位不重要的藩王。然而日本方面拒绝正式接待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在日本所得到的明朝两榜的试录、履历中,不见二人的姓名,因此不能证实他们的官方使臣地位469。
南明方面还试图绕过幕府,直接向岛津家族的领袖呼吁。岛津家族对于其中国贸易伙伴的事业有同情之感,而且他们想从事海外军事活动可能另有其自身的原因。据记载,周鹤芝在1646年初已作出安排,从萨摩岛接受3万人,连同粮饷、武器。但是此类计划据说为狡诈的黄斌卿所破坏。但在次年夏,黄斌卿也派遣其弟与冯京第一同前往萨摩,可能是希望恢复周鹤芝的计划。最后,岛津送了大量中国铜钱到舟山,但是没有任何军事援助470。
郑彩起初打算继承郑芝龙的事业,当然也包括外交在内。1648年12月,他致函长崎,建议以中国药物和丝绸换取日本的武器和作战物资;此外,郑成功也附一函,指出他和日本有特别亲善的关系,并请求派出数万兵士,援助御“虏”471。次年,琉球群岛的朝贡船出现于福建海域(原定进贡给隆武朝廷)。郑彩也利用此一机会,要求琉球当局做中日间的中介,鼓励他们输送火枪、刀剑、甲胄、硝石,以换取中国的白银及其他货物472。
尽管日本人一再拒绝派兵,以免在军事上卷入南明的抗清斗争,但忠明人士一直抱有希望,以为只要培植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即能获得一些其他的援助。1649年12月,刚在舟山建立的鲁王政权中了一个和尚的奸计。此人声称,朝廷若能向长崎一所佛寺赠送一尊观音像及一部鲁王母亲所藏的佛经,日本人定会感恩戴德。但后来朝廷得知,这个和尚在日本的传教行为为日人所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而被驱逐出境。于是这次出使成了一场空473。不过,据说在次年夏天,舟山得到了数十万升赈灾粮食。以后几年,郑成功毕恭毕敬,屡次致函颂德,以取悦于日本人,因而得到了铅铜与武器作为回报,但并没有得到日本的军力援助474。
日本方面对这些要求的具体反应如何,我们所知甚少。但一般说来,日本人不愿给予忠明人士以直接的军事援助,其原因有二:一是欲求稳定,刚成立不久的德川幕府,还有种种问题与顾虑;二是日人对南明的能力评价不高。大将军德川家光与家纲为巩固政权,要应付许多问题,其中包括如何加强日后被称为“锁国”的政策。这一政策禁止日本国民出国旅行;对于欧洲商人,不是完全驱逐(针对西班牙与葡萄牙人),就是加以限制(针对荷兰人)。而许多欧洲商人对此不能接受,采取敌视态度。另外,德川当时已能平衡大名的势力,但海外冒险可能破坏这种脆弱的平衡;还可能增加心怀不满的欧洲人在沿海地区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对于欧洲人的进攻,日本人担心自己不足以进行反击,因为他们对自己力量薄弱的海军在朝鲜之役中的不良表现,还记忆犹新475。不过,在日本人的记载中最明显可见的,是这样一种强烈对照:一方面,在忠于明朝的人士口中,明朝力量强大,前途辉煌;另一方面,日本人从长崎、朝鲜和琉球所观察到的,则是明朝的不团结、无效率,前景暗淡476。日本人绝不同情满洲人(满洲人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前已使缓冲国朝鲜就范),也不认为清朝征服中土是不可抗拒的。但是他们确实看到,中国已不再由明朝控制;再说,当时的日本领导层几乎不可能会对明朝有感激之情。因此可以理解,日本人不会愿意卷入这样一场其结果难以逆料的冲突。
广东中部是忠于明朝的力量抵抗清朝征服东南与华南的另一主战场。该地的军事行动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范围之广不及,程度之剧烈则过之。就抗清活动的大致轮廓而言,广东中部与先前普遍爆发抵抗的江南省南部十分相似。珠江三角洲实际上正在重演长江三角洲所发生的事。明朝官员暂时撤退,清朝方面在各城市行政中心轻易接管了代表政府威权的各种象征。甚至连倾向忠于明朝的地方显要也退到一旁,对眼前发生之事感到大惑不解,重新确定自己的立场还需要时间。至于普通百姓,则为满洲人的剃发易服令及残酷的“平定”措施所激怒。采取这些措施的将军不是别人,正是血洗苏松地区的李成栋。最终联合起来的各种抗清力量,也是一个大杂烩,其成分与江南及浙东的抗清力量一模一样。
但是在这最后一点,相似之中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广州的抗清力量中,明朝官军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小到无足轻重;而土寇、海盗(实际已构成了庞大的水、陆军)的比重要大得多。在江南,各地区的军事指挥因清军入侵而瓦解,因而各支官军既无集中控制,也无协调行动;而在广东,大部分官军部队已影踪全无,仍在广东的各总兵已没有多少兵士可以指挥。广东的常备兵,先前就已被抽调去援助南赣;留在广东的少数几支部队,人数太少,力量太弱,兵士不是轻易投降清朝,就是溃散,从而使本已相当可观的土寇与海盗组织更为庞大。
此外,长期以来,叛乱与非法活动在广东比在长江下游显著。例如在1640年,惠州地方官所面临的,是有组织的犯罪分子控制了道路和土地,并渗透入博罗各产铜区的军事和行政中心,这一形势所造成的结果是:地主及其代理人被拷打与谋害,税吏受折磨,赋税拒缴。据说自1643年起,广州东北及西北各县,不断受土匪骚扰达四十余年。北京陷落后,甚至在前面所说的广东军队调往别处之前,下级军官中的哗变和独立行动就已十分猖獗。又例如在1644—1645年,揭阳有一个武科出身的人,招募了一些“山贼”,以此为核心发展成蔓延甚广的“九军”起义,自称“后汉”政权。在沿海,下级军官联合广东的“蜑家”及各类土匪,夺取了海军设施,控制了海上税收。对广东中部社会领导阶层更具有威胁的,是当地贱民的无数次暴动。这些人一般被称为“仆贼”或“社贼”。这一类社会不安在崇祯末年即已开始,到1645年初达到了高潮。当时,顺德县地方官的下属,为其牢骚满腹的众仆人所杀。他们还焚烧其房屋,并大肆劫掠。此事引发了各地的同类事件,先是涉及广州西南部,然后蔓延到肇庆府南部。其中有些造反团体,据说人数达数千477。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士大夫显要们最终开始公然反抗广州府的清政权时,主要是河盗、山贼、四处流动的佣兵等的头领联合行动。佟养甲(关外“虏”臣)注意到,在他所称“南服荒徼”的氛围中,此类盗贼简直无地不有478。由于这一原因,广东和长江流域相比,缙绅阶层对抗清领袖的支持要差得多,不是态度更为保留,就是退出更早。
在1646年秋末及整个冬天,清朝从广州向各个方向派出军队,进行占领。李成栋率领其主力部队沿西江而上,直达梧州,企图俘获在广西的永历帝。起初,进展太过顺利,兵士不敷所需,因此佟养甲驻守广州城,只有几百人的一支小部队。不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绿林人物和明朝忠臣义士都明白,清军虽能防守广州城,其力量却很微弱,至于广州府其他地区的清军,根本不足以应付军事进攻。于是从1647年3月中旬至11月,著名的“广东三忠”发起了一连串进攻,收复了不少失地479。
南海陈子壮在三人中年事最长,而且颇有文才,又曾在天启、崇祯二朝参加“清流”党改革运动,因而名声也最著。弘光与隆武的官位他都拒绝。不出仕弘光朝,可能是出于因党争而起的厌恶之情;不出仕隆武朝的原因则是1630年代,唐王倡议扩大藩王在政府中的作用,他是最昌言无忌的反对者。现在他表面上顺从清朝,暗地则进行抵抗活动480。顺德陈邦彦是陈子壮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密友,在隆武朝曾出任兵部主事。福建失守时,他把狼粤兵调往江西任战守,然后又试图调解永历与绍武两个朝廷的不和,但未成功,因而失去了双方的信任481。东莞张家玉在三人中抗清最激烈,也最有军事领导才能。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他是翰林院庶吉士,而后一直被弘光朝列入黑名单,有与大顺军合作之嫌。此后,他鼓动浙东抗清,热情地为隆武帝效力;福建陷落时,又到广东的最东部招募新兵。父丧后归家,劝说清朝当局:退职的明朝官员内心虽有旧君故国之思,但并无危害,应予以尊重;希望以此来保护他的宗族和桑梓482。他的劝说似乎并不见效。他再次运用自己出色的带兵才干在广东抗清,这至少是一部分的原因。有意思的是,三人中没有一个与永历政权有亲密关系。他们削弱了清朝在广东的地位,从而减轻了清军从广西方面向流亡的永历朝廷所施加的压力。但是他们这样做,既不是奉明廷之命,也没有从明廷得到援助。
陈子壮与陈邦彦二人在珠江口以西协调各自的活动。河盗余龙徒党甚众,有船只数百艘。二人最初就是与余龙结盟,活跃于顺德县各水道。在3月的第三周,余龙和其他几股土匪围攻广州城未下。佟养甲于是觉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便从梧州召回李成栋483。在这第一次失败之后,陈子壮和陈邦彦转而设法与各式土匪、海盗、募兵以及被逐出封地的明朝小宗藩和军官合作,试图收复顺德、高明、新会等较小的城市484。
与此同时,张家玉在珠江口以东发动攻势,收复了家乡东莞,杀死了该地的清朝官员。他随后挥师往南,追逐清军,一路予以重创;又在新安与当地土豪的私人军队联合,但被清军击败485。于是向东北而逃,进入了惠州,在该府迅速地重建了博罗根据地。他从博罗出发,又收复了北面的几处地方以及差不多整个惠州府。由此可见,他有本事招募亡命之徒、豪侠之士、自卫武装、铤而走险的平民,等等,并在极短时间内把这些人组成庞大而有效的各支部队,其能力实在惊人486。在整部南明史上,张家玉是显示出这种才干的少数士大夫之一487。
4月初,李成栋返回珠江三角洲。此后直至夏末,他不得不驱驰各地,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镇压一次又一次的暴动,“如秋庭扫叶”,但是到8月初,局势发生了转折。当时,二陈及其海盗盟友再次试图夺取广州,这次行动规模更大,配合也更好。他们利用了城内间谍,分兵两路,发动战略攻势。但是这次攻势跟大多数由缙绅领导的军事行动一样,指挥不当,联络不畅,军机不密,作战外行,终于以惨败告终。从此以后,广州府西部及肇庆府东部的抗清运动只能是永远处于守势了488。陈邦彦随后集中力量在北面的清远抵抗,陈子壮则在高明陷于孤立。在李自栋的持续进攻下,这两个据点被攻破,二陈分别于10月与11月被俘,受到严刑拷打后,在广州城一起被公开处死489。11月初,张家玉被逼到了东北面的增城,与李成栋部激战后兵败。他受了重伤,投水自尽490。
在江南和广东给予明朝抵抗力量最惨重的打击的,都是李成栋。但是吊诡的是,此时这同一个李成栋,正要使南明重获生机。
第五章 复振与第三次抵抗:两广的永历政权
1648—1649年,清朝步步上升的好运急转直下。清朝之所以成功,明朝方面武人的不满情绪是一个重要因素。明将降清,原以为能享受更好的待遇,得到更多的机会,却未能从清朝方面得到满足。因此,事态发展自然会转为不利于清朝而有利于明朝。
在此一事态发展中带头的是金声桓(见第二章)。他是明末武人渴望晋升的一个显例。早在弘光朝,他已官至中军都督府佥事及援剿豫楚总兵官491。1645年6、7两月,金声桓投降之后,迅速行动,为清朝夺取了鄱阳湖地区,立了功劳。据说,当时九江等地前来迎接的诸生向他行廷参大礼,他趾高气扬,殊为得意492。不过他此后大感失望,因为清朝最初授予他的是以总兵官提督江西全省军务粮饷总理抚剿等事,官阶甚至比原来的还要低493。但是他显然希望征服江西其余部分,以进一步证实他的能力,从而得到升迁。此外,他现在权宜负责“抚剿”事务,兼管文武。他能握此大权,颇感称心惬意,因此一年来把全副精神用于江西战役,希望不仅在满洲人心目中,也在明朝降将的心目中,提高自己的地位。那些降将本来对这位伙伴的跋扈态度是痛心疾首,很不以为然的。
就清朝方面而言,对确有功劳者是不吝封赏的,但是他们对于不愿革除坏习惯的种种表现,尤其是对长江战役中明朝降将的这类表现,十分警惕。他们不久就觉察到,金声桓往往夸大自己的战绩以及江西战场的重要性,至于该省的不利形势以及他自己的财务,则不屑提及(或有意掩饰)494。此外,金声桓最亲信的部将王得仁一向以劫掠著称,清廷注意及此,决定把他免职495。
清廷考虑到这些情况,觉得金声桓的自吹自擂以及厚颜要求增加赏赐,实在是太过放肆,难以忍受。尤其是1646年6月,他的职务仅是改为“镇守”,他就表示反对,疏称宁愿保持原衔,并请皇帝另赐敕书,假以便宜行事之权。清朝兵部的答复很干脆:本朝从无便宜行事的制度,金声桓作为总理“抚剿”事的武将,所拥有的节制文武的特别权力,现在必须移交给新上任的江西巡抚、巡按。但是,由于江西继续动荡不安,也由于有臣下提醒清廷,“盖文官欺武官,明之亡也忽焉”,因此清廷允许金声桓保持江西提督总兵之职,不过免去了以前的紧急权力496。这很难使金声桓满意,尤其是因为新任巡抚、巡按对待他和王得仁二人傲气十足;金声桓一名部将升任总兵官,更表明了清廷有意破坏他已在江西培植起来的半私人指挥机构,他对此也大为不快497。
因此,金声桓下定决心转向,再次宣称效忠明朝;然而他还在等待,直到和江西的忠明之士以及湖广的永历官员作出秘密安排之后,才诉诸公开行动。但是王得仁知悉,巡按已上疏指责他抚绥时所为不当,渗入他营中的明朝忠义之士又从旁激励,他于是逼迫金声桓下手。1648年2月20、21日两天,在南昌的清巡抚被囚,巡按被杀,其余人人除辫。金、王二人,一人自封为公,一人自封为侯。他们起先奉隆武正朔(在江西的忠明之士中,隆武年号最为人所知),而后派遣使臣找到了永历朝廷的所在,告以“反正”之事498。前大学士、湖广人姜曰广,此时居于南昌。(指瑕:译者误将“弘光”译作“湖广”,姜曰广是江西新建人,弘光朝大学士。)金、王二人为使自己更名正言顺,劝说姜曰广给予支持,为他们的事业增加威望499。
虽然金声桓的行动,是出于因个人利益而起的意气用事,既无长图远虑,亦无领导才干,但是他的归明影响深远。不仅江西的忠明人士纷纷而起,而且远至湖广西部及福建沿海一带的官员也都开始背清向明。湖广东北部结寨自保的人再次活跃,远在长江下游无为等地的同情复明事业者攻击清军各据点。甚至河南东北部这样的战略要地也抓到了金声桓所派煽动起事的间谍500。除此之外,北方的山东中部,陕西东南部汉中地区以及今甘肃省东南部的回民聚居区等地,一向是清朝感到棘手的地区,现在又一次形成了燎原之势501。更糟糕的是,1649年1月,清大同总兵姜瓖也以复明名义发难,不久,就在北京西面的半个山西省以及陕北大部,都起而造反了。于是满洲援军被派往南方,协防南京,而多尔衮本人及其他最有才干的满洲亲王则亲自出马,应付大门口姜瓖的威胁。晋、陕二省的反抗,直至这一年的10月才完全镇压下去502。北方的起义,并不都是由真正的明朝忠义之士所鼓动、所领导的,与永历朝廷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金声桓叛清之后,全国各地似乎都看到了清朝的弱点。于是对清朝而言,南昌地区的困难局面变成了一场持续两年的危机503。
湖广的清军当局,本来就感到这个省布满了荆棘,现在获悉了东面的金声桓反叛的消息之后,不消说,就大大地收缩了军事行动。进攻全州和桂林的艰巨战役取消了,只有小股的孤立(注定要失败的)驻军留守道州与永州,而清朝真正能控制的区域缩小到长沙至武昌的一小块地方。明军当然迅速利用这一形势。以前的叛军与逃兵,名义上由堵胤锡统率,本来是在湖广西北部的山区固守,现在又回到了洞庭湖流域,占据了常德、益阳等重要城市,(指瑕:湖广西北部指的是郧阳、襄阳一带,而马进忠、王进才部驻扎九溪卫、永定卫,“忠贞营”驻扎在施州卫一带,这些地方不宜写作湖广西北部。)把清军打得晕头转向504。与此同时,总督何腾蛟及其属下各将领,终于能从湖广最西部和广西东北部脱围而出,在1648—1649年秋、冬,夺回了所有的老据点,直至湘潭505。因此,在金声桓反清后一年之内,差不多整个湖南又成了明朝的天下。
金声桓此举最重要的后果,是对李成栋的影响。李成栋是有理由对清朝所给予的待遇感到不平的又一个总兵。他起初被任为镇守吴淞、松江沿海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府都督同知,因而曾为征服长江三角洲地区出了大力。立了如此功劳,反被指控纵兵骚扰地方而受到正式的调查;虽然他的这些罪名是被开脱了506,但是显而易见,清朝对于再给他更大权力、更多责任,还是持保留态度。早在福建之役结束之前,他就已向北京提议,他本人与部属应得到更厚的赏赐。平定广东之战开始后,他几乎以一人之力东征西讨,因而在1647年6、7两月,清廷按例宣布任命两广各官时,他又以同样口吻为自己的功劳辩解507。令他失望的是,他只得到左都督、充提督广东总兵官的武职,节制两省文武的大权给了出任两广总督的佟养甲508。
因此,李成栋确实有理由牢骚满腹。有记载说,他最初经由广东攻入广西时,曾获得明两广总督印,私下保存了起来;又有记载说,他在镇压复明义军时,深为这些人的热忱所感动。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在1648年春初得悉金声桓归明之前,即已考虑过反清509。通行的几部史书喜欢强调他的爱妾对他的影响。据说其爱妾为了劝他重归明朝,在4月底以自杀来作最后的劝谏510。这件事确实可能使他大为感愤,但是在理智上对他作用更大的,还是下面两项消息:金声桓的军队就在他的北面511;一旦永历各军将领在湖广重占上风,他可能更陷于孤立,更易受伤害。
于是在1648年5月的第一周,李成栋在广州公开宣布奉永历朝正朔;在这件事上和他密谋的主要有两个人:养子李元胤及新任广东学政副使袁彭年。至于他如何迫使佟养甲一同反清归明,说法不一,但是他最初所持的理由似乎是,须行权宜之计,“以安民心”。总之,他找到了一个不杀佟养甲而实行反正的办法。看来他对佟养甲还是很尊敬的512。不过,满洲兵以及广州城内其他改从满俗的人就不那么幸运了。李成栋一面派遣官员向南宁的永历朝廷表示恭顺,一面就对辫发高领的人展开了一场大屠杀513。
永历朝廷处境穷蹙,“槟榔客、盐布客及土乐户皆列鸳班”;土司则升为知府、御史,因为朝廷以为,博取土司好感是明智之举514。永历帝直至5月2日才从江西得到金声桓反正的报告;而李成栋归顺之讯,五周以后就抵达了,如此好消息,真令人难以置信。李成栋的使者受到了小心款待;而后永历朝廷要求得到李成栋的个人函件和慷慨捐赠,以祛除疑虑,证明这不是圈套。不过,金、李二人最后都封为公,李成栋更被任命总制整个东南地区515。随后在7月底8月初,永历帝侍从诸臣经由浔州、梧州,最终于1648年9月20日回到肇庆,一路上接纳了分散隐藏于广西的数十名文武官员。这些朝臣经过一年半的艰困屈辱之后,荣耀而归,又受到李成栋的殷勤款待,心中颇为高兴516。
还都后的永历政权,其政治格局虽然错综复杂,但是所反映的,还是销蚀南明最甚的那两个问题,即辅佐皇帝与武人地位。在当时的情势下,这两个问题变本加厉。一方面,在长期大难临头、疲于奔命、勉强糊口的现实环境中,永历帝严重依赖其锦衣卫左都督马吉翔;另一方面,复振后的朝廷,此时事实上完全依靠李成栋的军事组织。
马吉翔初起时是广东的一名下级武官,因在隆武朝有特殊功劳而被拔擢入锦衣卫。1647至1648年,永历帝在湖广西南部及广西东部奔波亡命,马吉翔对皇室的安全与舒泰特别操心,只要是能为皇室做的事,总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作为武人,可说是甚通文墨,于是开始处理公文,起草谕旨与敕封;其妾殷勤侍奉高年皇太后,使她称心惬意,他因这一层关系,甚至间接取得了宦官首领的地位517。
吉翔机辩干办,独有擅长。宫中自太后而下,一针一线,无不取给。遇患难,寸步不离。辅部以至候人夫头,皆一身为之。诚为小忠小信,小有才矣。顾凡事欲出自我,而不能识其大。喜昵小人,务周旋情面。易为利动,不务存大体。若[王]坤与翔者,皆不可用而亦皆可用也。518
永历朝廷重建之时,马吉翔(此时已封文安侯)因自己的武人背景而避去大学士之位,做得很是得体。但是他“辞阁衔而不辞阁权”。他取得了佥都御史之职,又为各机构票拟,代行首脑职权,于是不仅掌管了锦衣卫的军务,还把持了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及六科给事中的文职事务519。
李成栋相对来说,沉默矜持,但也是一个有趣人物。他外表上严毅冷酷,然而在内心深处,感情丰富、复杂而敏锐。
成栋为人朴讷刚忍,无矜意,无喜容,不脂韦,不多言。文武内外惠敬而深畏焉。520
他或许因一直杀人而痛饮浇愁。只要有政府任用他,他就尽力而为(不过是太严厉了一点),所希冀的不是荣耀,而仅是政府承认其功劳,并予以适当的酬报。然而他为之奋战以保卫其利益的那些人,却对他不信任;以前的清朝是如此,现在的永历朝也如此,尽管他对永历朝是十二分的尊重。他为此常感痛苦。肇庆方面对他的贬斥,使他对文人官僚更增厌恶之情。不久他就决定,与朝廷保持距离,只集中精力履行一个武人对皇帝应尽的义务。永历帝准备为他筑坛,行封拜大礼,他上疏辞谢;不久就离开了广州城内的大本营,亲自率军防守梅关,收复南赣,所坚持的只有一件事,即在他军事行动的区域之内,不可安插文官521。不过,此后朝廷是在李元胤的监视之下,他那时已是南阳伯提督禁旅522。虽然二李与马吉翔不同,小心谨慎,不直接干预朝政,然而实际上,二李的意旨是很少能违背的。
永历朝廷迁回广东之后,第一件事是重设百官。当时有两类官员,一类是在朝廷最近的播迁期间忠心耿耿,有“扈从”功者;另一类是随李成栋归附,有“反正”功者。赏赐与权力在两类人中如何分配以取得平衡,是重设百官的首要困难。在后一类人中,有不少原来是拥护绍武政权的。在永历旧臣看来,这些人比曾经支持清朝者更可恶,更令人不能放心523。而那些来到广东之前曾与满洲人合作者,反倒被认为更靠得住。其原因不仅在于,李成栋与佟养甲的政府与军事体制,比永历朝所设立的要高出一头;而且也在于,那些人先前为征服者出力,现在又背叛,因而不大可能再得到清朝方面的宽恕。
不过,明朝政府内门户的分别另有更具普遍意义的基础,即来自同一地域,座主门生关系,以及某几个关键部门中的职位。旧臣与反正诸臣的分歧,不久便为这类朋党基础取而代之。从弘光朝的情况可以看到,不论何党,若要生存下去并取得支配权,必须在下述三方面有自己的得力成员:(一)亲近皇帝本人及其家属的所谓内廷;(二)由各部、司及都察院所组成的外朝;(三)省级机构,在南明时代,此类机构逐渐与各地总兵体制难分彼此。党争的首要目标,是猎获内阁职位,从而对皇帝处理公事以及任命其他各职,产生影响或予以控制。
在永历朝廷,两个松散的朋党逐渐形成。占优势的是“楚”党,其核心成员在都察院。在侍奉皇室的宦官及护卫皇室的武人中,均有此党的支持者或同情者。掌握永历朝最精锐武力的李成栋、瞿式耜,以及首辅严起恒,都赞同此党,楚党得名之由,是该党首领二人都来自湖广中部。二人分别占有都察院两个最重要职位,再加上另外三位御史,合称“五虎”,因为这五人在政治上咄咄逼人,在廷议中声嘶力竭524。
处于劣势的是“吴”党,其基础在内廷,成员是宦官和皇帝外戚,尤为重要的是马吉翔。尽管朝廷已有了更正式的机构,马吉翔依然是包揽一切的皇帝私人总管。在粤中地区之外,吴党的主要支持者是广西中部野心勃勃的将领陈邦傅(瞿、李二人鄙视他,并不仅是党争之故);在外朝的最重要党羽则多为各部侍郎。大学士中也有二人被视为吴党。吴党之得名,可能是由于该党部分领袖人物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525。
朝廷还都肇庆后16个月内,楚党一直居于上风。其主要原因是朝廷要依赖李成栋的军事组织,另一原因是真正的行政网并未建立起来,此外,李成栋的部将和养子一直控制了广东及禁卫部队,即使他本人死去以后依然如此。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即楚党由“清流”人物领导,植根于外朝的监察机构都察院,其共同特征为:通晓既合宜又合法并合乎道德的明朝处事成法,并坚决遵守526。
(朝廷还都肇庆)下考贡之旨,村师、巫童以及缁衣、黄冠,凡能搦管出黑字于纸上者,悉投一呈,曰山东山西某府某县生员。然必取其极远者,以无可证也。曳裾就道,弥漫如蚁,曾经出仕,佥曰迎銮;游手白丁,诡称原任六曹两侍。旬日间驻列济济。然相遇于朝堂道左,各不举手。为有一二科甲在内,故凌气质以自尊;二三势力在内,为豪亢以自高。此外菜佣、屠夫、出门、皂役、优倡、鸨卒等项,虽居然进贤冠也,行行队队,若不欲以面示人。527
此一记载语带贬抑,实际情况或许不致坏到如此地步,但永历朝廷确实需要一番洗心革面。楚党强调标准、资格以及措置得宜,尤其是言辞犀利的礼科给事中金堡,更为锋芒逼人。这很可能会刺痛皇帝及其他许多人(尤其是吴党中人)。但是,强调这些事情正是朝廷所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大批认真办事的文人入仕,才能着手重建一个像样的朝廷,以治理目前仅靠军令来维持的数省地方。换句话说,楚党声称,自己知晓如何管理一个真正的明朝政府,尤其是当时的永历朝廷,确实需要看起来像真正的明朝政府。
但是,吴党也在明朝政治史上一再出现的格局之内,因而其地位也是稳固的。前一阶段,险阻穷乏持续不断,头等大事是使皇室得以活下来,而不是如何统治帝国。在此情形下,与内廷有关的人自然是影响最大。永历帝的为人,尽管不愚,不荒淫,也并非万事不理,然而一见事情复杂,就生厌恶之情,而且也没有领导能力528。由于他的这种无主见的性格,在1648年朝廷重建之后,内廷势力依然强大。永历帝与先前的弘光帝至为相似,也是对朝章国故茫无所知,一旦需要乾纲独断,同样感到惶恐。于是宦官和马吉翔成了他的挡箭牌,每当“清流”官员把他视为临朝天子,提出种种要求时,就躲到这块挡箭牌后面。
楚党主要人物所标榜的,是澄清朝政,拨乱反正,使出仕者“得其人”,争取民心,在全国重建明朝的秩序。他们声称,目的不在党派利益,而是为大业独立无私地行事。但是,正如晚明屡见不鲜的情形一样,“同道为朋”的“君子”声称,一个合适的政府应维持“纪纲”,然而在这言辞的背后,其实是合谋驱除某些奸人。他们通常以为,这些讨厌的人破坏了国家的基本原则,应予清除。即使这是事实,但在政治斗争中,对于奸邪之辈的不道德强调得过了头,权宜之计用得过多,在小节问题上也过于挑剔,而“清流”人物对于这样做可能给政府的团结所带来的损害,往往是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对于他们所反对的那些行为赖以产生的形势,也毫无觉察。于是为理想而进行的奋斗,成了出于个人私利的冤冤相报;为了整肃“纪纲”,往往把婴儿连同澡后脏水一起给倒掉了。
就在两广复振的永历朝廷而言,楚党几乎集中全副精力,以对付不居首辅之名而有首辅之实的马吉翔以及拥兵自重的土皇帝陈邦傅二人手下的非正规武力(以及广布的党羽);至于更根本的问题,诸如备皇帝顾问、领导朝廷以及如何支持军务并论功行赏,则很少关注529。例如,楚党指控马吉翔自一位宗室及自己手下的书记那里收受大量贿赂,因而使二人任职御史台530;又指控他伙同一位中书舍人,在诰敕上改动一个字,以便陈邦傅能“世守”广西,而陈邦傅本来就逐渐把自己控制下的广西土地视为私有,经此一改动,等于官方对他的行为表示原宥,并使他变本加厉(陈邦傅为此事,一直受到在桂林的兵部尚书瞿式耜的猛烈抨击)。陈邦傅面对金堡的这一攻击,也上疏辩解,并在疏中最后提议,派金堡任他的监军御史(言下之意,就是要把他杀死)。于是一位楚党的中坚人物带领都察院全体官员辞职。这一示威行动来势汹汹,当时在別殿与一个客人闲谈的皇帝闻知此事,据说吓得把茶都泼翻了531532。
虽然“清流”御史悉数召还,两位吴党的大学士也因此类事件以及其他争议而离职,但楚党的这种胜利是空洞的,因为贪赃、任用私人、行为不端、依靠阃外将帅的势力之类的指控,同样也能适用于楚党中大多数人533。马、陈二人依然未受伤害。更坏的是,因持续不断的意气用事,实际上未做任何事来对暂归明朝版图的诸地区作真正的治理。
有一件事,以后对永历朝廷有致命的影响。从此事特别能看出,楚党发言人的“清流”立场与吴党更求适应环境的“现实主义”,是何等的不同。1649年春末,有两位官员以孙可望使者的身份抵达肇庆。孙可望是上一年占据云南省的流寇部队的领袖(见第六章)。孙可望的使者上贡礼物,并奉书邀封王爵,以坚其归顺明朝之心534。朝廷是否应允其所请的一场长期辩论,于是就开始了。一派人持赞同态度,以为只要能巩固朝廷的实际安全,武人领袖的虚荣,乃至据有土地的野心,不妨予以满足。他们以为,只要授一枚官印,发一纸诏书,即可赢得一个同盟者,若不如此,此人可能还会向朝廷发起进攻。
但是朝廷“纪纲”的维护者(他们怀疑,孙可望可能与陈邦傅勾结)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辞锋犀利、望之俨然的金堡总结了如下的理由:首先,依照祖训,凡尚生存的非明朝同姓者,不得封王,不论是亲王还是郡王。而更为重要的是,朝廷若屈服于压力,威望会贬损,士气亦会降低,即使可能在军事上获得此一巨寇的助力,也是得不偿失。不论是否授予王爵,朝廷对孙可望不可能有实质的控制;而朝廷若坚守原则,孙可望反倒有可能留下深刻印象,真心归顺明朝。总之,皇帝与文武大臣若能通力合作,目标一致,对抗大敌清朝,孙可望之流的乌合之众能做出些什么事,是大可不必顾虑的535。
这是典型的“清流”之见:行为正当犹如草上之风,普遍的真精神更能收成功之效。“清流”着重这种看法,使得在楚党完全失势之前谈论孙可望的请求,成为不可能之事。不过,朝廷为了安抚孙可望,也可能是为了满足他拔出于云南叛军领袖侪辈之上的需要,便授他以公爵,其他人则为侯爵。两位使者终于在仲秋离开肇庆,返回云南536。但是不久,在广西的两个吴党人物采取了另外的行动,使者的任务也就改变了。
陈邦傅对于西北方的孙可望军力一直警惕,希望与他保持友好关系,此时就伪造了诏书,封孙可望为“秦王”(按:为亲王),并派手下人赍诏前往537。孙可望接到此诏,大喜过望。他对于自己的新地位沾沾自喜,并以此训示周围所有的人。此时,他原先派出的使者回来了,带来的封号是“平辽王”(按:为郡王)。这一封号是前湖广巡抚堵胤锡矫诏制造出来的。堵胤锡可说是擅长招安前叛军,使之归附明朝;而金堡之类的人却一直为此指责他,他因此忿恨不平。这两个自相矛盾的封号自然使孙可望大惑不解,怒从中来。他的使者在盘问之下吐露了真相:朝廷敕封的其实只是公爵。孙可望顿时大怒,立即派使者回去,要求澄清。同时,永历朝廷的党争格局也已改变,但是在1650年春,由于与前不同的各种原因,朝廷再次以花言巧语拒绝孙可望的要求。从此与孙可望的关系就走上了一条灾难之路538。
这一类内部纠纷与处事不当,其原因多半是对于武人在国家机构中的适当作用、潜在角色究竟是什么,看法不同;其另一后果则是:在比云南更靠近、更重要的其他地区,永历朝廷也不能有效利用机会,应付危机。朝廷不能向江西与湖广的将领提供支援,因而收复这两个省的企图失败了。二省的将帅因此无法从战略错误及挫败中恢复过来,手下的兵士也不愿面对敌人。于是到了1649年中,二省将帅在清军与永历朝廷中间所构筑起来的缓冲地带迅速消失了。
在江西,有一个将领拒绝随金声桓归明。此事有致命的后果,因为他的大营就在赣州。金声桓因此不仅无法与南面的李成栋联合,而且一旦他从南昌和九江向东北方挥师进攻南京,后方就有可能受到攻击。他为此而作出了或许是错误的估计,认为夺回赣州,使之归明是第一要务。于是北方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来应付局面539。一支清一色由精锐八旗兵组成的清军,由满洲和蒙古(不是汉人)梅勒章京(副都统)率领,从北京派出,一路南下,来对付金声桓。1648年6月中旬,这支清军自东流越过了江西东北角。(指瑕:这支部队的主帅谭泰、何洛会,原本的职务都是固山额真。清军进军路线是:一路攻九江,一路攻饶州,“江西东北角”的说法似乎不是很精确。)金声桓、王得仁两人围攻赣州不下,匆忙折回北方,刚重入南昌城,清军就开始了第一次协力攻城战。8月底,清军猛烈攻城,但不能得手,于是就驻扎下来,作长围之计,想使这座坚城因穷饿而不战自屈540。
南昌未能从何腾蛟与李成栋方面得到有效的援助,被包围隔绝半年以上。明军在湖广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于1648年夺回全省。(指瑕:明军只是夺取了湖广南部的部分地区,长沙、岳州均未收复,充其量也就一半。)紧接着,在1649年1月,却爆发了一场极为激烈的内斗。一方是前大顺军的主力,现在称为“忠贞营”,名义上受堵胤锡节制。另一方是左良玉残部,现在名义上受何腾蛟节制541。当时何腾蛟希望从清军手中夺取长沙(从而恢复该地与北赣间的陆上交通),“忠贞营”却从长江上游一直奔向广西中南部,(指瑕:当时的情况是,“忠贞营”正猛攻长沙,功在垂成之时,何腾蛟令其东援南昌,解救金声桓、王得仁部。这个责任主要不在“忠贞营”。而且,“忠贞营”是东援不成后,从湖广东南边境开始“奔向广西中南部”,而不是从“长江上游”。“北赣”译作“赣北”为宜。)迂回跋涉,道路既阻且长,兵士满腹怒气,不顾一切。聚集在洞庭湖南岸的大量明军经此冲击,阵脚大乱(见地图11)542。那些原来仅在名义上听命于何腾蛟的部队,在“忠贞营”横扫过后,更是陷于一片混乱。因此,何腾蛟对于南昌金、王二人的呼救,除略作姿态外,爱莫能助。
在广东北部及江西赣州府之间交界地区的李成栋部,以前在满洲骑兵与高效率的清军后勤系统的支持之下,似乎是所向无敌,而现在遇到了身经百战的南赣人民的抵抗,却畏首畏尾,逡巡不前。南赣人此时为保住本地区清朝建立的秩序而顽强作战,正如以前为保明朝秩序而战一样。李成栋于是被迫在1648—1649年冬返回广州,重作整顿与补充,准备反攻。但是当他在2月再度出梅关时,(指瑕:这里应是译者的错误,作者的意思可能是1648年冬到1649年初。)清军已能从北方增援赣州,他因此无法救援南昌了543。
南昌城受重围6个多月,早已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有些兵士暗中同意投降,清军因而于1649年3月1日登城。金声桓、姜曰广二人自杀,王得仁作战被俘,后被处死,他们手下的忠义之士,大多数拒绝投降,也遭杀戮544。同一天在湖广方面,何腾蛟纯出意外,在湘潭被擒(他一心想重行召集逃亡士兵,外出连卫士都没有带);他坚持不屈,数天后在长沙就义545。与此同时,李成栋依然攻不下赣州,被清军救援部队逼到了信丰一角之地。有关他最后的时刻的各种记载仅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在信丰地区,试图渡过一条因雨水而暴涨的河流,遭溺死,时间大约是1649年4月的第二周546。于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一年前永历朝忽然复振所主要依赖的金、何、李三人,都从世上消失了。江西与湖广的明朝军力因而完全瓦解。虽然清朝并没有立即向前推进,但更向南方作第二期的征服,条件已经许可。
第六章 第三次失败与相持:大西南与东南
满洲人一直渴望提升其形象,使之看来像是把明朝从寇盗蹂躏中拯救出来。他们自从侵入明朝疆土以来,首要任务一直是逐步击溃与消灭李自成与张献忠的大量流寇部队。1645年,李自成残部大多加入了湖广的明军组织。自此以后,清朝方面更顺理成章地宣称,要完成其消灭流寇的任务,就必须击败各支自称南明的军队。以前他们指责弘光朝廷不发一兵去攻击西北的大顺军,现在更能振振有词,斥责南明各朝把倾覆北京明廷以及使崇祯帝(现在大受清朝敬重)殉难的人,视为自己的盟友。
因此,在1648年10月,永历军在何腾蛟与堵胤锡率领下收复了湖南大部之后,满洲亲王济尔哈朗受命消灭李自成继承者“一只虎”李锦(按:李锦独眼,故名“一只虎”)以及大顺军残部主力。这是率军反攻湖广省长江以南地区明军的另一种说法。但是当济尔哈朗于次年春抵达,实施反攻时,形势却是变化多端,混乱不堪。要向前推进是容易的,而要取得控制就难了,至于要找到真正的李锦,那是不可能的(“忠贞营”已一路劫547掠,进入了广西)。清军于1649年夏夺回了湖广最南部主要城市,但是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控制并不牢固,同时也没有再合力向前推进。总之,济尔哈朗并未受命攻入两广548。江西的情形也是如此:清军各将领接到命令,只须收复南昌,救援赣州,以及平定江西的忠明抵抗活动。因此,当李成栋的进攻部队在赣州附近瓦解之后,取得胜利的清军只向梅关作了侦察,而没有及时进入广东549。
清军一如既往,喜欢派新调发的军队进行主要攻势。1649年6月,北京清廷再次命令三位封王的老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做前锋,重新向南推进。不过,这一次耿、尚二人必须通过江西进入广东,而孔有德须回湖广,设法第二次攻入广西(见地图12)550。当各支军队到达战场之后,耿仲明军中发现有旗下逃人,攻势因此延缓。耿仲明本人亦因事发而受辱,自尽了。但是才略不减乃父的长子继茂,被允准继仲明统领全军,于是进攻又很快按原计划进行了551。与此同时,1650年1月,孔有德从长沙南进,集中全力夺回了永州;耿、尚二人也向南推进,越过梅关,抵达南雄552。
永历朝廷获知何腾蛟、李成栋二人的死讯,大为震惊,不仅因为现在朝廷的防御必将急剧恶化,而且还因为永历政局中占上风的一党所依恃的,主要就是何、李诸人的军事能力。朝廷于是设法对广东、湖广各军重新确立有效的领导,但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553;吴党的主要武人盟友陈邦傅麾下的广西军队,因而就成了朝廷能直接依靠的唯一未受破坏的部队,因此,在1650年2月的头7天内,当明军放弃粤北据点,让与清军前锋的消息传到朝廷时,皇室便匆忙逃离肇庆,直奔梧州。播迁途中,朝廷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剧变。虽然李元胤以及其他几位李成栋部的将领,依然担负重任,坚守广州城与西江554,但是,由于稳定的打破以及朝廷仓皇逃往陈邦傅辖地,对楚党领袖人物蕴蓄已久的怨恨,犹如洪水破闸、迸发而出了。五虎中的四虎,因此受到了近乎疯狂的迫害555。
四人在梧州被马吉翔的锦衣卫逮捕,并受到审问。其中以金堡所受报复最厉害。他被严刑拷打,终身成了跛腿。起先,皇帝东宫太后以及几个吴党中人,至少要想把楚党中最为唇枪舌剑的那些人处死,所持理由是他们阴谋煽动;但实际原因是,这些令人生厌者身处高位,成为众矢之的。不过随后,这位小孩一般易冲动的皇帝多少镇静了下来,许多官员纷纷上疏,认为在此危急之秋,倾注全力惩罚御史实属不智,李元胤并亲自入朝,声称自己与被监禁的四人关系密切,要求皇帝也处罚他556。但是直至仲夏,部分忠贞营部队移驻到梧州之后,迫害才告终止。忠贞营其时正跟陈邦傅争夺广西地盘,虽曾受到警告,不得干预朝政,但还是施加了压力,使吴党的锋芒受挫,被监禁的“四虎”也因此获释。四人最后分别判处充军、发徒、以银赎罪及免除官职557。这一连串事件生动地表明,尾大不掉已到了何等程度,亦即尽管口头上一直说以文制武,而事实上这种说法既是欺人之谈,也是自我毁灭。
与此同时,清军一直在稳步推进,而且这一次与1647年相比,更为有条不紊,军力集中在少数几处,避免战线拉得过长,对敌手的估计也更为谨慎。1650年春,孔有德巩固了对湖广西南端的控制,部署兵力,准备分三路进攻全州到桂林的狭长战略地带558。3月初,尚可喜与耿继茂从粤北南下,绕过肇庆与三水的明军,直抵广州城下。清军发动了首次进攻,但未能将城内顽强抵抗的明军逐出,于是作艰苦的长围之计,只腾出少数几支部队协助新降的明将平定东边叛服不常的地区。长围广州对清军而言是很惨的。这一年的广州之夏,天气湿热,到处是泥泞,又流行疟疾,清军的兵员和武器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而且广州城三面环水,普通围城技术不能完全适应。清军虽出钱招募了该地区朝秦暮楚的河盗,也建立了一支小舰队。但这次战役主要是双方用重炮互击559。
广州城被围八个半月之后,守卫老城西门的明将为清军所诱而背叛,清军于是能架起大炮,轰击内城。
1650年11月24日,处于此一有利地位的鞑靼人,全军冲入城内,很快就制服了全城。围城内的人居于不利地位,无法再抵抗;因为鞑靼骑兵一旦入城,就能疾驰于大街小巷,阻止中国人集中;虽然中国人并不比鞑靼兵少,但他们陷入混乱,并对自己巡抚(原文如此)的叛降感到震惊,因而不再能作有效的抵抗;于是任何人所能作的最佳选择,就是逃命。
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兵士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至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按:指明朝的忠义之士)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最后,在冬月的六日,总督及清军统帅下令,即日起不得再从事如此惨酷的杀戮。我得到确切的消息在八(十八)天之内,被鞑靼人残忍地屠杀的,在八千(万)人以上。560
同时,防守广西东北部明军各将帅之间的合作全面瓦解,尤其是全州发生了兵变,孔有德利用这一机会,得以在1650年11月27日攻入桂林(该城以前曾三次击退清军的进攻)561。瞿式耜同他的一个忠实助手一起被俘,拒绝了孔有德的劝降,于次年1月在桂林遇害562。
清军从东、北两面夹击梧州,皇室惊慌失措,于12月2日仓促出逃,溯西江而上563。永历帝的船队一路上受到暴乱兵士的大肆劫掠。还有几个将领想把皇帝献给清军,永历帝险些被他们捉住。许多从亡之士在混乱中四散奔逃,往往落入了土寇与土著部落之手。这些人对外地来的士人、官员、商人,不是抢劫,就是骚扰。此时陈邦傅及其部下准备从梧州向清军投降,皇帝及幸存的从亡者则在南宁暂时避难。永历朝廷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564
1651至1661年,是南明的最后10年。在这10年中,正规明朝文官体制的最后痕迹几乎全部消失;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永历朝廷完全依赖下述军事组织:在西南,是明季叛军最强的残部,现在由孙可望与李定国统率;在东南,是控制该地区的垄断海上贸易的半海盗组织,现在以郑成功为首。这两个组织原来都完全是在明朝体制之外发展起来的。迄今为止,所谓“明朝”,在很大程度上有其体制上的意义;而在现在这种形势之下,此一意义丧失了,“明朝”所代表的,毋宁只是一种精神——坚持抵抗外来势力侵略与控制的精神。但我们也能看到,西南地区还是有明朝皇帝,由于这一事实,文武领袖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一方具有文治倾向,另一方关注的主要是作战。相比之下,东南沿海地区实际上并无明廷存在,反而更能团结一致,抗清更为有效。
若要了解1651年以来永历朝廷的情势,不仅必须回顾北京陷落以来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省份所发生之事,在某种程度上还需回顾西南在明朝政府系统中所处的地位。(按:明代的四川省划与今日不同,包括今贵州省北部占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也包括今云南省东北角。贵州则相对较小,今川、贵边界划定于1727年。)
张献忠是崇祯年间未被李自成消灭、亦未从属李自成的一个主要叛军领袖。1643年,他在湖广中部首次自称“大西国”王,显示他有自立朝廷之想。在1644年,他率领全体部下进入四川,重建一国。他从都城成都控制了四川省大部分最发达的地区,并实行一般认为的血腥恐怖统治。由于这种恐怖统治,四川人口锐减,物资枯竭。不过,尽管成都相对而言地势隔绝,张献忠在成都还是不安全,他不能避开成都周围地区明军残部诸将领,也不能避开老对手李自成,后来还有陕西的清军。最后,他吸干了四川这一基地的脂膏。于是在1646年底,他显然想夺取已为清军所控制的李自成的老根据地,即陕西东南部西安周围地区,并发动了初步的进攻。但是当他扎营于四川中部地区北首某地的时候,受到了一支清军先遣队的袭击而丧命,时在1647年1月2日565。
张献忠死后第二个月,其主要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诸人皆为献忠“养子”)566拼死奋斗,重组了献忠残部,并率领各余部进入了相对安全的贵州省。他们从明将手中夺得了重庆之后,力量稍为壮大,于是在1647年春南下,占领了不设防的贵阳,一路上几乎没有遭到抵抗567。不过这一次他们并没有长驻贵州,因为诸人中公认的“大哥”孙可望,不久为云南所发生的非常情况所吸引,进入了该省。
云南在明朝,自始至终以一种特別的方式治理。云南与西南其他各省一样,有一个混合体制:一方面和全国各地相同,有正规的省、府、县各级文官政府;另一方面,与各地土著居民聚居区的情况一样,有一个世袭土司及“宣慰司”的系统568。但是在云南,与各部门平行,事实上是凌驾其上的,还有一个勋贵沐氏世袭的军事体制(及大采邑)。沐氏祖先是明太祖最宠爱的养子沐英。云南作为明朝一省,实际上是这位令人尊敬的沐氏祖先创立的,他还使云南成了汉族文明的一部分。沐氏世封黔国公,在15与16世纪,是有实际辖地的唯一明朝贵族,声望颇高,地位稳固,无人能与之抗衡569。
但在崇祯年间,沐氏对云南的控制因两种情况而削弱。首先,当时的黔国公沐天波让事权落入了一个腐败的部属之手;此人既狂妄,又苛求,引起了沐氏属下各官员及土司的不满,而要维护云南安全,必须获得这些人的合作570。其次,有些沐氏属官及土官土司,是近年中招募来协助平定云南境外叛军的,此时羽翼逐渐丰满,野心逐渐增加571。在晚明的特殊环境里,土著军事首领实有理由对自己在明朝政府结构中的地位感到不满,他们也拥有发泄这种不满的手段,以对抗控制云南文武统治机构的组织,即世袭勋贵沐天波的组织。
此一形势最终导致了专权自恣的土司沙定洲的叛变。他于1646年1月夺取云南府,试图取代沐天波世守云南。沙定洲篡夺了沐氏之位,击败了大部分沐氏军队,并使之听命,大多数明朝文官和其他土司也因受他威逼而勉强服从。但是沐天波及洱海道副使杨畏知与几支忠明的部队坚守云南西北部,沙定洲无法把他们消灭572。于是双方进入了相持状态。其后,一个土兵将领(此人以前曾在湖广结识张献忠部下诸将)得知孙可望已到贵州,就邀请他入云南,并向他保证,只要他能除掉沙定洲,即可在云南取得显要地位;云南双方的僵持因此打破了573。
于是在1647年4、5月间,大西军余部在为沐氏复仇、恢复明朝秩序的借口下,攻入了云南,他们在进军中不但无情地攻击沙定洲及其拥护者,也血腥地镇压了云南东部民众反对这又一次叛军接管而作的抵抗。沙定洲不久就被逐出云南府,向南逃回其据点阿迷。于是在西北部的沐天波及其他明朝官员与大西军开始了谈判。孙可望声称,自己已脱胎换骨,从叛逆变成了明朝忠义之士,但是沐氏及明朝官员对此有怀疑,不过他们同意,只要孙可望不再劫掠,并彻底消除沙定洲的活动,他们可以与之合作,让孙氏集团借用他们的威望。此一设想,在1648年秋由李定国实现了。李定国自从其“弟兄们”进入云南以来,他已进行了最为艰苦卓绝的战斗574。
同时,孙可望在云南府建立了一个政府。他要求各地像缴税一样捐助,以此建造了皇宫式样的大殿及其他建筑,举行了科举考试,任命了各类官员,包括传统的六部首脑,并以帝王姿态接纳重要人物。他为“兴朝”铸造钱币,在云南府附近重新分配土地,以设立“官庄”,对盐井、矿藏及饲料资源加以控制,征发当地工匠575。孙氏政权相对来说是暴还是仁,各种记载说法不一;但是就大体而言,他的统治看来比他故主张献忠所为更有秩序,同时也避免了张献忠那种极端的残暴。他首次向肇庆的永历朝廷派遣使者,要求加封王爵,其原因正在于他一心要南面称王。(按:四位大西军头领入云南后所获封的“王”,照明朝体制,只能算是第二等的郡王;而孙可望所要求的,是第一等的亲王。若有了这一封号,等于是正式同意,孙可望的地位高出于他的三位“弟兄”之上,暗示他是张献忠的当然继承者;若是他将来行使监国乃至帝王大权,也能名正言顺。)但是孙可望未能使其同党明确认可他这一政治计划。因此,永历朝廷迟迟不授以王爵,有关封王之事所得到的消息各异,都使孙可望深感挫折,大为愤怒。
李定国与孙可望有隙,其起因正在于孙可望的骄横。李定国承认,在张献忠四个继承者中,孙可望居于首位;但是他对孙可望巧用行政措施与政治手腕抬高自己的地位,是耿耿于怀的。另一方面,李定国将略优长、天资聪明,又深得军心,孙可望对此是既嫉妒又提防。他认为李定国不从号令,因此在1648年春,下令当众鞭打李定国。鞭打过后,孙可望泪流满面,抱住李定国,把他扶起,并委以更多的抚绥重任;但是,李定国心中的怨恨是不会褪掉的,尽管他显然还是对孙可望抱有手足之情576。此事表明,明朝的文武摩擦,即使在明朝反叛分子中间也发生了。但在当时,因保卫西南基地为当务之急,这种摩擦缓和了下来。
1650年春,孙可望派兵重回贵州,把上次攻入该省时未曾遇到的明军轻易击败,并予以收编;于是他就着手在首府贵阳建立第二个大本营577,并以此为中心,向南、北、东三方出征。随后是一连五年的攻势作战,迫使清军几乎完全退出西南各省,清朝对湖广西部与广东西部的控制也受到了严重威胁(见地图13)。
在四川西部,孙部诸将收复了大部分主要城市,迫使吴三桂军放弃了保宁以南所有在四川的据点向北后撤。但是他们试图压服四川南部各军阀,就没有那么成功了。此外,长江沿岸四川、湖广二省交界地区,长期以来为李自成余部占据,孙部诸将想与之合作,也没成功578。孙可望本人则负责向湖广西南部的进攻。他不是亲自上阵,就是督战,首先在1651年收复了沅州这一湖广、贵州二省的“门户”。然后在1652—1653年冬,他又派遣部下最好的将领之一从清军手中夺得了郴州,(指瑕:孙可望部是怎么从沅州隔着宝庆、永州打到郴州的?这一时间段李定国部正在那一带活动,孙可望部又是怎么夺得的?部下最好的将领之一是谁?白文选、冯双礼还是卢明臣?无论是谁那个时间段都不在郴州。)他本人则率军进入了宝庆地区。虽然他在这次战役中被击败,回到了贵阳,但在1655年春,他的另一个主要部将沿沅水迅速而下,几乎把常德攻下579。(指瑕:其实此次战役相当失败。该年,刘文秀率卢明臣、冯双礼准备水陆并进,攻取岳州、长沙,进窥武昌,第一个目标就是打下常德,当时春水方生,卢明臣率水师沿沅水顺流而下迅速攻克了桃源,但步兵却因暴雨无法及时赶到常德,清军从容调兵增防,在常德城下设伏,结果卢明臣部在常德城下遭遇优势清军围攻,大败,水师损失殆尽,卢明臣落水身亡。刘文秀中途听到消息就撤回了。)
但是更辉煌的战果是李定国向东南的进攻,显示了明季“流寇”的几项最显著的特点:以大量兵士神速推进,突然袭击(李定国懂得如何出色地运用西南的战象以及土兵的火器技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指挥风格;不愿,也不能保有根据地。1652年7、8两个月,李定国首先攻下了宝庆及湖广西南部西端的其他关键城市,以保护自己的后方。然后他亲自率军,火速向桂林挺进,于8月7日一举攻下580。这一次大胜利,使广西清军占领区纷纷倒戈,投向明朝方面,只有梧州尚在清军之手。但李定国并未留在桂林,而在下个月再次进入湖广,派别部攻占广东北部的连川,并遣前锋夺取长沙,他本人则占领了衡州。(指瑕:广东北部并无连川,只有连州、连山。长沙、衡州都是李定国进攻广西之前就已占领的,而不是桂林战役结束后占领的。)但是李定国尽管取得了这些胜利,却未能守住收复的各城,于1653年3月底,被迫杂乱无章地撤至广东西北部581。(指瑕:李定国部由湖广永明经龙虎关撤往广西,而不是广东。)
于是李定国集中精力进攻广东。1653年初,他发动了初次攻势。这实际上只是从湖广撤退那次行动的延续。虽然广东西北部的清军措手不及,李定国因而得以攻击肇庆,威胁广州城,但是这种进攻大体上只是试探性的。同年秋天,他到广西中部休整,沿途未能收复重被清军占领的桂林582。
李定国第二次进攻广东,时间更长,考虑也更为周到。1654年春,他通过广西南部进入了雷州半岛的中央。该地在上一年曾发生了几次亲明的严重暴乱,因此李定国很受民众支持,得以在高州建立大营,驻扎了5个多月,未受清军反击部队的骚乱。在此期间,他得了重病,身体虚弱583。但到了9月底,他已复原,于是就能推进到珠江三角洲西南部,并开始围攻新会。在他攻占广州城的计划中,新会是重要的一环584。但他水军力量不足,屯兵新会,不能前进,曾两次向福建的郑成功求援,然而因各种原因(详见下文),援军未能及时到达。新会坚守不降,1655年1月底,清军又从江西派出了援军,李定国军大败。清军追奔逐北,李军受了重创,一路逃回广西南部,在南宁重整败军,人数只剩下了几千585。
经过这一切之后,那些明朝的叛军兼义军,已不再能保有多少自清朝手中夺回的土地了。但是清朝方面对西南发生之事,似乎没有可靠的情报来源,因而对敌人的突然攻势大感震惊,损失惨重。最著名的清军总兵官徐勇,在守卫辰州之战中阵亡。大将军孔有德在李定国军涌入桂林时,把大部分家人杀死,然后与妻子一同自焚。满洲亲王尼堪受北京特别委托,处理湖广局面,在衡州附近遇李定国伏兵,被杀。清军在广州的指挥部受到了重创586。清朝方面于是对自己在这些地区的控制是何等的脆弱,逐渐有了更确切的认识。因此,在此后相当时间之内,他们集中主要精力,巩固自己的阵地,并在四川、湖广、两广的占领区内,进行认真的绥靖,对于更蛮荒的大西南,则采取了观望态度587。
李定国取得惊人胜利的消息,未能使孙可望完全满意,因为李定国在孙氏手下诸将中,声望早已如日中天,现在的每一次胜利,只能使他声望更增,在政治上更易受损害。事实上,在大“东征”的这几年中,孙可望在湖广西部亲率或指导了几次军事行动。这些行动对李定国而言,可能是威胁多于增援。据说孙可望还不止一次企图派人刺杀李定国588。此外,李定国1653—1654年间一直在两广,不回贵州,个中原因可能在于,他不能忍受孙可望因嫉妒而对他加以控制,但也不愿公开决裂——不论这是由于他与孙可望及其部下以前有兄弟情谊,还是因为他对于和这些人的联军开仗,没有取胜的把握。
现在的永历朝廷,尽管完全丧失了能力,但在西南地区存在着这样一个朝廷,使孙可望和他的一些部下之间的分歧加深。因为有了这一朝廷,表明在孙氏之外还有一个取得合法地位的来源,还有一个效忠的对象。孙可望建立了传统文治政府的各部门,使之凌驾于诸将之上。他手下将领跟李定国一样,对此感到不快,就有可能转向永历朝廷,因为永历朝有更为正统的明室背景,而且实际上也不会对诸将加以管束。(这并不等于否认:李定国新近对明朝的效忠,可能确是出于至诚。)孙可望当然也看出,朝廷对他的擅权自恣,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他用了巧妙的手法,一方面设法从朝廷获取它所能授予的最后点滴的权力,另一方面则逐步削弱朝廷,使之变得无足轻重;他的集团很可能想以此最终取代明朝,成为君临大明子民的政府。不过,他的企图后来并未成功。他显然既缺少领袖群伦的魅力,也没有足够的手腕来达成这一目标。孙可望眼看朝廷现在可以一口吞下,就加紧侵蚀其权力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但他越是这样做,李定国及其他诸将就更能以此为主要理由疏远他,同时对陷于困境的皇帝及其残余朝臣的求援,也更易于作出呼应。
1650年12月,永历帝一行抵达南宁(在广西南部),就在此之前,孙可望率军自云南返回贵州,为他以后的扇形攻势建立基地。次年春,他派兵“入卫”南宁,并提议,以其大营所在地云南府为行在所。他的手下人还以血腥手段谋杀了几位官员。这当然并非出于偶然,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反对孙可望封为秦王的主要角色。皇帝在此威逼之下,轻易地听从了居间斡旋的大臣,如马吉翔之流的建议,正式授予孙可望秦王的爵位,同时还赐国姓,赐新名589。这是加固孙可望权势的及时之举,因为他当时正从贵阳向东、北二方发起进攻。
与此同时,清军也在广西东部稳步推进。1651年秋,永历朝廷被迫逃离了南宁。到底要逃往何处,朝廷内部看法不一。但是,若不想奔往沿海,也不想避地南方的安南,那就只有设法前往云贵的孙可望地盘,别无多少其他选择。于是在1651—1652年冬,皇帝一行再次长途跋涉,一路上人数逐渐减少。他们途经广西最西南端一个危险的土著聚居区,有一次,清军在后追赶,相隔只有半日路程。他们最后受到孙可望一名部将的接应,被带到了云南的广南,抵达时已是1652年2月底590。但是,孙可望并没有礼遇朝廷,也没有像以前他建议的那样,在云南府重建朝廷(这样可能贬损他自己的威势),反而把皇帝及其约50人的七零八落的从亡诸臣,送到了贵州西南角一个僻远的前哨安龙(明安笼所),就好像把这一行人放到了他自己的后口袋中。朝廷陷于此一悲惨境地有4年之久,所处环境日趋恶劣,吃的只是当地的粗茶淡饭,被剥夺了仆役的伺候,孙可望手下人对待他们,大体上就像对待许多头牲口。
而同时孙可望在贵阳,举止排场更像帝王,发布他自己所撰的经书注解,供以后科举考试之用;铸造自己的官印;建立太庙,以朱元璋居中,张献忠居右,他自己的祖父居左;据说还准备篡夺帝位,开创“后明”朝591。但是他对历经蹂躏的贵州人民,却没有做任何事来改善其境遇,可能还使他们生活更惨。一位当时行经贵阳的旅客写道:
塘兵时被虎驮去,岭头坡足骸骨枕藉。商旅绝迹,止见飞骑往来冲突。又见割耳劓鼻之人,更有两手俱去者;犹堪负重行远,惨甚。即有奇山异水,不敢流览。592
永历帝当然想从这一日趋恶化的境地脱逃。他逐渐得知李定国的军事胜利以及与孙可望的疏离,于是多次向李定国秘密求援,最后在1654年春初,向李定国提出,只要能把朝廷从孙可望的压制下解脱出来,就授予一等王爵之位593。孙可望通过战场上的探子及安龙的奸细,获悉了这些求援之事;于是他的亲信于4月进入朝廷住所,开始审査,想把所有参与招邀李定国的官员都清査出来。永历帝出于胆怯的天性,不承认自己应对求援一事负责。5月6日他允许处决“安龙十八先生”,做他的替死鬼594。
永历朝廷在安龙处于不利境地之时,李定国正深陷于湖广与两广的战役中,不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处于不利地位,不足以与孙可望对抗,来响应皇帝的吁请。此外,他可能希望先夺得广东,然后在该省,而不是在边远地区恢复朝廷。总之,他对永历帝的第一次吁请未作承诺。他在广东之战失利,并受到粤东清军新攻势的压力之后,才把注意力转向安龙595。
因此,李定国开始政治冒险行动之际,正值其实际力量低落之时,他以后之所以能成功地对付孙可望,正在于他有办法与孙氏部将合作,对待他们既体面又公平,表示真心关怀永历朝廷,并依赖自己优于将略的名声。孙可望愈是派部下去伤害、威胁、对抗李定国,部下愈为李定国所吸引,或公开服从其指挥,或暗中受其影响。因此,当李定国在1656年春初向安龙进军时,孙可望派去拦阻他的将士,就有人悄悄和他合作。2月16日,李定国抵达安龙。孙可望先已派手下一名重要将领在李定国到达之前把朝廷移到自己严密控制的地区,但此人非但不抵抗李定国,反而协助他。李定国于是在4天之后护送永历帝一行离开安龙,前往云南。然后迅速在云南府展示武力,迫使孙氏部下诸将同意此一政变。3月底,永历帝被带往另一城市,并命名为“滇都”,(指瑕:云南府即今昆明,永历帝就是转移到了这儿,并改云南府为滇都,而不是“另一城市”。)然后开始授官封爵,多半是给李氏部属与盟友,试图重建一个多少像样的朝廷596。
在孙可望和李定国的权力斗争之后,是悬而未决的长期间歇。二人都觉得在自己地盘内没有足够安全,不能下决心向对方出击。暴动、叛逃、哗变,在双方营垒内都有发生。李定国几次设法与孙可望和解,先是送回在云南扣留的孙氏家人与卫士,后是派遣谈和使节。但是孙可望继续持好战态度,不愿媾和597。
到了1657年夏天,孙可望更是听信别人,发动了惩罚李定国的战争。他没有料到,劝他开战的人,已安排好在紧要关头投入李氏营垒。9月底,孙军越过贵州西部,1个月之后,在云南东部的交水与李定国军接战。此时,孙部几位主要将领按照事先的秘密计划倒戈,并告诉李定国另一支部队已从侧翼出发,攻击李军后路。孙可望的计划于是完全挫败,当他横越贵州后撤时,甚至所遣留守贵州的将领也敌意相向598。孙可望此时既愤怒,又疲乏,一路后撤,退至湖广,只剩下家人以及大约400人的一小支卫队。1657年12月19日,他向宝庆的清朝当局投降,一肚子怒气发泄在出卖他的人身上,敦促清军让他“雪深仇”,“洗大耻”,为清军打头阵,进攻四川、贵州、云南599。清朝方面对孙可望不够信任,不派他指挥任何战役,但还是优待他,很高兴又从明朝方面获得一件奇货。
在东南沿海高举明朝大旗的集团,没有如此破坏性的领导层内的分裂,也没有文武之间的冲突。自1651年至郑成功死前不久,他的权力在10年内是至高无上的,这一权威使他成了带传奇色彩的民族英雄,吸引了历史家、剧作家、小说家的想象,不仅在中国,甚至在日本也是如此600。从事大规模商业和军事活动的郑氏政权,虽然颇为复杂,属下有上千个能干的官员,事实上是特殊区域内的一个特殊政府,但是郑成功从不允许任何文武分裂发生在他的组织之内。
而且这是他自己的组织。永历朝廷距离甚远,皇帝与郑氏的交通既慢又不经常。因此,郑成功虽然在礼节上恪守臣职,忠于皇上,甚至谨小慎微,不“敢”接受册封,而事实上他有充分自由,做任何自己认为合适的事。他在自己的领地内其实是王。1651年春,他竭力想援助广州的永历军队,非但徒劳无功,还危及了自己尚脆弱的组织。在此之后,他只有在偶然的场合,当永历朝廷的号令与他自己在东南的计划适合一致之时,才起而应命。与此相似,他虽采用了许多明朝正规军事组织的形式和名称,但就总体而言,他的海陆军有自己特殊的结构与运作方式601。明朝皇帝在原则上是乾纲独断,而在事实上是绝对无能;因此应付皇帝令人沮丧;关于谁应当“辅佐”皇帝,内廷与外朝人物(包括各自的武人盟友)一直争执不休;对于朝廷的神圣“纪纲”,御史有代天司察之权,纪纲若有违失,即予抨击。而对郑氏来说,这已不成问题了。因此在东南地区,只在象征意义上的有明廷,而实际上并不存在。郑成功若要协调自己与明廷的利益,并竭尽所能致力于复明事业,必须要有灵活与独立行事之权。东南当时的情况使他所愿得遂。
郑氏的崛起,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其中不可忽视的是他自己的性格。郑成功机警聪明,精力充沛,孜孜不倦,具有领袖魅力,能使意志坚强者为他竭忠尽智,同时又能以铁腕对这些人加以约束。显然,他天生能在任何环境中坚持到底,他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他有强烈的自豪感与荣誉感,但愿制人,不愿受制于人。这一切表明了他内心深处桀骜不驯的个性,在当时当地的特殊情况中,这一天性使他成了政治上的强者。
当然,郑成功所遵循的道路,已由他那位同样出色的父亲所开拓,但是可以看出,他并不仅仅是在郑芝龙离开福建时继承了那个组织完备、运作良好的集团。与此相反,他奋斗多年,点点滴滴地重建和加强了郑氏机构,并逐渐排挤了与他争权的长辈。他在此过程中,不仅学会了如何统辖部下,还懂得了如何培育部下;他不想为此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由此而引起的坚韧不拔的谨慎态度,以及战略洞察力与组织能力,使郑成功不但是清朝的可怕对手,也令沿海的独立军阀望而生畏。尤其是1648—1650年间的广东东部之战,使他获得了切身的教训,懂得要保存实力,避免直接攻击敌方要塞,要建立后方基地并确保其安全,还要从各地的强宗大族征集其各自区域内的特产,并输送这些“贡品”。这种种的教训,使他建立了高效率的后勤系统(既满足正常给养,又可供临时赏功之用),并喜爱恩威并施的心战。在恩的方面,对待有才干的昔日敌人,既要宽厚,又要尊重,以此使其效力;在威的方面,则是使用事先熟筹的威胁以及展示令人生畏的实力,以迫使敌人就范,而不是径直使用搏虎全力,以虚耗己方。郑成功就是这样持续地培植自己的物质力量及领袖魅力,并把驭人之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从而使清朝在其征服明朝与绥靖地方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最强劲的对手。
郑成功利用其多方面的才能,不仅使清朝受挫,而且还取得了组织海上事务的机会。明朝政府对海上事务的政策,不是消极、漠视,就是仅留意自卫,因此海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正好由郑氏来填补。尽管官方对海事的态度是冷淡或阻挠,但在16世纪下半叶,中国沿海与东亚及东南亚各贸易中心之间的交易,在量与质两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增加,尤其是称雄海上的欧洲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所主持的侵略性的商业企业出现之后,情况更是如此602。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口,有很大一部分除从事国内沿海贸易外,逐渐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对外贸易以为生计。对这些人来说,任何组织,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只要能稳定或促进他们的贸易,至少不要过多进行干涉,都是可取的。这类组织的规章、税收、维持治安行动,他们看来都愿意顺从。明朝政府在这方面,未能有积极而肯定的行动,于是便由郑芝龙及其族人、子弟之类人物取而代之。这些人以“保护”人民为由敲诈勒索,而人民又不能从其他方面得到保护。因此他们乘时得利,终于建立了某种海上政府。
郑成功在抗清斗争中,不但利用得自维持海上治安及控制“海关”的收入,也利用从海上贸易获得的利润。他还把大量用于海事的人力、制造技能及船舶,从商业转到同样能获利的战争事业603。这样做,使组织松散的海上社会,把精力用于战争,而不是用于民生日用,当然有其限度。在此期间,许多中国人迁移到更远的地方,如台湾、暹罗、吕宋,乃至南美洲海岸,以此逃避郑氏的榨取,从郑氏连年征战的战乱中解脱出来。但是郑氏这一运动的规模与活力,以及沿海民众与郑氏之间的高度合作,证明了只要郑氏一直能得胜,许多其他的人可以与他分享利益,或是易于与他的利益相适应,郑氏在沿海贸易为他所控制的地区,因此得以有一个出色的情报网。这也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郑成功崛起的另一因素,是清军不论就所取姿态还是就地缘政治而言,都易受郑氏所用战术的伤害。满洲人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后裔,以其高超的骑射传统而自恃,因此擅长陆战。他们虽然相对说来已颇能适应河流湖泊的战斗,但碰到海战就惶惑恐惧。不过,在陆上所向无敌,已足以使他们能征服沿海狭长地带以外的中国其余部分。因此,满洲人在得到与之合作的中国官员的增援之后,还是没有把消灭郑成功列为优先考虑的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般说,这些中国官员自己对海上事务也是不重视或看不起的。郑成功于是赢得了时间来开创他的运动;清军若是早一点就集中力量于福建,他是不会如此令人可怕的。
但是,即使清军能很快克服其厌恶处理沿海地区的倾向,所需费用之浩大,也使他们望而却步,不能采取迅速有力的行动来对付沿海的抗清力量。浙江东南端、福建及广东最南部,相对说来不易到达,农业资源也有限,要运兵到这些地区去,并在那里保持庞大驻军,尤为困难,开支也尤为巨大。若是采取驻守战略,则需要大量兵员来守卫曲折海岸线上每一城市,以防“海寇”袭击。但是,如果要到海上义军的地盘内去对付他们,就必须白手起家,建立一支清朝海军(因为骑马驰骋的满洲人总是怕水,落水和翻船的次数太多,因而对征用来的船只和水手非常不放心),所需费用太大,难以支持。
因此,清朝首先做的,是尽力设法与郑成功达成妥协,也就毫不足怪了。即使到了1661年,他们已能集中主要力量于沿海地区,但他们选择的,还是尽量完全控制陆地,亦即把全部沿海居民向内迁移,多至数十里,造成一个无人地带604;而不是扬帆海上,追逐敌人。清朝这样做,目的自然在于使郑成功军得不到立足点,也失去攻击目标。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想打击郑成功的要害,因为他永远需要陆地上的物资,特别是那些不能在船上长期大量贮存的笨重货物,诸如粮食及其他大宗食物、淡水、金属矿石、供取火及修船用的木材,还有就是建造与维修大商船及战舰所经常需要的能工巧匠605。
厦门是郑成功军事活动的大本营,曾一度遭受威胁。1651年春,郑成功确立了对厦门的完全控制。在此之后,他就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军事准备,在金门建造了一个特别的训练营地,设立了一个机构来监督武器与甲胄的制造,还多少采用了标准的明朝兵制,把海陆军各一分为四606。郑成功的军事组织愈益成功,两边观望的武人加入的也愈多,而且郑成功又收编了族中长辈的部队,他的海陆军人数因此有了显著的增加;此外,当时鲁监国政权受了重创,于是这年冬天,残余的鲁王水师也从属于郑成功,他的军队因此再度得到了扩充(见第四章)。郑氏这一军事准备的最直接目的,是猛攻附近的漳州府以为报复,战事自1651年秋延续到1652年秋。在此期间,郑氏军队封锁了泉州港,夺取了几座县城,险些使漳州府城穷饿而屈,还获得了清浙闽总督陈锦的首级607!郑成功上次攻入广东潮州府,清朝方面已大感不安;不过潮州毕竟更为僻远,而且郑氏攻击的主要对象,也只是一大批其他的鼠窃之辈。但是郑氏这一次的攻势,令清朝如芒在背,必须有所行动。不过,清朝也知道,即使对漳州之役作最起码的回击,就国库、军队及福建人民而言,代价都是惨重的608。
于是在1652年9月,清朝对在北京的郑芝龙的行动和京外联系,有礼貌地施加了更多的限制,以提供“保护”。11月初,顺治帝发起与郑氏议和,旨在以谈判使郑成功就范。这场相互遣使的议和其后持续了两年之久609。顺治帝在赐新任浙闽总督的敕中解释说:
近日海寇郑成功等,屡次骚扰沿海郡县。本应剪除,但朕思昔年大兵下闽,伊父郑芝龙首先归顺,其子弟何忍背弃父兄,甘蹈叛逆?此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郑成功等虽有心向化,无路上达。又见伊父归顺之后,睿王令人看守防范;又不计其在籍亲人,作何恩养安插。以致成功等疑惧反侧。朕又思郑芝龙既久经归顺,其子弟即朕赤子,何忍复加征剿?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郑芝龙作书,宣布朕之诚意,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如执迷不悟,尔即进剿。如芝龙家人回信到闽,成功、鸿逵等果发良心,悔罪过,尔即一面奏报,一面遣才干官一二员,到彼审察的实,许以赦罪授官,听驻扎原住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闽广东海寇,俱责成防剿,其往来洋船,俱著管理,稽察奸宄,输纳税课。若能擒斩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610
新任总督作了相关的稽查,逮捕了1651年负责袭击厦门的官员611;郑芝龙也发信作首次试探,看其子是否愿意开始议和,信中也承认,其子对清朝官员的轻率行动作有力反击,所为是正当的。但他警告说,若战事继续,则“骑虎难下,兵集难散”612。
郑成功似乎对这次通信感到意外,但一旦看清了事实,他就兴致勃勃地投入了这场纵横捭阖,做生平最狡诈的表演,先是卑辞厚礼,故示谦恭,故作悔悟之态,以讨好清使,后来又向他们表示轻蔑,气焰熏天,不肯转圜。当时的官员尽力想发现,郑成功心中究竟作何想法,但一无所获;这段时期出色的文献也提出了如何作出解决的问题,结果还是令人茫然。他真的想投降清朝吗?还是故弄狡狯,利用议和赢得时间,以充实战备?下面我想作一些判断,但根据现有证据,要作出确实无误的回答,似乎还不可能。不过明显的是,郑成功在议和过程终了时,比开始时力量更强,而清朝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实际上却成了输家。在此还应当注意的是,若是郑氏地盘内有明廷存在,他就不可能放手去做,这样的议和也就不会进行下去。
1653年6月初,清廷强调,父子共同效顺一朝,实至美之事;并向郑成功指出,以前清廷所为,确有令他愤怒之处,现在已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更提议: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充泉州总兵官,有在福建沿海防剿海寇、管理与稽察海洋船只、收纳税课的特别权力;郑成功所部官员,还可照旧统辖,并食国家俸禄,但最终他还是要向清朝督抚负责613。郑成功在这场使节往来中,回禀其父,“矜诞”如昔:
夫既失信于吾父,儿又敢以父言为信耶?……夫归之最早者且然,而况于最后者。……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其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于人乎?且以闽粤论之,利害明甚。何清朝莫有识者?盖闽粤,海边也,离京师数千余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兼之水土不谙,死亡殆尽。兵寡则必难守,兵多则势必召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清朝不能效本朝之妙算,而劳师远图,年年空费无益之资,将何以善其后乎?614
尽管郑成功摆出好斗姿态,他在提议中所说到的清朝方面的失策,被清朝领导人物理解成想讨价还价——要供养他的部队与官员,区区一个府是不够的;单是一个总兵官,他嫌官阶太低,不足以控制部下;诸如此类。顺治帝虽然不愿把郑成功所要求的三省地方悉数交付给他,也不愿封他为王,使他与吴三桂平起平坐,但还是愿意给予四府,而不是一府,并授以靖海将军之号,以使双方交易易于达成。所有清军将从福建沿海地区后撤,准备移交郑成功统辖,以便他前来与清朝高级官员作出安排时不必有所顾忌615。郑成功向其下属说:“清朝亦欲绐(贻)我乎!将计就计,权措粮饷,以裕兵食也。”616
使节一来一往于郑氏大本营与北京之间,至少需时两个月,郑成功对此非常清楚,于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议和期间清军当撤出沿海地区的承诺。他声称,“腹决不可枵”,立即派兵进入南起潮州、北止福州的各地,实际上占领了漳州、泉州二府的全部沿海地区。清朝当局对这类行动的反应是:温和的抗议,隐约其词的威胁,以及略用武力,但收效甚微。郑成功使用了各种手段,从击败拥兵称霸的小头领,并胁迫其同类臣服,到向避难山中的士绅领袖赠礼物,致问候,因此他在短期内从一个半府征集了数量可观的钱粮,超过了隆武朝廷自福建全省所收纳的赋税总数617。
郑成功的一贯作风是,即使在谈判中也向对方持续施加压力(以此证明,他不是因软弱而议和)。此时他也依此惯例,命张名振回到在崇明岛西南沙洲的营地,尽力骚扰长江口附近清朝的驻军、城市、防御设施,以及大运河交通。张名振为贯彻这一命令,作了三次大胆的进攻,一次在1653年秋,另外两次分别在1654年春初与春末。直到1654年7月,他才被迫撤出崇明岛基地618。此外,在和议期间,郑成功还向李定国及永历朝廷发信,要求他们从西面攻击清军,造成“首尾交攻”之势619。
1654年春初,郑成功收到清朝诏书,要他回福建,正式接受新的封爵与权力,但他只派了几名使者前往。使者以为,福建是他的本土,到了此地不愿屈节为“宾”,因而未受接见。此后,在3月的第三周,清使允郑氏所请,前往距郑氏所在不到一半路的安平相见。郑成功在安平大摆宴席,款待清使,但不肯接受清使携来的印敕。他拒绝清使所提授予数府的建议,声称即便数省土地,也不足以供他海陆各军的给养。他公然提出,“高丽朝鲜有例在焉”,要求清朝“另罄外国宝贝以赠之”620。清廷第一次“招抚”郑成功的企图,于是以莫名所以的失败而告终。
许多清朝官员对郑氏的看法,自然因此而趋于强硬。清总督写信警告郑成功,应正视现实,并指责他悖理、欺诈、不孝,虚耗人的时间与精力,危及其父及家人,甚至使明朝的事业蒙羞621。清左都御史以为,应当把郑成功置于正规的清朝当局及行政机构之下。
气傲志高,心雄胆大,明明要挟。虽然归顺,实怀二心。以职愚见断之,将来为东南大患者,必郑成功也。从前飘泊海岛,脚跟不定。今得盘据于漳泉惠潮之间,用我土地,养彼人民;用我钱食,练彼精锐;养成气候,越显神通。将来求索粮饷,扰害地方,迫胁官吏,目无王法,日强日骄,何所不至。622
但是清庭高官听从郑芝龙劝说,再次尝试和议。这一次所用的使节,是郑成功一向与之亲睦的两个弟弟。顺治帝在8月向郑成功发了措辞严厉的谕旨,告诫他应合情合理,有话直说,并警告他,应即时作明智的决断,否则要面对严重后果。同时,相当于大学士的一位清朝大臣受命赴福州,再度与郑成功议和。这位主要使臣于是小心翼翼,南下至泉州。在郑成功的热情邀请下,10月26日,几位使者由郑成功之弟及继母陪同,怀着更加焦虑的心情重回安平。623
接着是一幕长达一月之久的和议拉锯战。清朝方面坚持,郑成功在接受清廷所授新的官阶、职务及特权之前,必须先按满洲式样剃发,作为服从的象征。但郑成功反对,认为无论如何,只有在他同清廷使者面谈,更确切地获知(亦即更激烈地讨价还价)他的新官阶究竟为何之后,才能作出如此的承诺。在这次和议期间,事出偶然,郑成功接见了一位自永历朝廷归来的使节,还收到了李定国的请求,要他前往援助,同攻广州。郑成功当然不会公开承认有这类接触,当时也不会响应李定国的吁请;但是清朝方面对此有所风闻,于是更有疑虑。总之,清使觉得有充分理由,对郑成功指责清朝狡诈、好斗,予以反驳624。
当清使表示失去耐心之时,郑成功写了一封亲笔信,说道,“欲接诏,欲剃发”!但又抗议说,清朝不论是对待他,还是对待和议,都是既无足够诚意,也不够庄重。另一方面,郑成功之弟及几位长期伺候郑芝龙的人,见到他涕泣涟涟,说道,若和议再度不成,他们自己的性命及郑芝龙的性命都将难保;郑成功回答说,他们不一定会遭祸;又说,自己所志已决,不愿再听到谈论此事。郑鸿逵应郑芝龙之请,亦以同样说辞劝这位侄儿,成功的答复是:“大义灭亲,筹之早而计之决矣。”625在1654年11月的第一周内,当清朝使臣确信郑成功并无归顺诚意之后,立即从闽南撤回,随后向北京禀报,和议使命已完全失败626。
郑成功在致其爱弟的临别信中再次抱怨说,清朝使节缺乏大臣气度,举动轻率,坚持要他及部下剃发,而且四府之入,亦不足以养他的军队。
大抵清朝若信兄言,则为清人;若不信兄言,则为明臣而已。……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627?
他在致其父亲的信中,总结了对整个和议的看法:
和议实非初心。……不意清朝以海澄公一府之命突至,儿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儿又不得已接诏以示信。至于请益地方,原为安插数十万兵众固圉善后之计。何以曰“词语多乖,徼求无厌?”又不意地方无加增而四府竟属画饼。欲效前啗吾父故智,不出儿平日所料。遽然剃发之诏一下,三军为之冲冠。……在清朝罗人才以巩封疆,当不吝土地;在儿安兵将以绥民生,故必藉土地。……天下间岂有未受地而遽称臣者乎?天下间岂有未称臣而轻剃发者乎?……天下间岂有不期信以心而期信以发者乎?……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大抵清朝外以礼貌待吾父,内实以奇货视吾父。今此番之勅书与诏使之动举,明明欲借父以挟子,一挟则无所不挟,而儿岂可挟之人哉?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亦大幸也。万一吾父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又据报督抚行文各府,办马料策应大兵。……儿此时惟有秣厉以待,他何言哉?他何言哉?628
郑成功为环境所迫,忠孝不能两全,对此可能感到不快;但是他既已选择忠于国而不是孝于家,确实只能“不顾”居于清朝的郑氏之亲了。
郑成功与清朝当局,对于开始和议的含义,显然见解迥异。郑成功一直愿意“议和”,以求妥协,减轻战事。而清朝的目的一向是“招抚”,亦即使郑成功投降时感到满意。双方目的既已不同,相互猜疑又是如此之深,因此,虽能彼此接近,却永不能达成协议。至于郑成功真心所要求的究竟是什么,看来一直是某种半自主或自主的领地,像朝鲜或交趾(越南最西北部分)一样,最好能包括浙江、福建、广东这沿海三省。他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安排,可以保留头发,甚至还可认同于明朝。至于在他心目中,这样一块领地是和清朝永久和平相处呢,还是等待时机,徐图恢复明朝,那就无由断言了。
无论如何,在清廷看来,这样一种看法是完全不能容忍的。清朝沿海诸省官员,在第二次和郑成功唇枪舌剑一番,以不和而告终时,自然会迅速上疏,说早就知道会有如此结局,并咒骂郑成功背信弃义,请求清廷大张问罪之师629。于是在1655年1月23日,满洲世子济度被任为大将军,率军征剿郑成功630;而郑成功也在厉兵秣马,再次试图完全夺取漳、泉二府631。现在是双方都在准备厮杀到底了。
第七章 最后的抵抗,最后的失败
主要的有组织的拥明活动,在两个地区差不多同时结束。这两个地区相隔遥远,地理环境十分不同:一个是云南西南部与缅甸之间的蛮荒瓯脱地带,另一个是福建南部与台湾岛(当时大部分居民为当地土著)之间环境同样险恶的海上边界区。在最西南的地区,局势对永历帝而言是步步恶化,愈演愈烈,而在最东南一端,郑成功在给予清朝几次沉重打击,达到英雄事业的巅峰之后,方被击败,但在这两个地区,某些明朝的基本问题始终存在。虽然永历帝手下一行,最后剩下的人数很少,但这些人为了生存,必须互相争斗,甚至比以前更为不顾一切,在皇帝辅佐问题上的倾轧与怨恨,一直持续到朝廷本身的惨剧收场。郑成功未能将其运动扩展至中国腹地,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文武双方的运作方式不能相互结合。
1656年12月,满洲人开始策划向贵州、云南的大规模进攻,并定于来年春发动。但是过了1年多,即孙可望投降1个月之后,这场进攻才得以实施。1658年1月,联合进攻贵州的命令下达给三位大将军:吴三桂自四川南部,洛托自湖广西南部,卓布泰自广西东北部同时出发。1658年6月底,3支军队向贵阳地区集中(只有吴三桂在进军途中遇到了坚强的抵抗);随后3位将军,还有掌管全部西南事务的清朝经略辅臣洪承畴,在平越附近的兵营会合,计划下一阶段更为困难的攻势(见地图16)632。
与此同时,永历朝廷在云南府依然专注于分功与弥补裂痕,自从上一年战胜孙可望以来,“酣歌于漏舟”,沉迷不反。李定国则还是不能确定,在前孙可望下属中,哪些人能予以信任,因此忙于内部整肃问题,不能随意部署军队,尽管此时清军已临近的消息,造成朝廷的一片恐慌,但明朝方面对于如何在贵州设防抵御清军,还是迟迟不决633。不过到了8月,李定国在贵州西部划分了3个防区,以保卫从贵阳到云南府的北、中、南3条通道。他本人扼守中部据点关索岭,以阻止清军渡过北盘江,同时可处于最佳位置监督各将领,因为这些人的忠诚还是靠不住634。
1658年12月底与1659年1月初,清军再次三路挺进:北路吴三桂,得到几个土司的合作,攻入了七星关;多尼攻中路(该军已代替了洛托部),夺下了关索岭,在北盘江的北部渡河;卓布泰则取南路,在南段的罗炎渡过北盘江——三支军队向云南曲靖集中635。李定国在这次战役中,对清军先头部队取得了几次鼓舞人心的胜利,但是当清军倾全力进攻时,他的防御就开始瓦解了。他虽然拼命作战,挡住了多尼和卓布泰的推进,但处境愈来愈危急636。
8月7日,清军绕过或是穿过李定国军,越过贵州边界,进入了云南东部,永历朝廷于是逃离云南府,在沐天波带领下西奔。沐天波虽然自沙定洲叛变以来,已失去了军事实力,但是,现在朝廷必须穿过土官、土司的辖境,而在这些人中间,沐天波是唯一有影响力的朝臣。当时很少有人愿意考虑逃到中国西南边界以外,但他们还是希望,能在大理以东划定一条疆界线。因此,当永历帝一行(约4000人)于1月26日进入永昌时,李定国及其最强悍(虽已受伤)的残存部将白文选,即以2万人沿云南府以西的主要通道构筑了第二道防线,试图阻挡住清军的第二次推进。当时李定国本人来到朝廷,情绪激动,羞惭满面,坚决要求朝廷因战事失利而惩罚他。皇帝只得亲至李定国府第,诚恳解释说,朝廷不能对这样一位忠臣定罪。李定国这才同意收回自劾的奏本,继续视事637。
2月22日,吴三桂与卓布泰从滇池地区出击,通过大理以南各关口,一路上消灭了所有的抵抗行动。于是在3月10日,清军进入永昌。惊慌失措的永历帝一行则逃抵腾越,沿路被当地强徒及护驾军队抢掠不已(宫内女眷以前施舍珠宝,以供养军队,此时甚至皇帝的几件龙袍也给偷走了)。他们在腾越扎营,膳食没有白米,只有马肉,真不知以后的处境还要坏到怎样。李定国则准备在怒江以西,沿着磨盘山的曲折地形,作最后一次认真的抵抗。3月中旬,他精心策划的伏击,最终还是给清军发现了,接着是一场恶斗,双方损失都很惨重638。
李定国以前曾苦口婆心,劝说这位不情愿的皇帝:要是防御再度失利,不可投降清朝,致使他李定国的一切复明努力付诸东流,而应当权居缅甸一两年,“再看天命”。因此,当磨盘山一战之后,李定国率残部向萨尔温江上游南逃时,永历帝一行崎岖跋涉,于3月的第三周通过铜壁关入缅甸境,一路上不愿再南奔的士兵时有哗变,部伍大乱639。同时,清军亦因磨盘山之战而受到削弱,士气不振,而且粮饷也不足,因此只能在距腾越不远处略作搜索,不久便返师东归,未能继续追逐永历帝和李定国640。
在边界的缅甸一方,永历帝一行还剩1500人,物资极度匮乏,护驾兵士大半已逃亡。前来迎接的当地缅官说,当地的纯朴百姓感到害怕,只有一切外来的人完全解除武装之后,他们才能前来供应衣食所需。在此关头,永历朝司空见惯的痛史又重演了。这就是朝廷文臣对马吉翔的指责。同类指责以前一再提出,这次又重提,即马吉翔(他在云南府时曾任首辅)控制了朝政。更有甚者,他们还指出,今日皇帝的处境甚至比以前更为不利,究其原因,是定策只知求稳,处事但求妥协,而对这一切实际应负责任的,正是马吉翔。以前他们指控马吉翔迁就孙可望,甚至鼓励孙可望擅作帝王威福,并与其合谋杀害“安龙十八先生”;然后又在事后责备他出了这个逃到缅甸的坏主意;现在则诋毁他自作主张,屈从缅方官员的要求,使永历帝一行不但武装解除,甚至“不带寸铁在身上”641。于是这个在缅甸的小朝廷又经历了一场磨难,在此期间,“外朝”官员自命有理由指责马吉翔篡夺皇帝权力,使永历帝陷于大劫。令人起疑的是,这一说法与皇帝身旁一位小内监的回忆恰好相反。这位小内监并不提及马吉翔,大体上把皇帝说成是自作决定的642。
3月的最后一周,在缅甸的八莫城,永历帝及646名随行人员,在伊洛瓦底江上船,其余的900左右,则自陆路南行,双方打算在缅甸首都阿瓦会合643。但是,当皇帝的船队抵达井梗时,缅甸人就开始威逼和破坏了。他们声称,需要核实皇帝一行的身份,于是问及明朝后期缅中间礼仪之事。马吉翔自认不解明朝制度,因而对这类问题无法作答。缅人当然不会满足,直到黔国公沐天波出示印信,与缅人所保存万历年间敕书上所钤之印相对,才袪除了疑团644。
有几位朝臣,担心日后处境更为不妙,于是想让皇帝东行,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与李定国联络,但为马吉翔所阻止。据说马吉翔还应缅人之请,致书八莫地区的一位明将,说永历帝已由海路前往福建,因此该将领及其他明朝武臣应停止前进,否则其部下及其他在缅甸的明朝子民都将被杀。与此同时,走陆路的一批人抵达了阿瓦,殊不知前来寻找永历帝的白文选,已与缅人恶战了一场。缅人可能把这一批人也看成了一支脱逃的中国军队,可能只是为了报复;总之,他们向这批人发起了攻击,杀死了800余人,剩下的90人左右逃入荒野,据说有数人最后抵达暹罗645。
但在1659年6月的下半月,缅王派两艘节庆“龙舟”,将人数更少的永历帝一行自井梗遣送往南。不久他们就在阿瓦以北江对岸的者梗县某地定居了下来。各种设施颇为简陋,一幢带有竹篱的大茅屋由皇帝及其家人居住,其他人则须自己动手建造竹木屋。但是缅王向永历帝送来了厚礼,馈赠时仪式隆重。明廷诸臣数月来颠沛流离,这是第一次可以放松一下,略作享受了646。
明朝中国人所说的“缅甸”,所指的只是今日缅甸地理范围之内诸“蛮夷”王国及部落之一。洪武与永乐年间,明廷称这类政治实体为“宣慰司”(但并不指派官吏),规定须按期朝贡,从而确立了对它们的主权。其后,今日缅甸境内各邦与各族一直扰攘不安,明代所谓“缅甸”这一政治实体,甚至一度并不存在。但是到了16世纪中叶,这一“缅甸”国再度兴起,在万历年间向外扩张,征服了北面诸民族,最后越过向来不明确的中缅边界,侵入云南境内。在16世纪最后30年,云南明军与“缅甸”军以边界诸弱国为棋盘上走卒,相互攻击。到了17世纪初,“缅甸”再次正式成为中国藩属,但双方关系一直紧张,自万历末期以来并无接触。事实上,当时上缅甸地区诸邦,已开始承认“缅甸”为该地区内政治上的霸国,并接受阿瓦的某种行政控制。阿瓦后来成了前现代民族国家政府的中心,但在当时,这一过程刚开始647。
当时的缅王平德勒(Pindale),与其开拓疆土的前任相比,力量既弱,又欠果断。他同意永历帝避难,是出于仁心,但在清军征服云南之后,逃入缅境的明朝军队势必引起麻烦,对此如何应付,他心中无数。有几支军队,主要是李定国和白文选部下,不仅对今日缅甸东北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相当大的破坏,而且还威胁说,要在诸如善邦之类“缅甸”周围部族中间,重新煽起对“缅甸”人的仇恨648。
最坏的是,从1660年春至1661年春,这些部队或单独,或联合,几度逼近阿瓦,要求把永历帝交给他们,使缅人大为恐慌。即使缅人交出永历帝,仍不能获得保证,皇帝及其难以驾驭的支持者,会心甘情愿,离开缅甸国土,即便愿意,亦未必能做到;而且阿瓦在平德勒治下,并无足够兵力可以驱逐这些明军。马吉翔应缅人之请,让皇帝发布上谕,将这些劫掠的军队遣送出境。但是李定国、白文选二人,原已得知永历帝至沿海,并已乘船出海的敕文,而现在见此上谕,确知朝廷在阿瓦,但因某种原因不能与他们联系,于是二人更为愤怒,更觉沮丧。沐天波与其他几位朝臣,策划劫走永历帝及太子,前往李定国军营,但被觉察。因而有旨(据说是马吉翔所为)将几个策划者逮捕处罚649。
这类明军的侵扰愈益令缅人烦恼,缅人对待永历帝也愈益不敬,于是沐天波只得遵从缅甸习俗,白衣椎髻跣足,礼见缅王。到了1660年仲秋,朝廷一贫如洗,缅人供应的稻米极少,最后的点滴值钱之物(包括皇帝玉玺)也都拿出来疗饥。在此情形下,马吉翔一再受到指责:擅作威福,控制供分饷的宝物,并操纵其分配,借以利己650。
但是朝廷的厄运还没有到头。1661年6月,缅甸枢密院黑鲁叨(Hluttaw)一怒之下,废黜了缅王平德勒,并予处死,更立其弟摆岷(PyeMin)为王。摆岷治国更有活力,曾主动出击,抵御入侵者,赢得了国人的好感651。这次篡弑后不久,缅人令所有永历官员渡过阿瓦本地的一条河,参加向新王宣誓效忠的仪式,同时为如何处置明廷重作安排。沐天波听到这一消息,当即大怒,指责缅人冷酷无情,以奸计行诈。
况且尔宣慰司原是我中国封的地方。今我君臣到来,是天朝上邦。你国王该在此应答,才是你下邦之理,如何反将我君臣困在这里。……难道尔国王岂不知他是下邦?今天朝皇帝到此已经三年,不瞅不睬,是何道理?今又如何行此奸计?尔去告与尔国王,就说我天朝皇帝,不过是天命所使,今已行到无生之地,岂受尔土人之欺?今日我君臣虽在势穷,量尔国王不敢无礼。任尔国兵百万,象有千条,我君臣不过随天命一死而已。但我君臣死后,自有人来与尔国王算帐。652
次日(8月13日),所有永历官员满腔愤怒,被带出了缅人指定的居处,悉数受戮。同时,缅人骑兵驰入者梗永历帝所住的村庄,杀死了15岁以上所有健康男子,包括皇族中人。屠戮后留命的,只有这些不幸官员的大约340名寡妇孤儿。皇室中人不死的,也只有皇帝、太后、皇后、太子、公主、贵人、几名小太监、一名病残卫士。缅人把所有未死者赶出杀戮现场,监禁了三天,不给食物,不给水,也没有盥洗设施。然后,在寒冷的秋日,缅人准许他们回到原来住所,但不供应食物。最后缅王差人送来食物,并向永历帝致歉;永历帝在奄奄待毙的妇人中间,对此姿态,只能是痛苦的沉默653。到了此时,明朝体制上的皇帝辅弼问题终于是解决了,不过永历帝当时大概是不会有如释重负之感的。
缅人采取这类措施,可能不仅是显示一下新君主的决心,他们或许已在准备答应清朝的要求。云南的清朝当局,在洪承畴节制之下,所实行的政策是逐步巩固。这也是洪承畴一生事业的特点:恢复农业生产,学会如何管理土官,在各战略要地驻扎军队,镇压顽抗的土司与叛军残余,希望失败、冬季缺粮及夏季疟疾最后会使李定国军瓦解654。同时,洪承畴得到清廷允准,开始向缅人施加外交压力。1659年仲秋,他在《给缅甸军民宣慰使司札》中,说明了清朝的立场:
照得明运告终,草寇蜂起,……(我皇上)乃应天顺人,歼灭群凶,……惟献贼遗孽李定国,自知罪恶滔天,神人共愤,鼠窜云南,假借永历伪号,蛊惑愚民。不知定国既已破坏明朝全盛之天下,安肯复扶明朝疏远之宗支,不过挟制以自专,实图乘衅而自立。横肆暴虐,荼毒生灵。……有能擒缚解献,则奇功伟绩,立奏上闻,优加爵赏,传之子孙。倘或不审时势,有昧事机,匿留中国罪人,不惟自贻虎狼呑噬之患,我兵除恶务尽,势必寻踪追剿,直捣区薮,彼时玉石难分,后悔无及。至闻永历随沐天波避入缅境,想永历为故明宗支,群逆破坏明室,义不共天,乃为其挟制簸弄,势非得已。今我皇上除李自成、张献忠、李定国,为明复不世之仇。永历若知感德,及时皈命,必荷皇恩,仿古三恪,受福无穷。655
但洪承畴已不能亲眼看到他这谕札对缅人所起的作用了。他年已66,多年来为清朝竭忠尽智,双目几已全盲,于是在次月获准致仕。清廷按照洪承畴的建议,将全部云南事务交付平西王吴三桂656。
吴三桂及其满洲同胞一直在滇南的元江地区与土司作战,至为艰难。这些土司藏匿了几位李定国的家人,并在李定国怂恿下抵御清军657。吴三桂不像洪承畴那样主张渐进,部分原因是这一艰苦作战的经历。他于1660年5月上疏说,只要李定国、白文选与永历帝还在西南边界的缅甸一方,云南土著的叛乱就一日不得平息,清军就得永远面对忠于明朝的游击部队,拉锯战不息。云南清军的粮饷也已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为此吴三桂以为,边界上的持久战难以再支撑下去,发动一次最后攻势以尽速消除麻烦,更为可取658。
此一建议在清朝官员中引起了广泛的辩论。政府的财政,总的说来已很拮据,西南战事的开支亦已过于浩大。户部事实上已在惊呼:1660年云南的军事开支已高达900万两,亦即比这一年预期的全国军费还要多出25万两!而且东南沿海的官员也在抱怨,他们对付郑成功,亦须增加开支;他们还说,云南地区只有耗费,而东南则有大量赋税收入。清廷基本上同意,缅甸战役确有必要,但落实到具体事务,则不愿向吴三桂开出空头支票。至于如何动用北京及云南府的府库,当时有各种建议供朝廷考虑。直到1660年9月22日,满洲公爵爱星阿被任为大将军,与吴三桂一同越过缅甸边界,追逐李定国,此事才告决定659。
同年11月,吴三桂重整各军;1661年3月,进攻开始。清军越过澜沧江,进入缅甸北部的木邦,插在李定国与白文选之间。此时李定国已东奔;白文选则北撤,但最终被迫在茶山投降。1661—1662年,清军继续向阿瓦推进,并事先警告缅王,若不交出永历帝,大兵即进攻首都660。永历帝必定已知悉吴三桂逼近,因为其时他致吴三桂一书,历数吴三桂自明朝所得恩典,并赞扬吴氏仗义出师,击败逼死崇祯帝的逆贼,但笔锋一转,又在词句间表示不解,为何还要对故明穷追不舍。永历帝说,虽然他与李定国在西南与人无患,与世无争,
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仆由是渡沙漠,聊借缅人,以固吾圉。山遥水远,言笑谁欢,只益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微命于蛮服,亦自幸矣。乃将军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兵,穷追逆旅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仆今者兵衰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血溅草莱,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圣朝,仆纵有亿万之众,亦付于将军。661
当此之际,吴三桂若是为这类说辞所动,那未免太愚蠢了。无论如何,处置眼前这位可怜的有问题人物及其十余龄的儿子,吴三桂是无权作最后决定的。
1月20日,吴三桂与爱星阿抵达阿瓦附近,受到缅人的隆重接待。二人随即派遣一支100人的特遣队到阿瓦城,捉拿永历一行的残余662。当夜皇帝及其家人从者梗的村庄被带走,乘坐旧辇抵达阿瓦对面的伊洛瓦底江岸,其余的妇孺则追随在后,步行前往。然后一行人上船,渡江到对岸。
皇上痰火病发了,太后、皇后十分着急。天已将明,就叫小内臣杨德泽:“你可出舱口去看一看。”见乱纷纷的人马,并不见有个旗号,只听满营中叫总兵王惠,又见几顶大轿,在岸上歇着。……(太后)就对小内臣杨德泽说:“此是清兵了。既是王惠来接我,就当速上来请安,如何延迟小船来?……”小内臣领旨而去。(皇上)又向太后说:“母后只管放心。臣儿想,(虏)既有受得明朝天下,他自然就有礼貌待人,必行国家天子之仪。……”
大约早晨八时,100余人,未带武器,来到皇帝船头。王惠上了船,自称为李定国所遣,但永历帝问起李定国消息时,他一句也答不出。皇帝于是明白,此人实际是吴三桂差来的。
皇上就大声说:“我大明有何负你,你必要将我明朝一网打尽?我想你们受功,不过封王。今日将我母子杀了,你们日后替祖宗做下个骂名,千载的罪人!……”又连吴三桂亦骂在里头。那时皇上的龙颜大怒,指着王惠大骂:“偷生匹夫,快下去!此地是忠臣良将跪的,你有何颜跪在此?还不快去?!”王惠受了皇上凌辱,十分惭愧,又有年纪,上岸跌了一跤,倒在江岸。众人急忙扶起。问他时,已不能言语了。663
不久,大将军爱星阿亲至永历帝座船,颇有礼貌地说:“今日听见大明圣主的驾来,特来一见,请万岁的安。”皇帝答道:“我是废国天子,将军如何行此大礼?”爱星阿继续称颂永历帝“龙颜真如梓童帝君”,以前虽人人听说,实在不信,现在一见,方知名不虚传。他还解释说,“今日之事,是天命所归,原不与我们相干。……我们出兵时,奉旨差我们请皇上圣驾,同往京都,共享天下。又叫臣等切不可惊吓皇上的龙体,我们主子还要亲自相会,看一看皇上。”664
一周之后,这支清军特遣队押着永历帝,离开阿瓦,长途跋涉回云南府,三个月后抵达。此时永历帝痰火大发,只剩悠悠一口气了665。不过,比这还要不祥之事正在策划之中。可能是因为顺治帝本年稍早时去世,因康熙帝年幼而摄政的各辅政大臣态度强硬,认为顺治朝的政策过于宽大,想予以纠正;也可能如某些传闻所说,永历帝的存在,在云南清军中引起严重不安,而且要押解他穿过整个中国,抵达北京,一路上颇有安全问题,满洲人以为最好应避免666;总之,在1662年5月底,最后一位有明朝皇帝称号的人,在云南府与其子一同被害,可能是勒死的(其后皇后在北京自尽,但皇太后活到91岁)。颇能说明问题的是,仅一个月之后,清廷就谕礼部封吴三桂为第一等的王667。
在吴三桂眼中,李定国此时已无足轻重,不值得穷追。李定国军在通过缅甸东北部时,受到清军打击,其后这支军队就进入了最后的解体阶段。李定国疾病缠身,心力交瘁,尤其是听到永历帝被掳之后,身体愈益虚弱。此时甚至他的主要部将也开始叛逃,并挟持李定国家人,做投降清朝的进见礼。大约在1662年8月,李定国在今云南与老挝最西北部的边界附近去世668。
对比之下,在东南一端,郑成功每次与清朝遭遇,每次接到报告,听到谣传,谈起清朝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命运,他就更感到清朝日趋衰弱。1655—1656年,“和议”最终破裂。郑成功随后即致书(实际上是一篇宣言)清福建巡抚,重申对和议过程的不满,并发誓说,清朝不接纳他的议和条件,必将自食其果。
即令清朝选八旗满汉乌合,调南浙疲卒,其伎俩止此耳。不佞所预计而知者,惟有秣厉从事。其谁劳谁逸,谁胜谁负,有不待再决耳。况清朝近来时势,比十年前日异而月不同矣。
且以清朝人事论之:陕西为天下元首,现今西虏倾国入河州地方,(按:河州即兰州,后属甘肃,但当时该省尚未设立。)方割全陕。(指瑕:清初,河州为陕西临洮府下辖的一个散州,不明白作者为何称河州即为兰州。)清朝若从之,则溃裂立见也;若不从之,则溃裂立见也。其元首之决坏如此者。湖广为天下腹心,前敬谨之兵精而且多,全军覆没。今洪承畴乌合之众,战败固其宜也。其腹心之决坏如此者。广东为天下手足,现今西宁王攻破肇庆,羊城亡在旦夕。清朝应援之兵,披甲不满三千,是驱犬羊而赴虎群,稍饱其腹耳。其手足之决坏如此者。
更以清朝天时论之:数年河北人民半付水国,江南百姓多化魁鬼。河决地震,灾异非常,不啻“春秋”山崩川竭之征,适符胡元日食星变之惨。圣贤所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其言已明验矣。……
用是南北齐发,水陆咸驱,掣其一方而旁及四国。将见吾兵抵吴而吴靡,入浙而浙摧,至粤而粤破,动闽而闽瓦解。此非不佞夸言也,实斯时必然之势耳。又不特此也。江北钱粮皆取给于南,盐课、艚粮,关系国命。我师特扼江淮,不特南北截为两断,将见畿辅立毙矣。669
清巡抚复书说,郑成功哆口而谈的所有“天时人事”,令人喷饭;对于清朝巩固大业,他未能见到大处远处,所说种种之事,只是尚待勘定的区区小问题;至于以自然现象为灾异,那只是“儿童之见”。
而台臺伏处海滨,见闻不远。一二游食之徒,好事造言,以相簧鼓。此如山村野落,传说市井,咄咄称怪,而不知其无稽也。……而台臺错认,以为穷洋孤岛,洵是万里长城,艨艟楫橹,可作长生宝箓,意益骄而念愈侈,不亦疏乎。670
不过,当时郑成功对这类话是听不进去的,他已再度忙于发动进攻,并实施其他计划,以期夺取沿海潮州、漳州、泉州各府大小城镇671。同时,他公开接受永历朝廷所授的延平王封号,并将厦门的中左所改名为思明州。他还扩充其卫队,用更复杂的新方法加以训练,并以其专断权力设置新类型的官吏,以处理监察、通讯及司法事务,加强对军队及后勤的管理。这最终可能演变成为新的文官层,但是在郑成功治下,一切人都是彻头彻尾为军事目的服务的672。例如,监军只是接受郑氏个人号令的“监军”而已,并非由文官机构御史台派遣;税吏其实只是军需官,并不向户部报告,除了将军队的粮饷、赏赐记录在案之外,别无其他职掌。郑成功在夺取土地之际,似乎只关注如何为其军事组织提供粮饷,从不设法成立任何政府机构,来治理主要从事农业的一般民众。
此时,郑氏组织的规模、纪律、严密程度,随郑氏雄心而俱增,他的坚强性格亦与之俱增。郑成功确是以鞭打来使各部队就范,同时,他追求成功之心始终不懈,使部下效忠之意决不少衰,而且此心此意还更趋强烈。他在整个生涯中,驭下之严到了不近情理的程度,违法者不论官阶多高,与郑氏关系如何密切,连小罪都不赦免。这样不合理的严厉引起叛逃,不必要地削弱了他的运动,有时对他的利益大有损害。但此时郑成功志得意满,他的福建主力部队人数达10万以上673。
清廷对这一切的反应,表现在下述三方面:首先在京城,对郑芝龙施加了更不祥的限制,他现在已不是清廷的奇货,而是累赘了。清廷易于指责郑芝龙及其家人一直与敌人非法来往;易于说继续在北京善待这些人只会鼓励郑成功制造更多麻烦,因为他显然以为,只要他的父亲及其他家人受清朝礼遇,他自己也就不会受亏待。到了1656年底,郑芝龙被囚,于是再次向其子呼吁;但是郑成功不表同情,称其父“自投虎穴”,再次声明对清朝无好感,决心不受其牢笼674。其次,清朝首次在沿海各省发布限制与“海寇”贸易的禁令,同时又加紧诱使郑氏组织中人叛逃675。这类初步措施,后来演变成双重的政策:一方面,只要郑氏集团中人继续叛逆,就切断大陆沿海人民同他们的贸易;另一方面,又向郑氏手下人示以诚信,欢迎来归;这一双重政策,数年之间越来越成功。最终,不出郑成功所料,清廷果然因其坚拒“招抚”而发动了讨伐行动。
福建省清军的轮换,在粮饷、后援等方面,确有巨大困难676,不过1655年初,清廷还是任命了满洲宗室济度为大将军,统军“征剿”郑成功。在郑成功方面,自该年仲夏至秋季,下令将大陆上邻近厦门各县的大多数城墙及其他堡垒,一概拆毁,并撤走厦门城居民,以划出一个战斗地带677。济度直至10月才抵达闽南,麾下各军因长途劳顿而疲乏不堪。济度提议“免宥”郑成功之罪,但受到成功耻笑,称作“似谑戏”。战事于是不可避免了。但是直至1656年5月9日,济度才得以调动步军通过同安,并从泉州派出海军舰队,从而发起进攻。随后来了一场暴风雨,战斗一度中止,最后,清朝惨淡经营的舰队几乎全军覆没;郑成功以为清朝统治脆弱动摇的看法,得到了证实678。
事实上,郑成功此时已开始第一阶段大张声势的“北伐”,进军长江流域了。早在1653年春,与清朝的“和议”尚未中断之时,他就已在认真考虑此事了。他现在比以往更有决心实施这一计划。有几个原因,其中最根本的,或许是他自视为全国领袖人物,而不只是地方首领,还认为清朝在中国的力量正在衰落。不过,永历朝廷远在西南,而且愈走愈远,愈来愈与外界隔绝;若是清朝败亡后明室将继之中兴,那么,在人口更多、政治地位更重要的各地区附近,高举复明的火炬,当然是必须的679。而且郑成功与清朝议和的经验,更从三个方面使他更急于北伐:首先,郑氏在休战期间,粮饷和作战物资的储存大量增加,因此在1655年,郑氏比以往有更充分的准备,足以发动主要攻势。第二,郑成功明白,清朝跟他议和一无所获,此后必会尽全力讨伐他,以作惩罚;他希望以攻击浙江与南直隶来延缓清军南进。第三,从上文所引以及郑成功的其他声明可知,他决心向清朝显示,自己的威力是多么可怕,清朝小觑他,必得后悔。
实际上,这次“北伐”不是一次单独行动,而是一连串时断时续的努力,可分下述四阶段(见地图15)680:
(一)1655年3月至1657年4月舟山与福建东北部之战。郑成功在战胜济度之前,即已指派手下一位最好的福建海军将领,会同郑氏集团在福建以北水域最富经验的海军指挥官张名振,一起攻击浙江与南直隶的沿海设施,以窥探清朝“腹地”。然而这支舰队(有五六千艘船只,六七万人)遇到了风暴,因此在1655年11月25五日收复舟山,使之重归明朝统治之后,远征就停止了681。1656年8月,清军夺得了郑氏在海澄的主要补给基地。郑成功要对此报复,弥补其损失,更要继续上次出师的未竟之业,并向福建省城施加压力,于是在1656年秋,亲率船只数千艘,进攻沿海的福州府。郑军在这次战役中,完全控制了闽江入海口682。其后,在秋末和冬季,郑成功继续北上,深入沿海的福宁府。1657年2月,郑军歼灭了一支精锐的清军反攻部队,三位著名的清朝梅勒章京(副将)于是役阵亡683。
这几次轻易的胜利,肯定使郑成功更觉得清朝无能,更促使他下决心进攻江南。但是在他的北面,事情就不如此顺利了。1656年1月,张名振死于舟山;同年10月中旬,清军重占舟山(当时舟山称为“海外无用之地”,疮痍满目,人民逃散,终于不守),前鲁王水军几位主要将领,非降即死684。因此,郑成功若要通过杭州湾以北不熟悉的水域,已无杰出人物可做他的向导了。于是在1657年春,郑成功保住了在福建东北部的各基地,班师回厦门。第一阶段的北伐就这样无果而终了685。
(二)1657年秋浙江台州府之战。这年8月,郑成功袭击了闽南的兴化,以夺取粮饷,随后直接扬帆北上,进入浙江的灵江口,先摧毁清军的沿海堡垒,而后于10月3日攻占台州府治686。但这一次,郑氏的南方出了问题。福州府的清军,运用某种非常策略,从郑氏部将手中夺回了闽安要塞。该城扼守闽江口,为郑氏军队在闽北的主要据点。郑成功匆忙赶去,企图挽救局势,但为时已晚,于是回到厦门,遣散了原定出征的部队,以便过冬687。但在次年3月,郑成功着手进行新的训练强兵计划,将其卫队重组、加强,并首次创建了著名的“铁人”部队。这些部队的士兵特别强壮,全身披挂铁衣甲688。
(三)1658年6月至1659年6月浙江东南沿海之战。郑成功在厦门誓师,并于登船前告谕将士,可见他这一次准备长驱直入,短期内不会班师。他为了积聚可供7个月出征的粮饷,先自福建东北角的沙埕出发,越过闽浙边界,攻入温州府689。而后率领舰队到舟山,再作训练,一个月之后,向北直驶崇明。不过,这支舰队在中途停泊洋山列岛时,遭到特大飓风的袭击,损失惨重。郑成功家属231人,其中六妾三子,因所乘船只遭遇持续3天的风暴,溺死海中;幸运者漂至大陆,为清军所俘的有九百余人。郑成功手下人和别的水手一样迷信,因此这次灾难严重影响了士气。剩余的舰队还有数千艘船,10万余人,郑成功只得允许他们先回舟山,然后到台州进行休整690。他本人则在1658年12月1日占领了温州城附近瓯江口的一处要塞,并分遣各将领到福建东北与浙江东南沿海诸多避风港过冬。尽管郑成功当时地位脆弱,然而清军在1659年初想把他逐出温州,仍未能得手。于是温州就成了他的大本营,直至当年6月691。
(四)1659年6月至9月长江三角洲之战(见地图17)。郑成功经由定海侵入宁波府,为下次更大攻势进一步补充人员、船只与粮饷,并削弱清军威胁后方、截断归路的能力。这是他一生事业巅峰的开始692。郑氏舰队在附近几个海岛上作了几次练兵之后,再次向崇明进发,于1月7日停泊在该岛以南以险闻名的沙洲地区。他的兵士惯于劫掠,这一次他施加了严格限制,在7月的其后二十余日中,使舰队泊于长江口外海面,只许兵士略作劫掠,以取得柴火之类的必需品,长江口以南人口稠密的各城市,则严禁攻击693。
郑成功对军事计划和出征目标,通常是相当保密的,但这一次长江之战,却从不想作突然袭击,颇值得注意。1655年以来,他一直在坦率告诉清朝,打算进攻南京地区。而后他移驻宁波,又给清朝事先警告。现在他在沿江而上之前,滞留二十余日(与清朝武官中可能的变节者接触,或许还在搜集内地情报);其后也是行军缓慢,对于清军会赢得时间,集结守军,似乎是满不在乎。个中理由,看来是这样的:郑成功信心十足,要打一场最大的仗,以取得最大的胜利,从而在汉人和满洲领袖中间造成相应的巨大心理效果。此一战略,与他以前镇压各小地方的方式,如出一辙,都是保存兵力,以取得几次关键的胜利,从而使敌人屈服。他在直破瓜洲、镇江以后,希望南京因震慑而降服;若是做不到,便用武力攻下南京。他以为北京清廷经此打击,将会不知所措,从而无法支撑下去。
不过,郑成功将此战略用于江南时,估计过高。一个例子是,清朝对中国其他地方的控制,并不像郑成功所想象的那样脆弱。他对清朝能力的看法,是得自沿海各府的经验;但是不论在何种情况之下,南京地区的防卫,要严密好几倍。而且近年来张名振和郑氏麾下其他将领对长江三角洲不断的威胁,使清朝方面的领导得到了磨炼,使他们对于如何防守江南入口处的长江口,取得了有用的经验。要塞守军已增强,还采取了许多特别措施,不使敌方海军突过镇江——诸如横江辅设大索,在两端安置加固的炮船,敌船驶入,将陷于其间694。此外,郑成功的到达,为时已太迟。要是他的北伐能像原来计划的一样,早一年实行,战事可能更为容易,因为当时正在征剿西南,有大量满洲军队卷入。但是当郑成功在1659年夏抵达时,先前派往贵州、湖广的满洲各军已返回南京,或是已在归途695。
而且郑成功在东南沿海地带有广泛的情报网,颇为有用,但在江南,这样的情报网并不存在。此一因素,加上不熟悉江南地形,使郑军在长江之战中不能得心应手,尽管兵士都经过彻底的训练,人数也占优势。前面说过,鲁王海军主要将领中熟悉长江口情况者,全都已死去,不是病殁,就是被杀。因此,郑成功在他北伐的这一阶段,挑选来做他主要副手之一的,是一位书生张煌言。他曾在已故的张名振手下参谋军事多年,深受浙东“清流”传统影响,曾为监国鲁王的定策之臣,绍兴失陷后,不屈不挠,支持复明事业,沿海抗清活动的每一方面,他几乎都有份696。尤其是张名振三次攻入长江口,他都参与。因此,当郑成功最终进入长江水道时,做向导的就是张煌言。由此导致了明朝历史中最末一次主要的文武矛盾。
1659年7月31日至8月2日三天之内,郑成功在长江中的焦山,集结了2300艘舰只的大军,举行了庄重仪式,以震慑清朝。第一天,着红衣祭天;第二天,着黑衣祭地;第三天,着白衣祭明太祖朱元璋697。当时郑成功本人也赋诗一首:
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呑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698
而后坚毅无比的张煌言,率军突破江心“滚地龙”,击毁了数艘沿岸炮船,于是其他郑军便能在8月4日攻下瓜洲,切断了自瓜洲沿大运河往北的清军调动及联络。随后张煌言驾轻便小舰,溯江而上,在南京四周及邻近展示明朝旗帜。郑成功则彻底击败了长江南岸清朝守军,逼近镇江,军威赫奕。8月10日,镇江慑服而降699。此时,船只遇到逆风,只能由纤夫在岸上拖着,沿长江缓慢行进。张煌言及其他人向郑成功建议,上岸走陆路,由镇江直趋南京,以节省时间,但未被采纳。在整个战役中,郑成功的步调太过悠闲,以致大军抵达南京城外时,已是两周后的8月24日了。80艘满载清军的船只,得以在此之前由贵州返回南京。郑成功几位最好的谋士,主张先发制人,立刻攻城,然而又遭拒绝。郑成功在等待,希望能诱使清朝方面几个关键人物投降,从而避免代价巨大的攻城战。而且清朝从松江、苏州、金山、杭州等地派兵增援南京,郑成功也没有设法阻止。他以为,自己在南京城下的大军,仅步兵就有85000人左右,清军从这里拼凑数百,那里补充数千,并无多大威胁700。但是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将士的素质,而不是其数量。郑成功不久以痛苦的教训重温了这一原则。
更有意义的是,虽然江南有不少地方投降,或是向郑成功、张煌言派人表示效顺,这类地方的数目实在不小,总共有七府、三州、三十二县701;但是郑成功方面对此民众反清高潮,既没有制订任何政治计划,也没有安排好官吏,有条不紊地予以处理。当时的江南,神化郑成功一类的事,似乎已很普遍,然而郑成功并未设法在政治上加以利用,诸如向民众告谕等事,都没有做。他向这些地方,尤其是与他有联系的各地,派出了官吏,其中大多是武人。但从根本上说,在他的心目中,这些地方与东南沿海各地似乎并无二致:一般说来,取得一地,当守其土,治其民,但郑成功视东南沿海各地,只是人员、牲畜、银钱、食物及作战物资的来源而已。他用以联络各城的一小批士人,包括张煌言在内,事务繁重,耗尽了心力。有人向郑成功提出,在北伐中对这方面应多加注意,但他未予理会702。张煌言深信,当地士绅的同心同德,可使诸事改观;然而使他大感困惑的是,郑成功对武人的私利不予置疑,并相信要影响历史,主要得靠赢得战争。因此,当南京局势恶化之时,郑成功环顾周围地区,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支援可资依赖,在这陌生环境内未免感到孤立,于是就匆忙班师了。
郑成功的等待策略,不仅使手下将士因无所事事而气衰,也使进攻的主动落入清朝之手703。最后,在9月8日,清军从仪凤门发起初攻,郑成功就在当夜迅速重新部署了兵力。但是次日凌晨,清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南京西北边二门发动了总攻,大出郑军意料。于是在随后的一场恶斗中,郑军气索,为清军所败。郑成功丧失了几位最能干的将领,包括他最亲密的顾问甘辉,他的步军也大量被歼。不过他的海军可说毫无损害,因此能把他本人及少量残存步军载回镇江704。
张煌言致书郑成功,央求他留在镇江,说“兵家胜负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但郑成功急于撤退,遂于9月14日率军返回崇明。张煌言则困于稍上游的荻港附近,所带的一支小部队于9月23日被来自湖广的清军内河舰队击败。他以前在江南曾为自己及郑成功争取到不少地方人士的支持,现在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在崇明的郑成功,现在主要关切的,是阻止清军前往骚扰他的福建老营。因此,他又以惯常的看似矛盾的方式,一方面攻击崇明岛上的要塞,显示他的军力依然不可小觑;另一方面,请吴淞总兵官居中调停,欲与清廷重新议和。但是他的军队士气太低落,不能奋勇作战;而清廷也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和议。于是当张煌言历尽千辛万苦,自陆路从南直隶西南部逃往浙江东南沿海时,郑成功已率领舰队,扬帆而南,于1659年秋末返抵厦门了705。
郑成功知道,清军不久就要发动主要攻势,因此甫返家门就着手准备应付。事实是,郑成功还在南京时,清廷即已指派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统领特遣部队进攻郑成功,并下令清朝南方府库及其余各军全力支援。1660年2月,达素抵达福州,筹划如何将广东潮州、浙江温州台州、福建漳州泉州的清军水师兵力最大限度集中起来,以攻取厦门湾中郑成功的一群小岛706。郑成功的海军主力,还有舰只两千余,远超过清朝方面船只总数,而且他已将外围各军悉数召回厦门地区,因而其防御比从前还要坚强707。不过,尽管郑氏军力强大,并未受损,但因南京之败而士气低落,信心动摇。此一军事组织,不久以前还扬帆千里,在陌生区域内打击清朝的要害,而现在要靠告谕将士、安定人心、整肃军纪的特殊措施,才能使之为自己脚下的土地而战708。
1660年6月上半月,一支清水军主力突破了泉州湾的郑军封锁,与漳州来的另一支清军会合,在厦门西、北两面和郑军打了一仗。清军舰队同以前一样,几乎全军覆灭,郑成功发谕给一败涂地的清军将领,并遗以巾帼,约其合兵再战709。但这一次,郑成功其实没有多少理由可以得意。清军准备充分,他深有体会;自己的将士表现欠佳,则难以令人满意。而且他知道,清朝在所有其他战场都已获胜,以后便能将更多的物力用于福建,像这一类的进攻也就有能力一再发动。事实上,这次战役刚过去,清廷就将南方三藩王之一的耿继茂派往福建(而不是贵州或广西),并命征服作战的老将宗室洛托从旁协助。郑成功在此弹丸之地,要无限期保持足够兵力,以击败这类人物所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实在是无此可能710。
因此在1661年春初,郑成功强使其将领同意,将郑氏主要基地迁往台湾。在此以前,这些将领对此是一向冷淡的,这一次也很少有人会感到高兴。一个将领,因公开说出了他人心中所欲言,而受到了处罚。他以为,台湾孤悬海外,疾病流行,是一个不宜于居住的荒徼之地。不过郑成功立志已决,因为他需要一块更大的土地,既不易受清军威胁,又靠近东亚主要的海上贸易通道。此时,他想到了台湾的资源及其他好处,以为取得这些东西,将是易如反掌。郑成功对台湾的知识,得自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位前中国雇员,此人为巴结他,把台湾说得天花乱坠,而他对此或许是过于轻信了711。
东印度公司是荷兰的国家企业,自1624年以来即在台湾(荷兰人称为“福摩萨”)西南沿海建立了一个贸易殖民地。公司与郑芝龙的关系并不融洽,但与郑成功的关系更坏,因为成功经常为了“与鞑靼人作战”而干涉公司的贸易。许多公司官员一直在担心,郑成功有朝一日会在中国沿海陷于逆境,从而设法取得台湾。当时,在荷兰殖民地附近定居的中国人愈来愈多,1652年,他们发动了一场暴乱。荷兰人以为,这是郑成功所派的人在暗中煽动的。自此以后,郑成功每次在厦门周围的作战准备,都会引起新的谣言,说即将进攻台湾。南京败后,情况尤为如此712。
但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东亚总部的所在地巴达维亚(雅加达),很少有人想进一步花钱于台湾的前哨基地;因而对迫在眉睫的郑成功进攻的传言,多数人认为,犹如“一缕烟,风起即消”。1660年10月31日,台湾殖民地的荷兰总督,致书郑成功质询,成功复书态度诚恳。有些荷兰官员,可能由于愚,也可能出于一厢情愿,显然已为这类言辞所欺。郑成功在复信的开头,向荷兰人表示友好亲善,而后说:
夫足下得报,实多讹传,居然以为信。荷兰居人与中国互市,络绎不绝,启导者,吾父也;嗣后有增无减,玉成者,不佞也。而足下间于奸邪小人之言,于不佞善意,偏生疑虑,不佞所昼夜擘画者,出师征讨,收复失地也;区区弹丸之地,岂有意于图谋乎?且不佞用兵,素采声东击西之术,旌麾之所指,又谁得而知之……今所望于足下者,息争端,祛嫉意,复旧谊耳。他日底定,传令互市重开,其可必也。
结果,荷兰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有效加强其殖民地的防御713。
1661年3月,郑成功为台湾之战作了部署。4月,其舰队自金门出发,但在中途遇到恶劣天气,被困在澎湖列岛达七天之久。此事颇为棘手,因为郑成功事先以为,渡海轻而易举,必然很快到达,而且台湾食物丰富,可以就食;因此,他的舰队几乎没有带什么粮饷。因此,当郑军于4月30日最终抵达荷兰殖民地附近海岸时,士兵已是饥肠辘辘,于是立即冲上岸,洗劫赤嵌中国居民区的粮仓。然而驻守在“台湾”(指一海湾)的简陋要塞及两艘战舰上的荷兰士兵与水手,只有数百人,对他们来说,士兵数千与战船数百的郑成功大军,不论是否吃饱,都是大祸临头714!
5月1日,郑成功命令赤嵌附近较小的赤嵌楼(Fort Pro vintia)以及位于“台湾”与大海之间狭窄通道中沙洲之上稍大的台湾城(Castle Zeelandia)投降。他答应让荷兰人安全离开,因为他与荷人之间素无怨恨;但是他坚持要重新取得这块其父曾慷慨允许荷人使用的领土(按:原文意思如此)。东印度公司“福摩萨”委员会及总督揆一要求和平共处,并在岛上保留基督教,却为郑成功所拒绝。于是荷人立即交出了无法防守的赤嵌楼,但在台湾城则竖起了“血旗”,与郑军摆开了交战阵势715。
郑成功出于几个理由,没有立即向台湾城展开攻击。首先,他一向不喜欢代价惨重的攻城战。而且他以为,由于夏天季风北吹,荷兰人向巴达维亚报信,然后取得增援要好几个月,在此期间,被围的城堡守军可能穷饿而降。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他自己方面也严重缺粮。他命令从大陆运粮来的船只,一直未能回来,大米实际已尽,当地的玉米与芋头也决不充足。于是郑军士兵普遍不满;台湾人民,不论是汉人还是土著,接受郑氏统治,最初还不是太勉强,而现在也普遍不满;郑成功只得拨出大量士兵开垦田地,为下一季的收成进行屯种。而且许多士兵水土不服,染上了瘟疫,不是病倒,就是死亡716。郑成功肯定没有料到,渡过台湾海峡如此困难,台湾又是如此落后;要是荷兰方面没有内部几次背信弃义之事,郑成功这次战役可能未必成功。
8月中旬,大出郑成功意料,一支荷兰“增援舰队”抵达了,并把所需的士兵、食物、物资运到了台湾城。于是在9月,他不顾自己军队内部的虚弱,不得不重新进攻。但是荷兰增援舰队的司令对此懵然无知,看到敌人声势之大,战技之精,而自己的城堡似已陷于绝境,不觉丧了胆。于是,当揆一总督接到清朝当局表示愿意协助抵抗郑军的信件之后,这位舰队司令自愿携带荷人接受清朝提议的复信前往福建。但是他未履行承诺,跑到了暹罗717。这样一来,台湾城守军(患病忍饥,不足600人)自然士气大减;到了12月中旬,几个荷兰士兵投降郑军,泄露了如何最有效进攻城堡的宝贵情报。1662年1月25日,易被攻破的外城受到炮击而被摧毁;两天后,揆一和“福摩萨”委员会决定接洽投降,2月1日,正式投降,历时9个月的一场劫难结束了718。
甚至在荷兰人撤离之前,郑成功就已将赤嵌改为“东都明京”,设立“承天府”,下属二县,颁布永历历法,并专横地要求吕宋的西班牙总督“进贡”。郑成功在其小王国之内建立了文治政府的雏形,如订定赋税系统,管理渔猎,监督土地分配;但同时依然很谨慎,不使自己看起来像僭越帝王权力719。但是从当时情势明显可见,郑成功如此做,是为防止手下士兵和民众的全面叛乱而不得不然。正如一位早期台湾史专家所指出的,“这个政府是极度军事化的;在整个郑氏统治时期(即包括郑成功继承人在内),武官至少有338位,而文官只有56人。这个岛实际上是由军法统治的。”720因此,统合文武这一问题,在明朝从未获得解决。
郑成功若是真想利用台湾作为基地,再向清朝进攻,那么,由于缺少粮饷,尤其是台湾造船能力不足721,而且台湾与大陆间的海道是既阔又危险,因此这一想法简直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郑氏部下,不论是驻在福建沿海还是驻在台湾,肯定也知道这一点。郑成功出发到台湾之后,部下投奔清朝的人数立即增多,一个原因是没有了郑王的虎威,另一原因则是清朝加紧努力,迁移沿海居民,禁止海上贸易,扩大本身的海军力量,终于取得了预期的效果722。1662年3月,郑成功命其长子郑经及留守厦门与金门的各将领放弃这些岛屿,连同所有家眷一起撤到台湾;军纪问题因此而愈益严重了。他们按兵不动,实际上是拒绝了服从命令。郑成功现在是处处碰壁,因而他在台湾的部下若有过失,即予严惩,其酷烈的程度几近疯狂723。
1662年五六月间,当郑成功得知其长子私通其幼子的乳母,并产下一子时(对于一向以严格著称的郑成功来说,这无疑是乱伦),形势恶化成为一场危机。郑成功当即下令,将长子、乳母、婴孩,以及长子的正室(因治家不严)一并处死。他手下诸将想仅把乳母和婴孩斩首了事,以使郑成功息怒。但他更为恼怒,甚至下令(但未被执行)将所有不遵命的人都处死724。此时,他亦已获悉,永历帝在西南边远地区被俘,并可能已遇害,他自己的父亲最终亦被清朝杀害725。所有这一切,使郑成功的精神大受刺激,他终于病倒了。1662年6月3日,他死于台湾,年仅37岁,死因可能是精神失常,以及并发某种引起谵妄的疾病726。
明朝文治政府最后两个著名的象征人物鲁王和张煌言,一个在福建沿海,一个在浙江沿海,因健康和环境的恶化而日薄西山,奄奄待毙。张煌言以前一直以一小支水陆两栖的抗清部队,骚扰各清军据点,但力量薄弱,当然未能成功;后来他又告诫郑成功,不要放弃大陆,去和土番及红毛夷争夺孤悬海外之地。他还指出,清帝新死,清朝的迁海政策普遍不得人心,郑成功若能再度北征,“百万雄师可得,百十名城可收矣。”727此一劝告无效,他于是恳求在金门的鲁王,请他积极行动,举起郑成功放落的大旗,给明朝子民再一次机会,奋起响应复明号召728。但鲁王本人痰喘病甚重,在1662年12月23日也死去了729。因此,虽然台湾与其他地方的人民继续用明朝名义作为抵抗征服、抵抗政治压制的象征730,明朝本身实则已寿终正寝了。
“明朝”,作为一个统治的实体以及17世纪东亚人心目中的概念,犹如一座松石与软泥堆积而成的大山,上面受到大雨冲刷,下面又在震撼,渐渐地东冲掉一块,西冲掉一块,最终荡然无存。自从弘光时期以来,明朝就不再能统治整个中原本部,也不再对中原周围民族保有优势。南京陷落,鲁与隆武政权成立以后,明朝不再有一个居于中国传统建都之地的单一的中央政府;而在这两个政权被击败之后,明朝只是在中国版图的边陲暂时栖息,谈不上有什么首都。
弘光政府是完全按照明朝先例建立起来的,各机构一应俱全,包括六部在内,而六部自唐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基石。但是当时这些机构的能力已大受腐蚀,对于名义上在其治下的各地方公务,既不能发挥影响,更不能实行管理。新任官员不能或不愿到各省任职,在任官员则不能或不愿执行指令。他们最不能或最不愿做的,是上缴钱粮,而这正是国家的命脉。隆武帝还有决心尽力保持首都与各地方之间最后一丝微弱的正常行政关系。但在隆武朝廷消灭之后,永历政权即使在局面最好的时候,也从未能恢复这种关系。而且永历政权所唯一能依赖的具有超地方权力的组织,是各式武人的横行不法的军队及其大体上漫无统系的后勤系统。
这段时期的历史,确实也可看作是明朝逐渐再度军事化,尽管这样的军事化,肯定不能导致恢复太祖时代的强盛。虽然明朝初期强调尚武精神、平民政治,但到了15世纪中叶,明朝所发展出的一套权力与奖励体制,绝对是以文统武,以高等文士凌驾其他平民阶级。其后,经济上的变化、政治上滥用权力、军事上的诸种问题,使士大夫阶级的统治地位受到质疑;于是对士大夫控制的挑战,不论是在中央政府还是在地方社会,就被看作是对明朝秩序本身的挑战。由于这一原因,在南明,很少有一个人兼具文武两方面的才略,政治家与将军也极少可能协调一致。直至1650年代,在东南和西南的所有明朝官僚事实上都消失了,这一个矛盾才随之而消除。但是正规明朝军事机构消失得更早,享受不到对文人官僚的惨胜。军事化在全国范围内不受控制地扩展与加深,因而最后代表明朝的最坚强的军事组织,都是在明朝正式政府的范围之外非法滋生和壮大起来的。
尚未消失的最后一个明朝基本特征,是其皇帝。明朝皇帝必须是太祖的直接后裔,按照古代传统行登极礼,建立年号。这一象征一直持续到1662年永历帝遇害之时。但是明朝的皇帝制度及其正常运作方式,早已死亡蜕化了。不论在明朝还是在其他朝代,一个中国皇帝,至少在外表上必须既统且治。在明朝,此一外表之所以能维持,在于皇帝有一个非正式的文臣集团可资磋商,其组成分子是资深政治家与杰出文士。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几位明朝皇帝的气质、中国党争的格局、某些特殊的体制上的不明确——此一安排困难重重。在南明,朝廷本身的生存所依恃的,是在皇帝及其主要顾问中间维持一种使办事有效的关系,但是先后几位君主及其大学士从未真能团结。在居于帝位者这方面,对于内阁的用处是不甚了了,观念错误;而在官员中间,关于内阁的适当作用及组织也一直未能达成一致看法;因此,如何辅佐皇帝这一明朝的问题自始至终存在。
尽管有这一切困难,拥护明朝政权的有组织的力量,还是能抵抗清朝的征服与统治,持续了至少18年。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一般人以为,明朝体制支持了一个成功的、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统治大秩序,几乎达三百年之久;因而他们对明朝的基本体制有真正的自豪感、信任感。在17世纪的东亚次大陆,到处是一片混乱,应主要对此负责的,是否即是明朝体制,退一步说,是否即是在后期受到歪曲的明朝体制,答案过去不清楚,现在仍然不清楚。但是明朝上层统治者,到了1640年代,以其长期形成的习惯与态度,在操纵或不当地运用这些制度。他们显然不足以应付这一混乱局面。清朝的制度与统治中坚终能应付这样的局面,但所用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南明的区区二十年。
引用书目
(一)中文731
《大明会典》,五册,台湾:东南书报社,1963年(影印万历十五年刊本)。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清世祖实录》),《大清历朝实录》,五—七卷。台北:华文书局,1964年影印本。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清圣祖实录》),《大清历朝实录》,卷八—十三。
川口长孺:《台湾郑氏纪事》,周宪文辑,《台湾文献丛刊》,第五种,1958年。
方豪:《由顺治八年福建武闱试题论郑氏抗清的主力》,《大陆杂志》二二卷六期(1961年3月),页1-20。
王夫之:《永历实录》,张秉文辑《船山全集》第十二卷,台北:华文书局,1965年。
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编:《十二朝东华录》,五〇九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
王秀楚:《扬州十日记》,《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第三册。
王崇武:《跋永历帝致吴三桂书》,《东方杂志》四三卷九期(1947年5月),页37-41。
王进祥:《朱舜水评传》,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年。
王葆心:《蕲黄四十八寨纪事》,影印本,台北:中华书局,1966年。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十七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47年。翻印本,台北:广文书局,1964年,题为《中国近代内乱外侮历史丛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北京:中华书局,第四册,1979年;第六册,1980年。
毛一波:《书鲁王之死与郑成功受诬事》,《文献专刊》四卷三—四期(1953年12月),页9-10。
《郑成功与张苍水》,《台湾风物》四卷四期(1954年4月),页4-10。
《鲁王抗清与明郑关系》,《台湾文献》一一卷一期(1960年3月),页60-74。
《浙闽公案与南澳公案》,《台湾文献》一一卷一期(1960年3月)页75-80。《南明武臣郑彩的事迹》,《民主评论》,一二卷一四期(1961年7月),页14-18。
《南明史谈》,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
《郑成功官爵考》,《台湾文献》,二三卷四期(1973年12月),页5-6。
古藏室史臣:《弘光实录钞》,《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第八册。
石万寿:《论明郑的兵源》,《大陆杂志》四一卷六期(1970年9月),页20-29。
《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幼狮学志》一一卷二期(1973年6月),无连续页码。
《论郑成功北伐以后的兵镇》,《台湾文献》,二四卷四期(1973年12月),页15-26。
石旸睢:《南明钱录》,《台湾风物》,一一卷四期(1962年),页46-47。
司马光:《资治通鉴》,《四部丛刊·史部》第九九——一七八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
田大熊原:《国姓爷的登陆台湾》,石万寿译,《台北文物》四四卷(1978年6月),页111-121。
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第三一三种,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五九四卷,台北:台湾银行,1957—1972年。
江之春:《安隆纪事》,《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第十四册。
江日升:《台湾外记》,方豪辑编《台湾文献丛刊》第六十种,共三册,1960年。
江荫香:《桃花扇名人小史》,香港:汉文图书公司,1970年。
全祖望:《鲒埼亭集》、《鲒埼亭集外编》,《四部丛刊》第九五函,影印二册本,台湾:华世出版社,1977年。
朱子素:《东塘日札》二卷,《纪录汇编》、《荆驼逸史》题此名。《明季稗史初编》卷十三及《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第二册题为《嘉定屠城纪略》,缩略改动本题为《嘉定县乙酉纪事》,《痛史》第八册。
朱文长:《史可法传》,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年。
朱维铮:《施琅与郑延平的恩怨》,《文史荟刊》,一卷(1959年6月),页88-95。
多尔衮:《多尔衮摄政日记》,影印本,《笔记五编》第十三册。台北:广文书局,1976年。
沈荀蔚:《蜀难叙略》,《笔记小说大观》第二二〇册。
汪光复:《航澥遗闻》,《荆驼逸史》本。
汪宗衍:《读〈清史稿〉札记》。香港:中华书局,1977年。
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
李文治:《晚明民变》,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48年。
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
李介:《天香阁随笔》,《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八六册。
李世熊:《寇变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李光涛:《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二本(1947年),页193-236。
《洪承畴背明始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七本(1948年),页227-301。
《明季流寇始末》,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
《明清史论集》,二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引用书中下述各文:《清人与流贼》,上册,页349-357;《多尔衮山海关战役的真相》,下册,页443-448;《李定国与南明》,下册,页591-614。
李光涛辑注:《明清档案存真选集》,三册,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1975。
李光璧:《记后明政府的抗清斗争》,《历史教学》,二卷三期(1951年9月),页26-28。
《农民起义军在鄂地区的联明抗清斗争》,《中国农民起义论文集》,页295-306,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
李振华:《明末海师三征长江事考》,《大陆杂志》,(上):六卷九期(1963年5月15日),页1-5;(下):六卷十期(1963年5月31日),页18-22。
《张苍水传》,台北:正中书局,1967年。
李健儿:《陈子壮年谱》,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第二册,页516-550。
李清:《三垣笔记》,《嘉业堂丛书》第六七——六九册,影印本,《中华文史丛书》第八三册,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
李履庵:《关于何吾驺伍瑞隆史迹之研究》,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第二册,页612-644。
李学智:《重考李振华先生〈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大陆杂志》,七卷一一期(1953年12月15日),页7-8;七卷一二期(1953年12月31日),页21-27。
李腾岳:《郑成功死因考》,《文献专刊》,一卷三期(1950年8月),页35-44。
阮元等编:《广东通志》,三三四卷,同治三年刊。
阮旻锡(别号鹭岛道人)《海上见闻录》,《台湾文献丛刊》第二四种,1958年。
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影印本,《明清史料汇编》第七三册。
吴密察:《郑成功征台之背景——郑氏政权性格之考察》,《史译》,一五卷(1978年9月),页24-44。
吴晗:《明代的军兵》,《读史札记》,92-141页,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
吴伟业:《绥寇纪略》,《史料丛编》第二一——二四册,台北:广文书局,1968年。
吴智和:《明代的江湖盗》,《明史研究专刊》一卷(1978年7月),页107-137。
吴缉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三一本(1960年),页381-403。
《论明代废相与相权之转移》,《大陆杂志》三四卷一期(1967年1月),页6-8。
《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二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引用书中下述各文:《论明代税粮重心之地域及其重税之由来》,上册,页33-73;《明成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漕运的建立》,上册,页155-173;《论明代宗藩人口》,下册,页237-289。
《明代最高军事机构的演变》,《南洋大学学报》,六卷一期(1972年)页144-154。
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刘世行辑《贵池先哲遗书》本,贵池:1920年。
《楼山堂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余贻泽:《中国土司制度》,重庆:正中书局,1944年。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国学基本丛书》第三七五种,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
何是非:《风倒梧桐记》,《荆驼逸史》本。
佚名:《监国纪年》,《明季史料丛书》第九册。
《京口变略》,冯梦龙编《甲申纪事》第六卷。
《淮城纪事》,《痛史》第八册。
《龙飞纪略》,周昔雍编《兴朝治略》第一卷。
《隆武遗事》,《痛史》第九册。
《绍武争立记》,题黄宗羲撰《行朝录》中含有数种来历可疑之作,此为其中之一,此处所引用者,载《梨洲遗著汇刊》第二册,台北:隆言出版社,1969年。
《蜀记》,《痛史》第九册。
《苏城记变》,《明季史料丛书》第八册。
《滇寇纪略》(北京图书馆抄本)。
《扬州变略》,冯梦龙编《甲申纪事》第六卷。
《祁彪佳集》,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
《甲乙日历》,《台湾文献丛刊》第二七九种,1969年。
林时对:《荷牐丛谈》,《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五三种,1962年。
林朝栋:《郑成功克台前台厦之间的经纬》,《台南文化》,五卷二期(1956年7月),页91-98。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重印本,台北:世界书局,1965年。
屈大均:《安龙逸史》,《嘉业堂丛书》第七十册,吴兴,1918年。
邵廷宷:《思复堂文集》,徐友兰辑《绍兴先正遗书》四集,影印本,台北:华世出版社。
昆明无名氏:《滇南外史》,《明季史料丛书》第十册。
《明史》,《仁寿本二十五史》第八三五—九三四册,台北,二十五史编刊馆,1956年。
《明季史料丛书》,郑振铎编,上海:圣译园,1944年。
《明季稗史初编》,留云居士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原题《明季稗史汇编》,上海琉璃厂图书集成局刊,1896年。
《明清史料汇编》,沈云龙编,八三册,台湾永和:文海出版社,1965—1973年。
《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会议秘书处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金成前:《郑成功李定国会师未成之原因》,《台湾文献》一六卷一期(1965年3月),页115-127。
《甘辉周全斌刘国轩与明郑三世》,《台湾文献》一六卷四期(1965年12月),页133-143。
《施琅黄梧降清对明郑之影响》,《台湾文献》一七卷三期(1966年9月),页151-166。
《郑成功起兵后十五年间征战事略》,《台湾文献》二三卷四期(1972年12月),页80-99。
《明郑重要将领史事分述》,《台湾文献》二四卷四期(1973年12月),页67-85。
《郑成功南京战败与征台之役》,《台湾文献》二五卷一期(1974年2月),页44-58。
金堡:《岭海焚馀》,《台湾文献丛刊》第三〇二种,1972年。
金声:《金太史集》,《乾坤正气集》第457—465卷。
周昔雍编:《兴朝治略》,崇祯十七年刊,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善本书。
洪承畴:《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计六奇:《明季南略》,《台湾文献丛刊》第一四八种,三册,1963年。《明季北略》,《台湾文献丛刊》第二七五种,四册。1963年。《革命远源》,二册。“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辑,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
南园啸客:《平吴事略》,《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第一四册。
胡耐安:《明清两代土司》,《大陆杂志》,一九卷七期(1959年10月15日),页1-8。
[胡钦华],题为邓凯作:《求野录》,《明季稗史初编》卷一七。《天南纪事》(北京图书馆抄本)。
柳亚子:《怀旧集》,上海:耕耘出版社,1947年。
查继佐:《鲁春秋》,《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一八种。1961年。《罪惟录选辑》,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三六种,二册,1962年。《东山国语》,沈起补正,《台湾文献丛刊》第一六三种,1963年。
侯方域:《壮悔堂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
《纪载汇编》,《申报馆丛书》续集,申报馆,光绪四年。
姚名达:《刘蕺山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海外散人:《榕城纪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台湾文献丛刊》第二八六种,二册,1970年。
马少侨:《明末武冈人民的反藩役斗争》,李光璧编《明清史论丛》,页135-144。
秦世镇:《抚逝檄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陈湖逸士编:《荆驼逸史》,锦章图书局刊。
夏允彝(夏完淳):《幸存录》、《续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卷一四—一六。
夏完淳:《夏完淳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夏琳:《海纪辑要》,《台湾文献丛刊》第二二种,1958年。
孙金铭:《中国兵制史》,台北:阳明山庄,1960年。
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台湾文献丛刊》第九九种,1961年。
徐芳烈:《浙东纪略》,《痛史》第七册。
徐世溥:《江变纪略》,《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第三册。
徐孚远:《交行摘稿》,《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二三种,1961年。
徐承礼:《小腆纪传》,《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三八种,六册,1963年。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三四种,五册,1962年。
《清史列传》,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
梁启超:《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东方杂志》,二〇卷六期(1923年3月),页54-56。
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历史研究》1978年5期(5月),页76-82。
许重熙:《江阴守城记》,《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第三册。
郭垣:《朱舜水》,台北:正中书局,1964[1937]年。
郭影秋:《李定国纪年》,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
康范生:《仿指南录》,《荆驼逸史》本。
庄金德:《明监国鲁王以海纪事年表》,《台湾文献》一一卷一期(1960年3月),页1-59。
《郑氏军粮问题的研讨》,《台湾文献》,一二卷一期(1961年3月),页55-66。
《郑清和议始末》,《台湾文献》一二卷四期(1961年12月),页1-40。
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黄道周《黄漳浦文选》附录,第三册。
姚莹、顾沅编:《乾坤正气集》,影印本,台北:环球书局,1966年。
堵胤锡:《堵文忠公集》,十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光绪十三年。
曹永和:《荷兰与西班牙占据时期的台湾》,林熊祥等编《台湾文化论集》,第一册,页105-122,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年。
麦少麟:《民族英雄张家玉》,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第二册,页588-611。
张宗洽:《郑芝龙兄弟究系几人》,《中国史研究》,1980年三期(9月),页167-168。
张城孙:《中英滇缅边界问题》,《燕京学报》一五期,特刊,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7年。
张效乾:《明清两代与越南》,《大陆杂志》三五卷三期(1967年8月),页18-21。
张家玉:《张文烈遗集》,张伯槙编,《沧海丛书》初集第四——六册,影印本,《明清史料汇编》第七四册。
张家璧:《难游录》,《明季野史杂钞》本,手抄本,无日期,北京图书馆缩微胶卷。
张崟:《计六奇与〈明季南北略〉》,《清史论丛》第二辑(1980年),页320-329。
张菼:《郑荷和约签订日期之考订及郑成功复台之战概述》,《台湾文献》一八卷三期(1967年9月),页1-18。
张煌言:《北征得失纪略》,载张寿镛编《张苍水集》,另有选辑《张苍水诗文集》,《台湾文献丛刊》第一四二种,二册。1962年。
张德芳:《〈扬州十日记〉辨误》,《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页365-376,上海:中华书局,1964年。
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影印《粤雅堂丛书》本,1851—1861年。
张麟白:《浮海记》,钱秉镫《所知录》附录,台北:世界书局,1971年。
陆世仪:《江右纪变》,《行朝录》附录,徐友兰辑《绍兴先正遗书》四集第四八册,会稽,1894年。
陆圻:《纤言》,《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第四册。
陈子龙:《陈忠裕年谱》,载王沄编《陈忠裕全集》,1803年。
陈以令:《明代与越南、高棉、寮国的邦交》,《中国外交史论集》第一集,独立页码,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7年。
陈去病(别号有妫血胤):《永历皇帝殉国实纪》,《民报》二三期(1908年8月)《谭丛》,页89-96。
陈世庆:《明郑前后之金门兵事》,《台湾文献》六卷一期(1955年3月),页1-5。
陈田:《明诗纪事》,一八五卷,影印本三十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
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715-744。
陈邦彦:《陈岩野先生全集》,温汝能辑,听松阁,1805年。
陈作鉴:《论洪承畴变节与人才外流》,《畅流》,(一):二七卷一一期(1963年7月),页2-3;(二)二七卷一二期(1963年8月)页2-3;(三)二八卷一期(1963年8月),页12-13。
陈洪范:《北使纪略》,《荆驼逸史》本。
陈贞慧:《书事七则》,在《陈定生遗书》内,《常州先哲遗书》第五册,1895—1898年。
《过江七事》,《痛史》第十一册。
陈国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一期(4月),页158-164。
陈舜系:《乱离见闻录》,在吴宣崇编《高凉耆旧遗集》内,北京图书馆缩微胶卷。
陈碧笙:《一六四六年郑成功海上起兵经过》,《历史研究》1978年八期(8月),页92-93。
陈汉光:《鲁唐交恶及鲁王之死》,《台湾文献》一一卷一期(1960年3月),页106-114。
《明宁靖王及五妃文献》,《台湾文献》二〇卷三期(1969年9月),页45-64。
陈燕翼(别号闽人):《思文大纪》,《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一一种,1967年。
类子匡:《郑成功传说的探讨》,《文史荟刊》二卷(1960年12月),页47-69。《郑成功诞生传说之研究》,《大陆杂志》二二卷八期(1961年4月),页22-25。
《郑成功逝世传说与世界同型故事比较研究》,《台湾文献》,一二卷一期(1961年3月),页25-31。
《从民俗学上看郑成功的丰功伟业》,《新建设》二卷三期(1961年9月),页61-69。
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台湾文献丛刊》第二五四种,1968年。
盛成:《沈光文与明思宗及南渡诸王》,《学术季刊》四卷三期(1956年3月),页42-73。
盛清沂、王诗琅、高树藩:《台湾史》,林衡道编,台中: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7年。
温睿临:《南疆逸史》,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
乐天居士编:《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1912年,重印本,十四册,台北:广文书局,1968年。
冯甦:《滇考》,在宋世荦编《台州丛书》二集内,临海,1817—1821年,《见闻随笔》,《台州丛书》甲集,第七—八册。
冯梦龙编:《甲申纪事》,郑振铎编《玄览堂丛书初集》,第一〇七—八册,上海,1941年。
《中兴伟略》,在《明清史料集》内,长泽规矩也注,东京:岩波书店,1974年。
彭孙贻:《湖西遗事》,张钧衡辑《适园丛书》第一〇七册,吴兴,1913—1917年。
《平寇志》,影印康熙刻本,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
彭国栋:《南明中越关系史话》,《中越文化论集》第二集,页256-266,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
彭普生:《李自成被害日期探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三期(8月),页35-39。
华廷献:《闽事纪略》,《台湾文献丛刊》第二三九种,1967年;《闽游月记》,《荆驼逸史》本。
黄玉斋:《明郑抗清的财政与军需的来源》,《台湾文献》九卷二期(1958年6月),页17-32。
《明郑成功等的抗清与日本》,《台湾文献》九卷四期(1958年12月),页99-126。
《明郑成功北伐三百周年的纪念》,《台北文物》七卷四期(1958年12月),页123-128;八卷一期(1959年4月),页122-128;八卷二期(1959年6月),页116-124;八卷三期(1959年10月),页146-152。
《郑成功时代与日本德川幕府》,《台湾文献》一三卷一期(1962年3月),页114-134。
《明永历帝封朱成功为延平王考》,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文物论集》,页87-94,台北:1966年。
《弘光朝的建立》,《台湾文献》一八卷一期(1967年3月),页88-115。
《弘光朝的史略》,《台湾文献》一八卷三期(1967年9月),页92-118。
《弘光朝的崩溃》,《台湾文献》一八卷四期(1967年12月),页150-177。
《明季三大儒与永历帝》,《台湾文献》一九卷四期(1968年12月),页82-86。
《明隆武帝拥立的经纬》,《台湾文献》二〇卷二期(1969年6月),页128-155。
《明隆武帝的政略》,《台湾文献》二〇卷四期(1969年12月),页142-170。
《明隆武帝与尚书黄道周》,《台湾文献》二一卷一期(1970年3月),页67-102。
《明隆武帝与绍武》,《台湾文献》二一卷二期(1970年6月),页68-105。
黄向坚:《黄孝子寻亲纪程》,《笔记小说大观》第四二一册。
黄仲琴、夏廷棫:《金门鲁监国鲁王墓》,《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六卷六九期(1929年2月),页2805-2808。
黄宗羲:《舟山兴废》,《梨洲遗著汇刊》第二册,台北:隆言出版社,1969年。
《海外恸哭记》,《梨洲遗著汇刊》第二册。
《日本乞师记》,《梨洲遗著汇刊》第二册。
《明夷待访录》,影印《四部备要》本,台北:中华书局。
《四明山寨记》,《梨洲遗著汇刊》第二册。
黄典权:《南明大统历》,台南:景山书林,1962年。
黄淳耀:《黄陶庵先生全集》,陈应鲲编,乾隆二十六年序。
黄开华:《明史论集》,香港:诚明出版社,1972年。
黄道周:《黄漳浦文选》,《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三七种,三册,1962年,选自陈寿祺编《黄漳浦集》,1830年。
黄彰健:《读清世祖实录》,《明清史研究丛稿》,页594-612,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
《读明史余应桂、揭重熙、傅鼎铨三人传》,《明史研究专刊》,一卷(1979年7月),页170-172。
费密:《荒书》,作者1669年序,唐鸿学辑《怡兰堂丛书》第七册,成都,1922年。
《笔记小说大观》,五百册,上海进步书局,民国年间刊,影印本,台北:新兴书店,1960年。
舒翼:《史可法扬州死难考》,《光明日报·史学》,1959年9月17日。
傅以礼:《残明大统历》,《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页8841-8845,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
《明末南方的“佃变”、“奴变”》,《历史研究》,1975年五期(5月),页61-67。
雷亮功:《桂林田海记》,《明季史料丛书》第九册。
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1688年序,尊闻阁,1911年。
万言:《崇袖长编》,《痛史》第一册。
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原题《先王实录》),影印手抄残本,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
杨云萍[杨友濂]:《郑成功焚儒服考》,《台湾研究》一卷(1956年6月),页31-37。
《南明时代与琉球之关系的研究》,《史学汇刊》二卷(1969年8月),页173-187。
《南明时代与日本的关系》,《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六卷(1974年5月),页1-17。
《南明弘光时代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七卷(1975年5月),页157-178。
《南明鲁监国事迹的研究》,《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八卷(1976年5月),页33-61。
《南明永历时代的研究》,《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九卷(1977年4月),页59-88。
《记新得南明钱币》,《钱币天地》二卷一期(1978年1月),页3-7。
杨宽:《一六四五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李光璧编《明清史论丛》,页215-225。
杨德恩:《史可法年谱》,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
杨德泽:《杨监笔记》,罗振玉编《玉简斋丛书》,上虞,1910年。
杨学深:《关于清初“逃人法”——兼论满汉阶级斗争的特点和作用》,《历史研究》1979年十期(10月),页46-55。
漫游野史:《海角遗编》,《虞阳说苑》甲集,第二册,1917年。
廖汉臣:《郑氏世系及人物考》,《文献专刊》一卷三期(1950年),页54-64。
《郑芝龙考》,《台湾文献》十卷四期(1959年12月),页63-72;一一卷三期(1960年9月),页1-15。
《鲁王抗清与二张的武功》,《台湾文献》一一卷一期(1960年3月),页81-105。
《延平王东征始末》,《台湾文献》一二卷二期(1961年6月),页57-84。
《延平王北征考评》,《台湾文献》一五卷二期(1964年),页47-74。
蒙正发:《三湘从事录》,《笔记小说大观》第十编第三册,台北:新兴书局,1975年。
赵令扬:《论南明弘光朝之党祸》,《联合书院学报》四卷(1965年),独立页码。
赵翼:《廿二史札记》,二册,台北:世界书局,1965年。
赵曦明:《江上孤忠录》,《台湾文献丛刊》第二五八种,1968年;其他版本亦有以作者为黄明曦者。
赵俪生、高昭一:《“夔东十三家”考》,《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页154-162,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
潘镇球:《明代北边军政及卫所的崩溃》,《崇基学报》七卷一期(1966年11月),页90-100。
谈迁:《国榷》,张宗祥辑编,六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年。
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三册,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年。
郑成功、郑经:《延平二王遗集》,《增订中国学术名著》第一集第八册,台北:世界书局,1965年。
郑喜文:《明郑史事五则》,《台北文物》十卷一期(1961年3月),页74-84。
邓凯:《也是录》,《明季稗史初编》卷一八。
黎光明:《明末清初之四川》,《东方杂志》三一卷一期(1934年1月),页171-181。
黎杰:《南明广东三忠史迹考》,《珠海学报》三卷(1970年6月),页162-173。
鲁可藻:《岭表纪年》,缩微胶卷手抄本,无日期,台北“中央”图书馆。
刘宗周:《刘子全书》,影印道光刊本,《中华文史丛书》第七辑,第57号,台北:华文书局。
刘家驹:《顺治年间的逃人问题》,《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第二册,页1049-1080,台北:清华学报社,1965—1967年。
刘健:《庭闻录》,《台湾文献丛刊》第二四八种,1968年。
刘翠溶:《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减免赋税的过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三七卷二期(1967年),页757-777。
刘茝:《狩缅纪事》,丁红编辑,在《明末清初史料选刊》内,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滇粹》,页52甲-58乙,影印1909年石印本,杭州:古旧书店,1981年。
刘辉:《史可法评价问题汇编》,香港:杨开书报供应社,1968年。
龙文彬:《明会要》,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赖永祥:《明郑藩下官爵表》,《台湾研究》一卷(1956年),页79-101;二卷(1957年),页47-78。
赖家度:《一六四五年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李光璧编《明清史论丛》,页195-214。
阎尔梅:《阎古古全集》,张相之编,1911年。
钱秉镫:《所知录》四卷:(一)《隆武纪年》,(二)《永历纪年》,(三)《南渡三疑案》,(四)《阮大铖本末小纪》;台北:世界书局,1971年,影印稀见抄本。
《藏山阁集选辑》,《台湾文献丛刊》第二二五种,二册,1966年。
钱肃乐:《钱忠介公集》,张寿镛辑《四明丛书》二集第二册,四明,1932—1948年。
钱:《甲申传信录》,《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第八册。
钱绮:《南明书》(或已失传)。
谢浩:《李郑的事功及其联军与联婚的研析》,《南明暨清领台湾史考辨》,页28-162,台北:著者自印本,1976年《隆武“福京”“选举”考》,《台北文献》四〇卷(1977年6月),页105-192。
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国立北平图书馆,1932年;《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明季奴变》,《清华学报》八卷一期(1932年),无连续页码。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应廷吉:《青燐屑》,《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四。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玄览堂丛书》续集第一二册,南京,1947年。
韩菼:《江阴城守记》,《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第三册。
《明桂王致吴三桂书》,《天津益世报·说苑》,1937年4月24日—26日。
颜虚心:《明史陈邦彦传旁证》,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第二册,页551-587。
瞿元锡:《庚寅十一月初五日始安事略》,《荆驼逸史》本。
瞿式耜:《瞿忠宣公集》,《乾坤正气集》卷五五七——五六四。
瞿共美,别号逸史氏:《东明闻见录》,《明季稗史初编》卷二三。
《粤游见闻》,《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十。
瞿昌文:《粤行纪事》,《笔记小说大观》第二二〇册。
简又文:《南明民族女英雄张玉乔考证》,《大陆杂志》四一卷六期(1970年9月),页1-19。
魏永竹:《郑成功南下勤王之探讨》,《台湾文献》三三卷一期(1982年3月),页131-139。
魏宏运:《史可法》,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
关文发:《试论明朝内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45-65。
罗香林:《狼兵狼田考》,《广州学报》一卷二期(1937年4月),无连续页码。
《香港新发现南明永历四年所造大炮考》,《文史荟刊》一卷一——二期(1959年6月)。
苏同炳:《鲁王使刘忠至杭州赎取王妃及其子案》,《台湾文献》二〇卷三期(1969年9月),页111-117。
《延平王与延平郡王之争平议》,《台湾文献》二四卷二期(1973年6月),页10-13。
《由崇祯六年的料罗海战讨论当时的闽海情势及荷郑关系》,《台北文献》卷四二(1977年12月),页1-39。
苏梅芳:《清初迁界事件之研究》,《历史学报》(台湾成功大学)五卷(1978年7月),页367-425。
苏:《明苏爵辅事略》,东莞,1919年。(未经检阅)
顾炎武:《圣安(皇帝)本纪》,《台湾文献丛刊》第一八三种,第一册,1964年。
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清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第二辑(1980年),页139-157。
《明代的宗室》,《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89-111。
(二)日文
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研究》(清朝前史の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65年。
上田信:《明末清初江南都市围绕着“无赖”的社会关系》(明末清初江南の都市の「無頼」をめぐる社会関係),《史学杂志》90.11(1981年11月),页1-35。
川越泰博:《明代海防体制的运营构造——以创立期为中心》(明代海防体制の運営構造—創成期を中心に),《史学杂志》81.6(1972),页28-53。
川胜守:《明末南京兵士的叛乱——关于明末都市构造的一次素描》(明末南京兵士の叛乱—明末の都市構造についての一素描),《星博士退休纪念中国史论集》,页187-207。山形;论集委员会,1978。
王贤德:《明末动乱时的乡村防卫》(明末動乱期における郷村防衛),《明代史研究》2(1975),页26-49。
中山八郎:《汉地的辫发问题——清初辫发令施行的中心》(漢土に於ける辮髪の問題—清初の辮髪令施行を中心として),《中国史研究》5(1968),页1-24。
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师研究》(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东京:富山房,1945年《郑成功与朱舜水》。《台湾风物》4.8—9(1954年9月),页11-28。
《张煌言的江南江北经略》(张煌言の江南江北経畧),《台湾风物》5.11-12(1955),页7-53。
田村实造:《明朝官俸与银的问题》(明朝の官俸と銀の問題),《东方学会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页475-494,东京:东方学会,1972年。
安野省三:《“湖广熟,天下足”考》(「湖広熟すれば天下足」考)。《木村正雄先生退官纪念东洋史论集》,页301-309,东京:汲古书店。
村上直次郎译:《出岛兰馆日志》,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荷兰东印度公司)三册,东京:文明协会,1939年。
谷光隆:《关于明代勋臣关系的一次考察》(明代の勲臣に関する一考察),《东洋史研究》29.4(1971),页66-113。
佐伯富:《关于明清时代的民壮》(明清時代の民壮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15.4(1957年3月),页33-64。
佐藤文俊:《围绕着明末就藩王府大土地所有的二三个问题——潞王府的情况》(明末就藩王府の大土地所有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潞王府の場合),(一)《木村正雄先生退官纪念东洋史论集》,页235-257,东京:汲古书店,一九七六年,(二)《明代史研究》3(1975年12月),页23-41。
林春胜编:《华夷变态》三册,东京:东洋文库,1958—1959年。
岩见宏:《明代的民壮与北边防卫》(明代の民壮と北辺防衛),《东洋史研究》19.2(1960年10月),页156-174。
竺沙雅章:《关于朱三太子案——清初江南秘密结社关系的考察》(朱三太子案について—清初江南の秘密結社に関する—考察),《史林》62.4(1979),页1-21。
前信次:《关于郑芝龙招安的情况》(鄭芝龍招安の事情について),《中国学志》(1)(1964),页141-170。
浦廉一:《华夷变态解说——唐船风说书研究》(華夷變態解説—唐船風説書の研究),《华夷变态》上册,页2-78。
神田信夫:《平西王吴三桂研究》(平西王呉三桂の研究),《明治大学文学部研究报告·东洋史》第二册,东京:明治大学,1952年。
森正夫:《十七世纪福建宁化县黄通的抗租叛乱》(十七世紀の福建寧化縣における黄通の抗租反乱),《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20(1973),页1-31;21(1974),页13-25;25(1978),页25-65。
《关于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乱》(一六四五年太倉州沙溪鎮における烏龍会の反乱について),《中山八郎教授祝寿纪念明清史论丛》,页195-232,东京:燎原书店,1977年。
《关于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明末社会関係における秩序の変動について),《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三十周年纪念论集》,页135-139,名古屋:名古屋大学,1979年。
清水泰次:《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东京:大安,1968年。
桑原藏:《明庞天寿致罗马教皇之文书》(明の龐天寿より羅馬法皇に送呈せし文書),《史学杂志》11.3(1990年3月),页338-349;11.5(1900年5月),页617-630。
布目潮渢:《明朝的诸王政策及其影响》(明朝の诸王政策とその影響),《史学杂志》(上)55.3(1944年3月),页1-32;(中)55.4(1944年4月),页50-87;(下)55.5(1944年5月),页23-73。
重田德:《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75年。
(三)西文
艾维四(Atwell, William S):《晚明士大夫陈子龙(1608—1647)》(Ch’enTzu-lung[1608—1647]:A Scholar-Official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博士论文,普林斯顿大学,1974年。
《从教育到政治:复社》(From Education to Politics:The Fu She),收《理学的展开》(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第333-367页,狄百瑞(De Bary)主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5。
《1530—1650年间国际金块流通与中国经济》(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95期(1982年5月),第68-90页。
布莱尔(Blair, Emma H.)和罗勃特逊(Robertson, James A):《1493—1898年的菲律宾群岛》(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第55卷鲍恩(Bourne, Edward G.)所作注解与导引,克里夫兰,A.H.克拉克公司,1903—1909。
勃克色(Boxer, Charles R.):《1661—1662年包围台湾城以及从荷兰人手中夺得“福摩萨”》(The Siege of Fort Zeelandia and the Capture of Formosa from the Dutch,1661—1662),《伦敦日本学会学报与记事》(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London),第24期(1926—1927),第16-47页。
《葡萄牙援明抗清的远征》(Portuguese Military Expeditions in Aid of the Mings against the Manchus),《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7卷1期(1938年8月),第24-36页。
《郑芝龙的兴起与没落》(The Rise and Fall of Nicholas Iquan),《天下月刊》,11卷5期(1941年4—5月)第401-439页。
《日本的基督教世纪:1549—1650》(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1549—1650),伯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1951年。
《1600—1800年的荷兰海上帝国》(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1600—1800),伦敦,霍金森,1965年。
波拉(Bowra, E.C.):《满洲人征服广州》(The Manchu Conquest of Canton),《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第1期(1872—1873年),第86-96、228-237页。
卜恩礼(Busch, Heinrich):《东林书院及其政治与哲学意义》(The Tung-lin Academy and Its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cance),《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第14期(1949—1955),第1-163页。
揆一[Frederic Coyett](C.E.S.):《被忽视的“福摩萨”》(Neglected Formosa),德·布克莱尔(Inez de Beauclair)、兰巴克(Pierre Martin Lambach)、坎贝尔(Willian Campbell)和布鲁斯(A.Blussé)编辑和翻译,由台北资料中心(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5年出版,收第21号《增卷》(Occasional Series),原文为1675年阿姆斯特丹印刷的荷兰文。
陈纶绪(Chan, Albert):《明朝的兴盛与灭亡》(The Glory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诺曼,俄克拉何马: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2年。
陈少岳(Chan, David B.):《燕王篡位:1398—1402年》(The Usurpation of the Prince of Yen,1398—1402),旧金山,中国资料中心,1976年。
张天泽(Chang T’ien-tse):《1514至1644年的中葡贸易:中葡文献综述》(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莱顿,1934年。
陈明山(Chen Min-sun):《有关晚明及满洲人征服中国的三种当时的西方资料》(Three Contemporary Western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Late Ming and the Manchu Conquest of China),博士论文,芝加哥大学,1971年。
秦家懿(Ching, Julia):《朱舜水,1600—1682:日本德川时代的中国儒学者》(Chu Shun-shui,1600-1682:A Chinese Confucian Scholar in Tokugawa Japan),《日本学志》(Monumenta Nipponica),30卷2期,(1975年夏)第177-191页。
全汉昇(Chuan, Han-sheng):《明末叶至清中叶中国与西属美洲的丝绸贸易》(The Chinese Silk Trade With Spanish America from the Late Ming to Mid-Ch’ing Period)收《亚洲研究》(Studia Asiatica),第99-117页,劳伦斯·汤普逊(Lawrence Thompson)主编,旧金山,中国资料中心,1975年。
孔贝(Combés, Francisco,与Pablo Pastells合作):《棉兰老与霍洛史》(His-toria de Mindanao y Joló),雷坦那(W.E.Retana)编,马德里:1897年。
科拉迪尼(Corradini, Piero):《清初文治政府:六部建立札记》(Civil Administr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anchu Dynasty:A Not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x Ministries),《远东》(Oriens Extremus)第9期(1962年12月),第133-138页。
顾瑞伯(Crawford, Robert B.):《明朝宦官权力》(Eunuch Power in the Ming Dynasty),《通报》(T’oung Pao)49卷3期(1961年),第115-148页。
《阮大铖传》(The Biography of Juan Ta-Ch’eng),《中国文化》(Chinese Culture)6卷2期(1965年3月),第28-105页。
《儒化法家张居正》(Chang Chü-Cheng’s Confucian Legalism),收《明代思想与社会》(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狄百瑞主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0年。
郭适(Croizier, Ralph.C):《国姓爷与中国民族主义:历史,神话,英雄》(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History, Myth, and the Hero),《哈佛东亚论文集》(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第67卷,康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
狄百瑞:《中国专制主义与儒家理想:十七世纪的观点》(Chinese Despotism and the Confucian Ideal:A Seventeenth-Century View),收《中国的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第163-203页。费正清主编,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年。
邓尔麟(Dennerline, Jerry):《财政改革与地方控制:官绅联盟经历满洲人的征服继续存在》(Fiscal Reform and Local Control:The Gentry-Bureaucratic Alliance Survives the Conquest),收《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86-120页,魏斐德和卡罗林·格兰特主编。伯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1975年。
《许都与南京的教训:政治统一和江南的地方防御》(Hsu Tu and the Lesson of Nanking: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Local Defense in Chiangnan,1634—1645),收《从明到清》(From Ming to Ch’ing),第92-132页。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卫思韩(John E.Wills, Jr.)主编。
《嘉定忠臣录:十七世纪中国儒家领导与社会变革》(The Chia-ting Loyalists:Confucian Leadership and Social Chan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
《满洲人征服中国与顺治朝》(The Manchu Conquest and the Shun-chih Reign),1982年,《剑桥中国史》(第9卷,待出版)抽印本。
戴德(Dreyer, Edward L.):《1363年鄱阳湖之战:明朝建立时的内陆水战》(The Poyang Lake Campaign,1363:Inland Naval Warfare in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收《中国战法》(Chinese Ways in Warfare),第202-242页,柯尔曼(Frank Kierman, Jr.)编。
《明初政治史:1355—1435年》(Early Ming Government:APolitical History,1355—1435),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2年。
艾利逊(Elison, George):《上帝被毁:日本近代史初期的基督教形象》(Deus Destroyed:The Image of Christianity in Early Modern Japan),康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
伊懋可(Elvin, Mark):《市镇与水道:1480至1910年的上海县》(Market Towns and Waterways:The County of Shanghai from 1480 to 1910),史坚雅(Wm.Skinner)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第441-473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
房兆楹(Fang Chao-ying):《早期满洲军队人力的估计方法》(A Technique for Estimating The Numerical Strength of the Early Manchu Military Forces),《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3卷1—2期(1950年6月),第192-215页。
范德(Farmer, Edward):《明初政府:两京的演变》(Early Ming Government: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哈佛东亚论文集》,第66卷,康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
菲力克斯(Felix, Alfonso, Jr.)编:《1570—1770年的菲律宾华人》(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1570—1770),马尼拉,苏里达利达出版社,1966年。
费兹帕屈克(Fitzpatrick, Merrilyn):《中国东南的地方利益和反海盗管理》(Local Interests and the Anti-Pirate Admimstration in China’s South-east),《清史问题》,4卷2期(1979年12月),第1-33页。
富路特(Goodrich, L.C.)和房兆楹编:《明代名人传》(A Dictioonary of Ming Biography),2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
林懋(Grimm, Tilemann):《明初至1506年的内阁》(Das Neiko der Ming-Zeit von den Anfangen bis 1506),《远东》,1卷(1954年),第139-177页。
奚孙凝芝(Hsi, Angela):《重新评价1644年的吴三桂》(Wu San-kuei in 1644:A Reappraisal),《亚洲研究学报》,34卷2期(1975年2月),第443-453页。
许文雄(Hsu Wen-hsiung):《从土著岛屿到中国边疆:1683年前台湾的发展》(From Aboriginal Island to Chinese Frontier: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before 1683),收《中国的岛疆:台湾历史地理研究》(China’s Island Frontier: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aiwan),第3-28页,那仲良(Ronald G.Knapp)编,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0年。
亭奥(Htin Aung, Maung):《缅甸史》(A History of Burma),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
黄仁宇(Huang, Ray):《明代财政》(Fisc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收《明代的中国政府》(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第73-128页,贺凯(Charles O.Hucker)编。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军事开支》(Military Expenditures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远东》,17卷(1970年),第39-62页。
《倪元璐:新儒家学者政治家的现实主义》(Ni Yüan-lu:Realism in a Neo-Confucian Scholar-Statesman),收《明代思想与社会》,第415-419页。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赋税与财政》(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4年。
《万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canc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
《1619年辽东之役》(The Liao-tung Campaign of 1619),《远东》28卷1期(1981),第30-54页。
贺凯(Hucker, Charles O.):《明末东林运动》(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收《中国的思想与制度》,第132-163页。
《明代监察制度》(The Censorial System of Ming China),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
《明朝政府组织》(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收《中国历史上的政府制度研究》(Studies of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in Chinese History),第57-124页。毕绍甫(John L.Bishop)主编。
《1556年胡宗宪击徐海之战》(Hu Tsung-hsien’s Campaign against Hsü Hai 1556),收《中国战法》,第273-307页。
贺凯编:《明代中国政府研究七篇》(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东方文化研究》(Studies in Oriental Culture)第2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年。
恒慕义(Hummel Arthur)编:《清代名人传》(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2册,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1943年。
李成珪(I Songgyu):《顺治时期的山东:地方控制的建立以及缙绅的反应》(Shantung in the Shun-chih Reign: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Control and the Gentry Response),最初发表在韩国《大东洋史学科论集》第1期(1977年)。由山根幸夫和稻田英子译为日文,刊《明代史研究》第6期(1979年),第25-47页。傅佛果(Joshua Fogel)日译英,刊《清史问题》(1)4卷4期(1980年12月),第1-34页;(2)4卷5期(1981年6月),第1-31页。
岩生成一(Iwao Seiichi):《十六与十七世纪日本对外贸易》(Japanese For-eign Trad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亚洲》(Acta Asiatica),第30期(1976年),第1-18页。
颜复礼(Jäger, Fritz):《瞿武耜的最后时日》(Die letzen Tage des Kü Schisi),《中国》8卷5—6期(1933年),第197—207页。
基恩(Keene, Donald):《国姓爷诸战役:近松的傀儡剧及其背景与意义》(The Battles of Coxinga:Chikamatsu’s Puppet Play, Its Background and Importance),伦敦,泰勒外文出版社,1951年。
柯尔曼(Kierman, Frank, Jr.):《中国战法》(Chinese Ways in Warfare),《哈佛东亚丛书》第74号,康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
列文森(Levenson, Joseph R.):《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y),伯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1968年。
李龙华(Li Lung-wah):《明季对川贵边界地区的控制:明朝政府边疆政策及土司制度的个案研究》(The Control of the Szechwan-Kweichow Frontier Regions during the Late Ming:A Case Study of the Frontier Policy and Trib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Ming Government),博士论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8年。
雷伯曼(Lieberman, Victor B.):《1540至1620年间缅甸的欧洲人:贸易与统一》(Europeans, Trade, and the Unifcation of Burma,1540—1620),《远东》,27卷2期(1980年),第203-226页。
《冬努缅甸的省政改革》(Provincial Reforms in Toung-ngu Burma),《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公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Studies),43卷3期(1980年),第548-569页。
《缅甸首都由攀固移至阿瓦》(The Transfer of the Burmese Capital from Pegu to Ava),《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80年第1卷,第64-83页。
赖特(Lighte, Peter R.):《云南的蒙古人与沐英——在帝国边缘》(The Mongols and Mu Ying in Yunnan—At the Empire’s Edge),博士论文,普林斯顿大学,1981年。
刘约瑟(Liu, Juseph):《史可法(1601—1645)与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She Kefa[1601—1645]et le contexte politique et social de la Chine an moment de I’invasion mandchoue),博士论文,巴黎大学,1969年。
罗荣邦(Lo, Jung-Pang):《明初水师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远东》,5卷(1958年),第149-168页。
《有关和战问题的筹划和决策》(Policy Formul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on Issues Respecting Peace and War),收贺凯编:《明代中国政府研究七篇》。
马奉琛(Ma, Feng-Ch’en):《清初满汉间的社会与经济冲突》(Manchu-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ficts in Early Ch’ing),收《中国社会史》(Chinese Social History),第333-351页,孙以都(E-tu Sun)和德范克(John de Francis)编,华盛顿特区,美国学会联合会,1956年。
马克穆伦(McMorran, Ian):《爱国者与党人:论王夫之与永历朝政治》(The Patriot and the Partisans:Wang Fu-chih’s Involvement in the Politics of the Yung-li Court),收《从明到清》,第136-166页。
毛如昇(Mao, Lucien)译:《扬州十日记》,《天下月刊》,4卷5期(1937年5月),第515-537页。
马丁努斯(Martinus, Martin):《鞑靼战史:声名最著的中华大帝国之征服》(Bellum Tartaricum, or 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原文为拉丁文,译为英文。伦敦,约翰·克鲁克,1654年。
梅林克-劳鲁夫兹(Meilink-Roelofsz, M.A.P.):《十七世纪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发展诸方面》(Aspects of Dutch Colonial Development in As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收《不列颠和尼德兰在欧亚》(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n Europe and Asia),第3卷,第56-82页,布鲁姆利(J.S.Bromley)和柯斯曼(E.H.Kossmann)编,纽约,麦克米伦,1968年。
梅谷(Michael, Franz):《满洲统治中国溯源》(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42年。
牟复礼(Mote, Frederick):《中国专制主义的成长:评以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魏特夫理论》,(The Growth of Chinese Despotism:A Critique of Wittfogel’s Theory of Oriental Despotism as Applied to China),《远东》,第8卷(1961年),第1-41页。
《诗人高启,1336—1374年》(The Poet Kao Ch’i,1336—1374),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
《1449年土木之变》(The T’u-Mu Incident of 1449),收《中国战法》,第243-272页。
《南京的转变,1350—1400年》(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1350—1400),收《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第101-153页。
黎安友(Nathan, Andrew J.):《中共政治派系模式》(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53卷(1973年1—3月),第34-66页。
吴振强(Ng, Chin-keong):《明朝后半期福建人的海上贸易——政府政策与中坚集团的态度》(The Fukienese Maritime Trad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Ming Period—Government Policy and Elite Groups’ Attitudes),《南洋大学学报》(Nanyang University Journal),5卷2期(1971年),第81-100页。
《1506—1644年闽南农民社会研究》(A Study of the Peasant Society of South Fukien,1506—1644),《南洋大学学报》,6卷,第189-212页。
纽霍夫(Nieuhoff, John):《从联合诸省的东印度公司出使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An Embassy from the East 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约翰·奥吉比(John Ogilby)翻译,曼斯顿,学术出版社,1669年。
安熙龙(Oxnam, Robert B.):《马上治之:1661—1669年的满洲政治与鳌拜辅政》(Ruling from Horseback:Manchu Politics and the Oboi Regency,1661—1669),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5年。
帕森斯(Parsons, James B.):《一次中国农民暴乱的高峰:1644—1646年间张献忠在四川》(The Culmination of a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Chang Hsien-chung in Szechuan,1644—1646),《亚洲研究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卷3期(1957年5月),第387-400页。
《明末农民叛乱》(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亚洲研究协会论文》(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Monographs and Papers)第26号,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70年。
伯希和(Pelliot, Paul):《卜弥格》(Michel Boym),《通报》,31卷1—2期(1935年),第95-151页。
罗友枝(Rawski, Evelyn Sakakida):《华南农业变化与农民经济》(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康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
罗茂锐(Rossabi, Morris):《穆斯林与中亚的叛乱》(Muslim and Central Asian Revolts),收《从明到清》,第170-199页。
陆西华(Roth, Gertraude):《满洲与中国关系》(The Manchu-Chinese Rela-tionship),收《从明到清》,第4-36页。
鲁德福(Rudolph, Richard C.):《明监国鲁王真墓》(The Real Tomb of the Ming Regent Prince of Lu),《华裔学志》,第29卷(1970—1971年),第484-495页。
沙加(Sakai, Robert K.):《萨摩封邑琉球群岛》(The Ryukyu Islands as a Fief of Satsuma),收《中国人的一统世界》,第112-134页,费正清编,《哈佛东亚丛书》,第32种,康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
沙松(Sansom, George):《1334—1615年日本史》(A History of Japan,1334—1615),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1年。
《1615—1867年日本史》(A History of Japan,1615—1867),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3年。
萧大伟(Shore, David H.):《明代中国的最后一朝:南方的永历政权(1647—1662)》(Last Court of Ming China:The Reign of the Yung-li Emperor in the South,1647—1662),博士论文,普林斯顿大学,1976年。
苏均炜(So, Kwan-wai):《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日本海盗》(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东兰辛,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75年。
《对大学士严嵩的新评价》(Grand Secretary Yan Song:A New Appraisal),收《中国史和中美关系论文集》(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第1-39页。《东亚丛书》,增刊第7期,东兰辛,密歇根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82年。
史景迁(Spence, Jonathan)和卫思韩(John E.Wills):《从明到清:十七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区和连续性诸问题》(From Ming to Ching: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年。
司蒂斯哥哈德(Steensgaard, Niels):《十七世纪的亚洲贸易革命:东印度公司与陆上商队贸易的衰落》(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aravan Trad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3年。
司徒琳(Struve, Lynn):《影响广州三角洲地区南明诸事件概述》(A Sketch of Southern Ming Events Affecting the Canton Delta Area),广州三角洲讨论会提交论文,香港大学1973年4月。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历史的运用:清代历史著述中的南明》(Uses of Histo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e Southern Ming in Ch’ing Historiography),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1974年。
《康熙时期几位郁郁不得志的学者:其矛盾心理与所作所为》(Ambivalence and Action:Some Frustrated Scholars of the K’ang-hsi Period),收《从明到清》,第324-365页。
《徐氏兄弟及康熙时期对学者的半官方扶助》(The Hsü Brothers and Semioffcial Patronage of Scholars in the Kang-hsi Period),《哈佛亚洲研究学报》,42卷1期(1982年6月),第231-266页。
《悲惨结局:永历帝死期考》(The Bitter End:Notes on the Demise of the Yongli Emperor),《明史研究》(Ming Studies),21卷(1986年春),第62-76页。
托比(Toby, Ronald P.):《重论锁国问题:为使德川幕府取得合法地位所做的外交活动》(Reopening the Question of Sakoku:Diplomacy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okugawa Bakufu),《日本研究学报》(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3卷2期(1977年夏),第323-363页。
《近代日本早期的国家与外交》(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As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kugawa Bakudu)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
曹介夫(Tsao, Kai-fu):《康熙与三藩之乱》(Kang-hsi and the San-fan War),《华裔学志》,第31卷(1974—1975年)第108-130页。
冯克莱(Van Kley, Edwin J.):《来自中国的消息:十七世纪有关满洲人征服的记录》(News from China:Seventeenth-Century Notices of the Manchu Conquest),《近代史学报》(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45卷4期(1973年12月),第561-582页。
和田清(Wada Sei):《有关满洲开国者太祖兴起的若干问题》(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Rise of T’ai-tsu, Founder of the Manchu Dynasty),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ōyōBunko,第16卷(1957年)35-73页。
魏斐德(Wakeman, Frederic, Jr.):《清朝征服江南期间的地方主义与忠明情绪:江阴的悲剧》(Localism and Loyalism during the Ch’ing Conquest of Kiangnan:The Tragedy of Chiang-yin),收《晚期中华帝国的冲突与控制》,第43-85页。
《1644年的大顺政权》(The Shun Interregnum of 1644),收《从明到清》,第43-87页。
王伊同(Wang, Yi-T’ung):《1368—1549年的中日官方关系》(Off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1368—1549),康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
魏波渡(Weithoff, Bodo):《中国第三条边界:传统中国国家与沿海地区》(China dritte Grenze:Der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Staat und der küstennahe Seeraum),威斯巴登:奥托·哈拉苏威兹,1969年。
卫德明(Wilhelm, Hellmut):《多尔衰、史可法的通信》(Ein Briefwechsel zwischen Durgan and Schi Ko-Fa),《中国》,8卷5—6期(1933年),第239-245页。
卫思韩(Wills, John E.,Jr.):《胡椒、枪炮与谈判:1662—1681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Pepper, Guns, and Parleys: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1662—1681),康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
《从汪直到施琅的海上中国》(Maritime China from Wang Chih to ShihLang),收《从明到清》,第203-238页。
吴缉华(Wu Chi-hua):《明代中国北边防线的后退》(Contraction of Forward Defenses on the North China Frontier during the Ming Dynasty)、《远东史论文》(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太平洋研究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第17卷(1978年3月),第1-13页。
山胁悌二郎(Yamawaki Teijirō):《大贸易商、国姓爷及其子嗣》(The Great Trading Merchants, Cocksinja and His Son),《亚洲》(Acta Asiatica)第30卷(1976年),第106-116页。
英千里(Ying-Ki, Ignatius):《明朝最后一位皇帝》(The Last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Catholicity),《辅仁大学学报》(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第1期(1925年),第23-28页。
中西日历对照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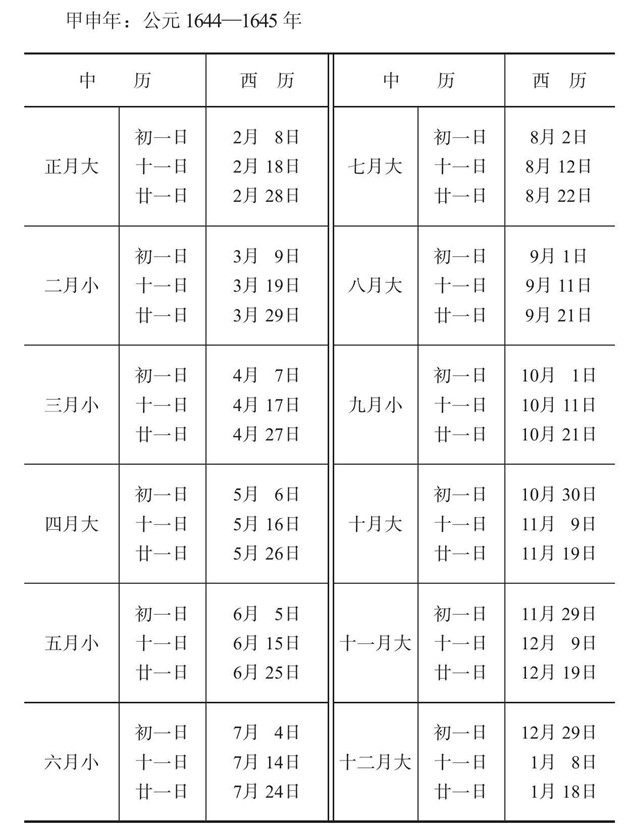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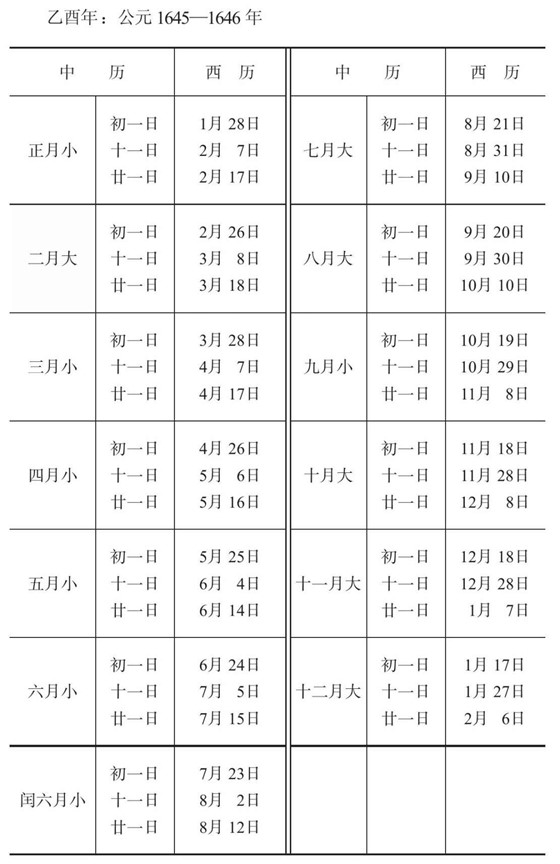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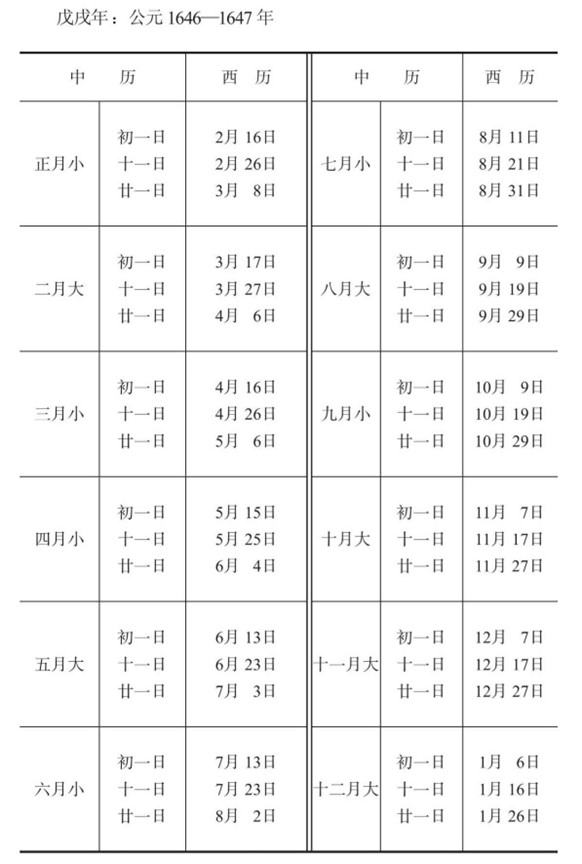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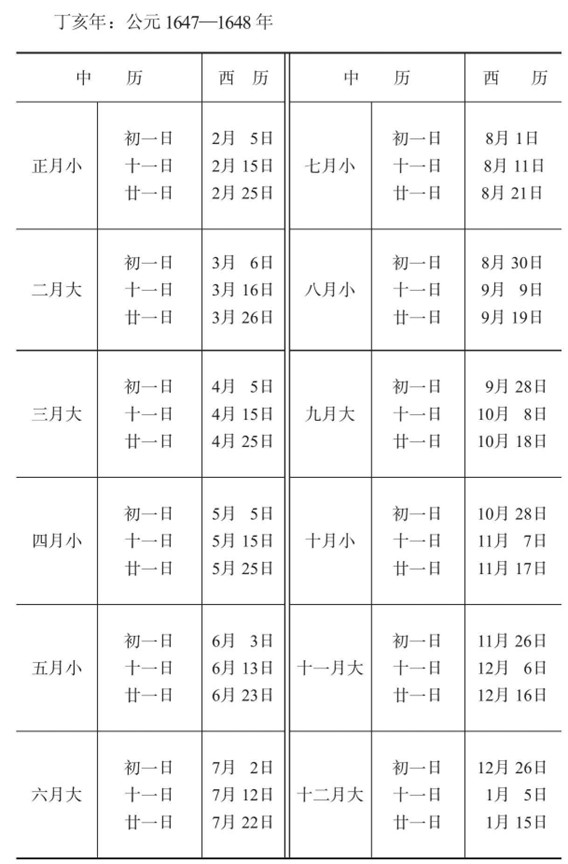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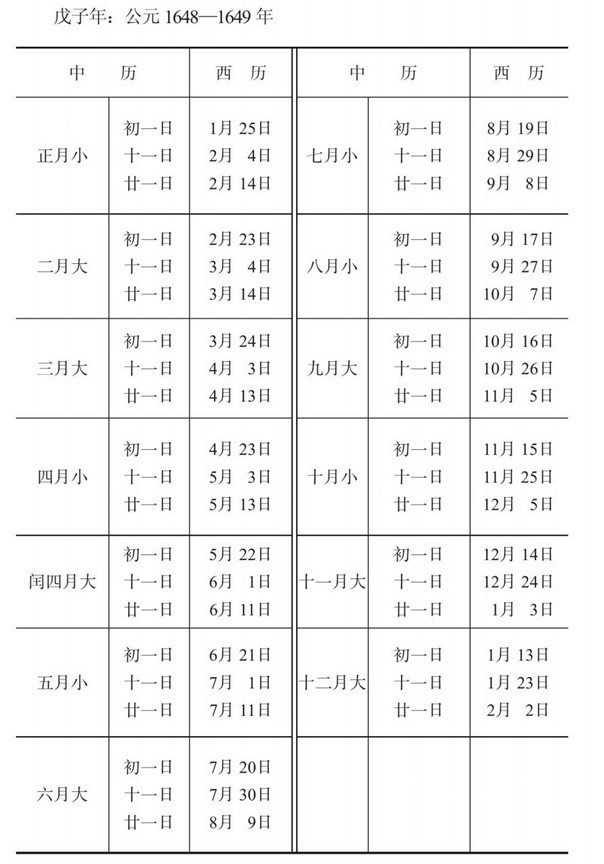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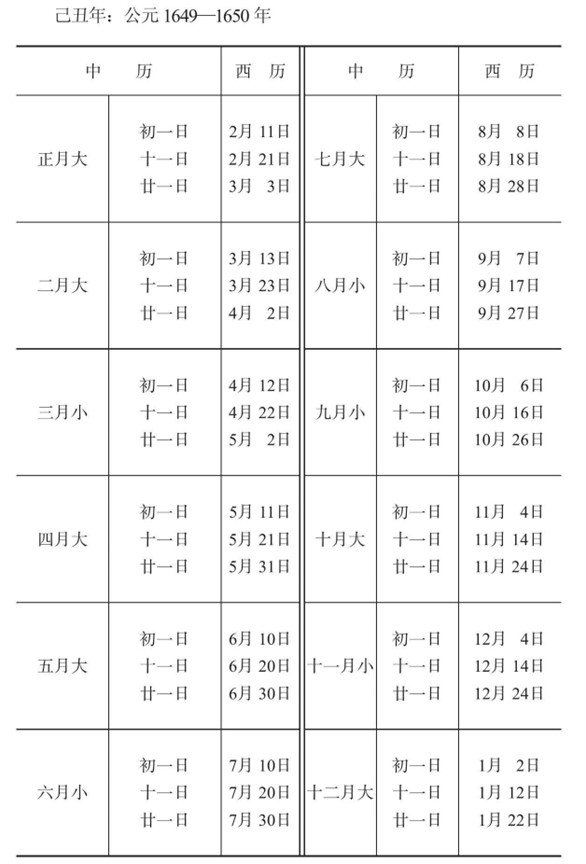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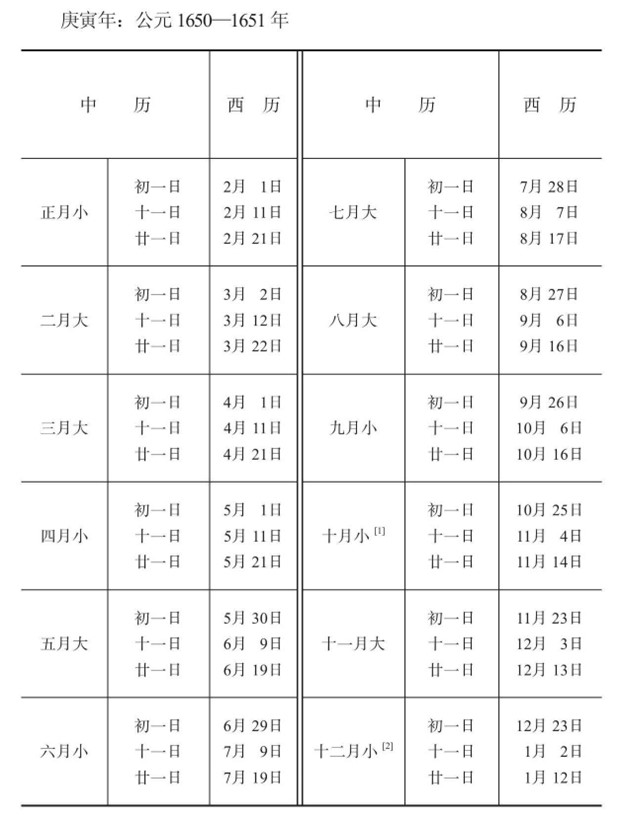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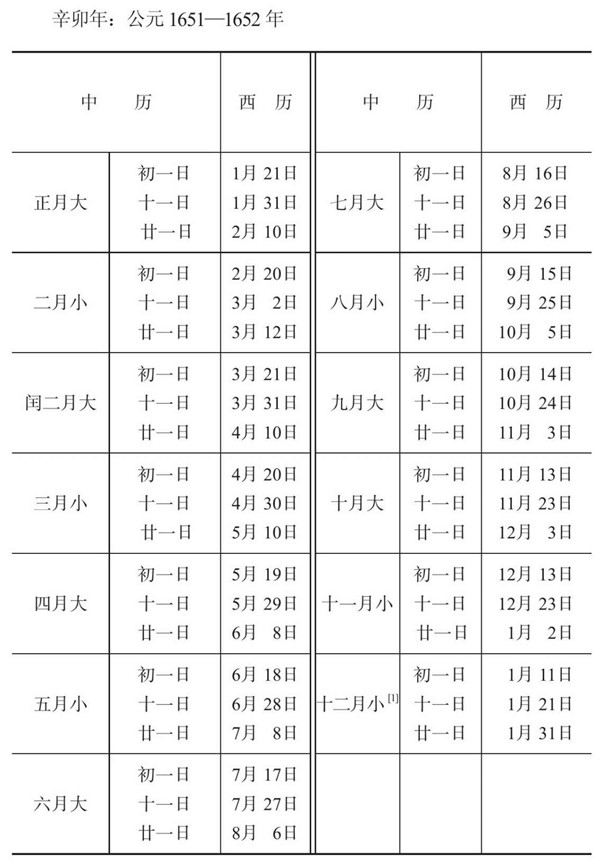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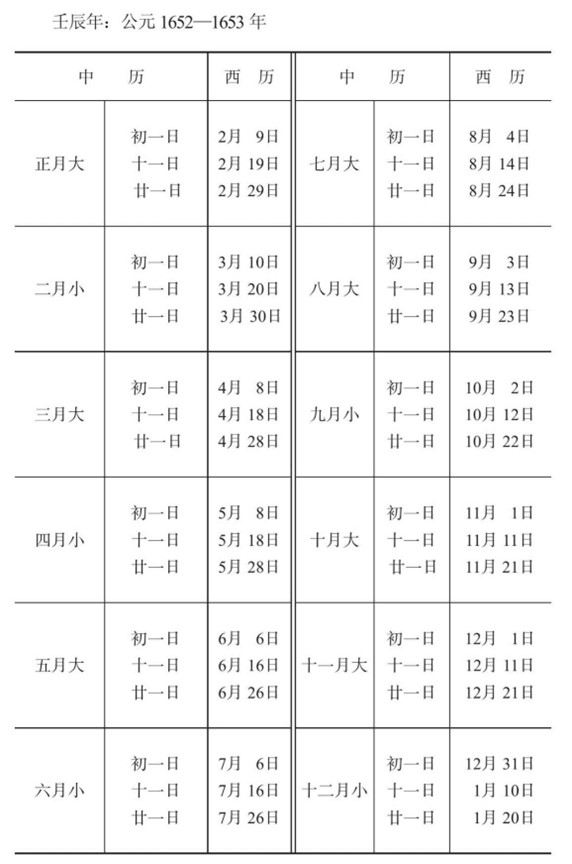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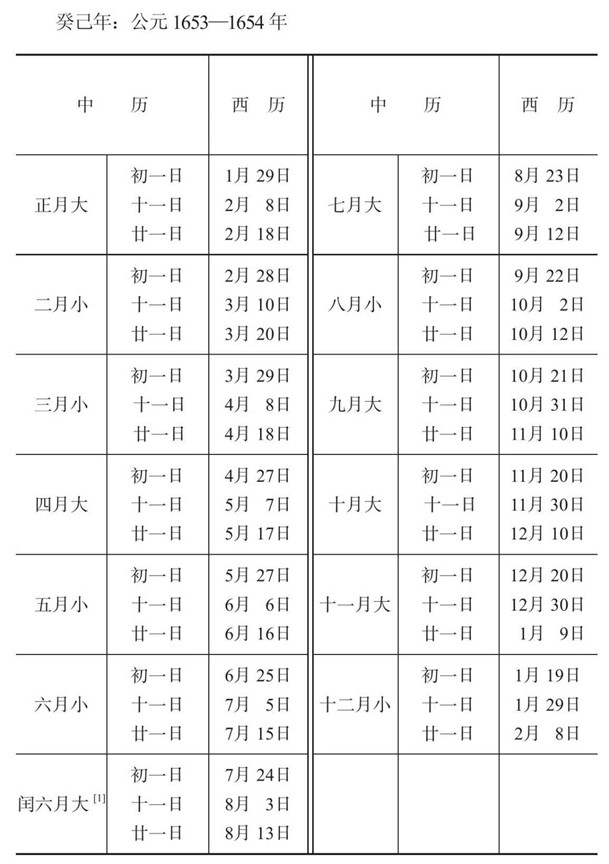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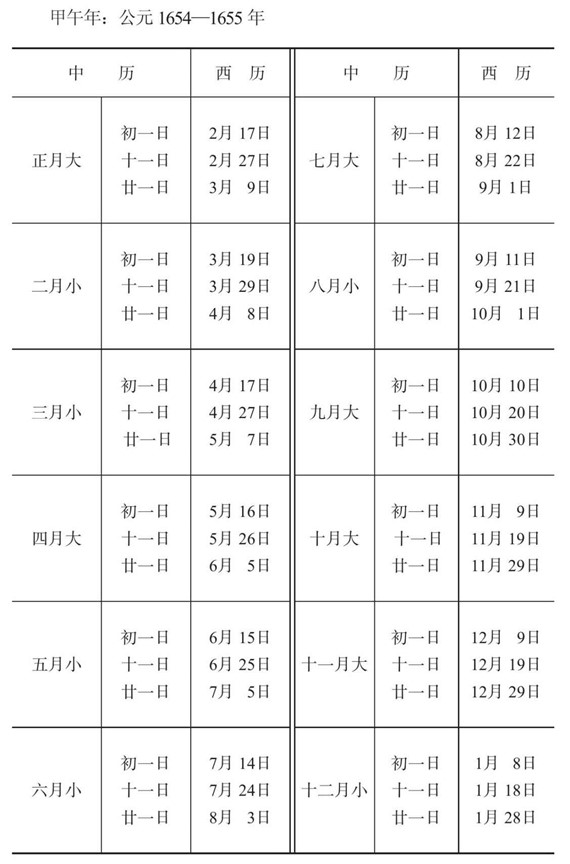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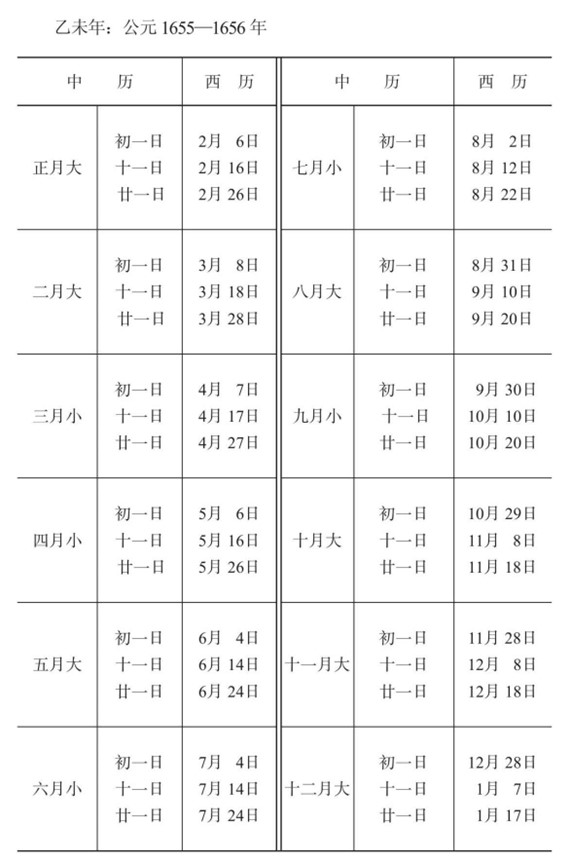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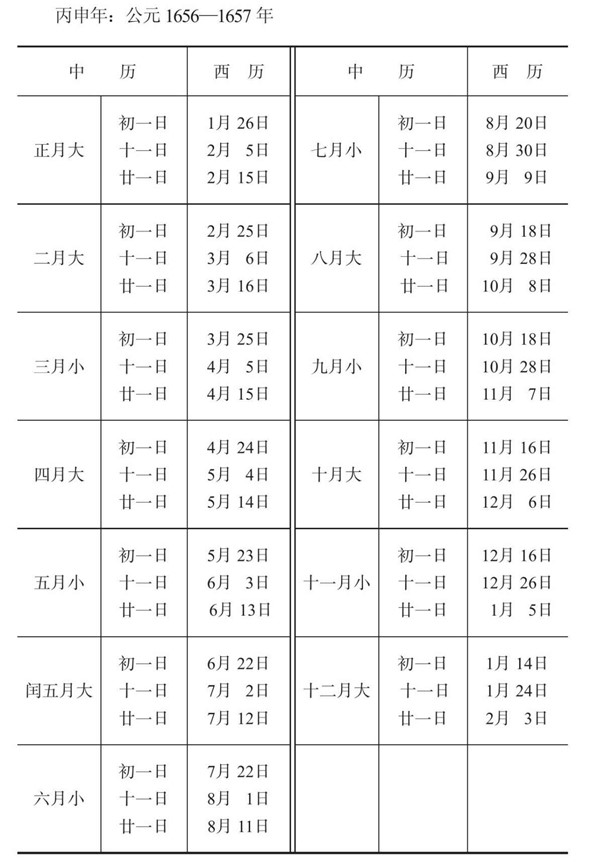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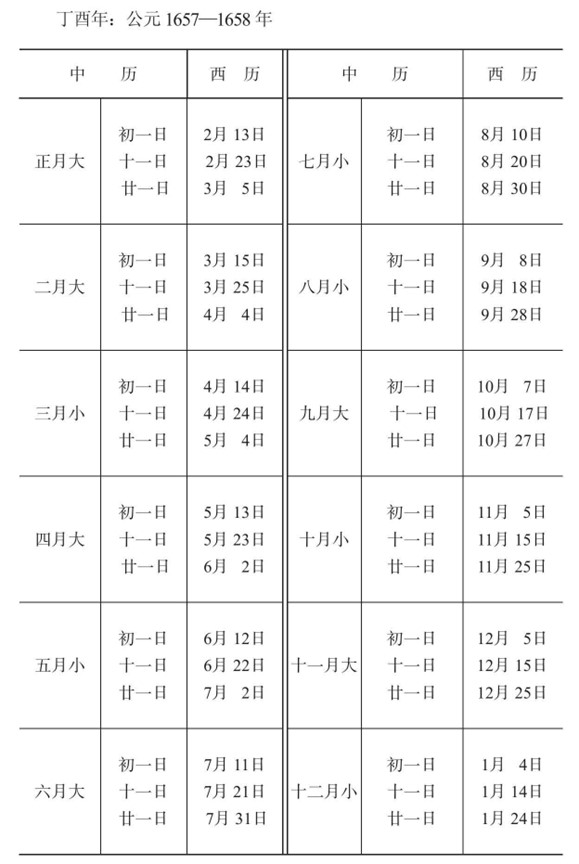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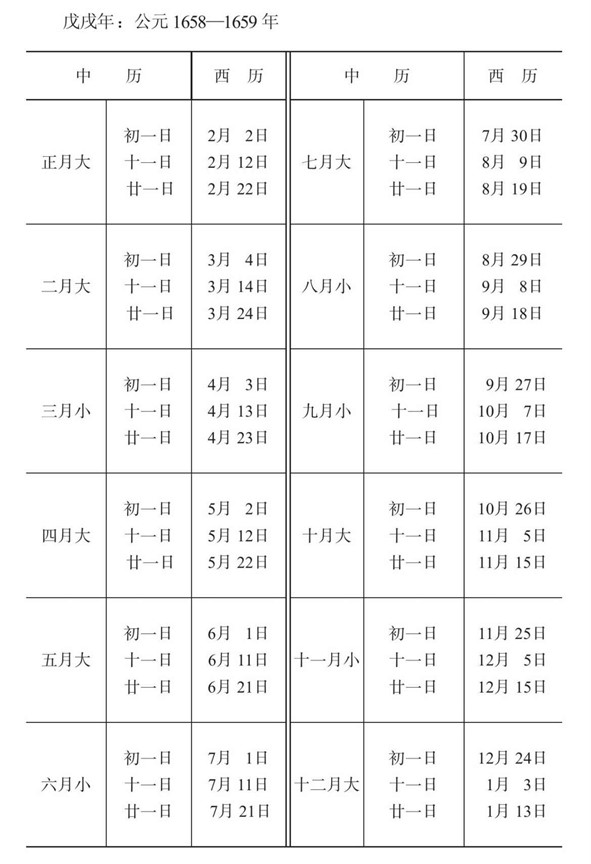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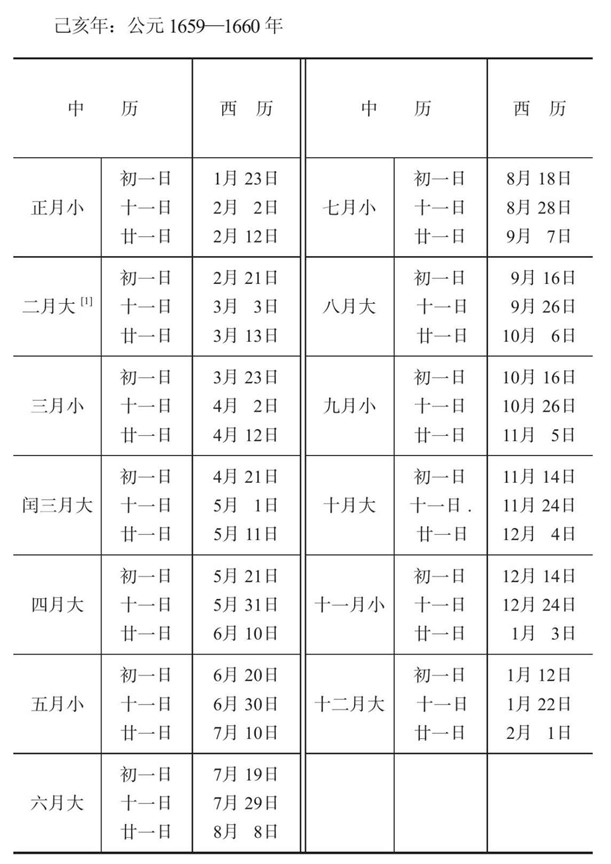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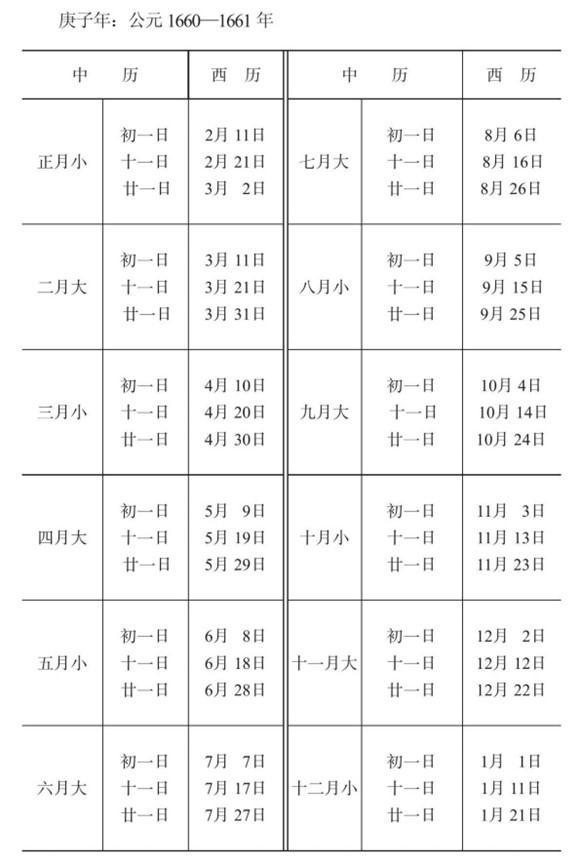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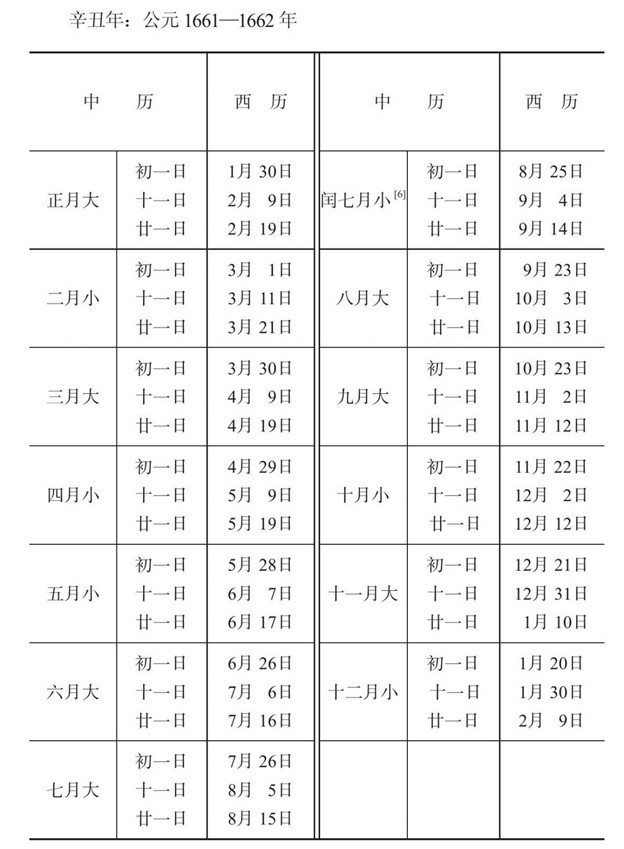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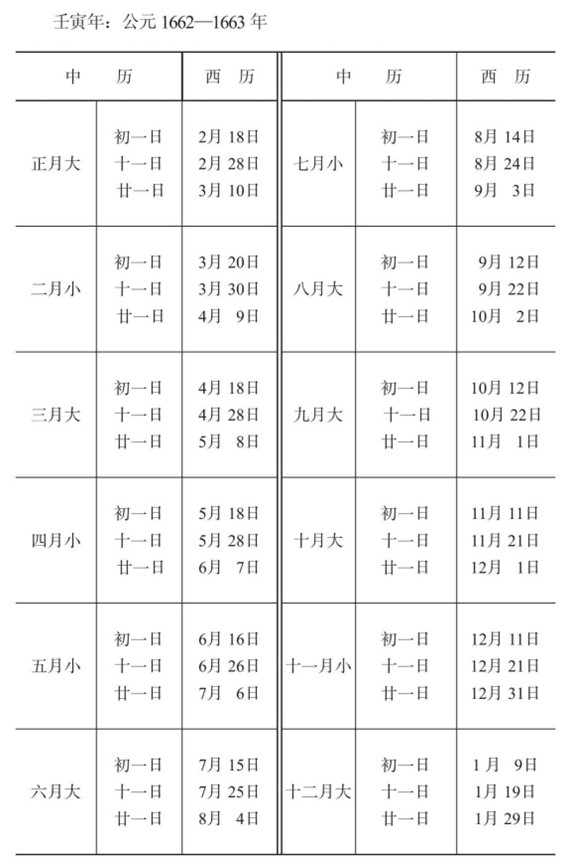
明清之际年号对照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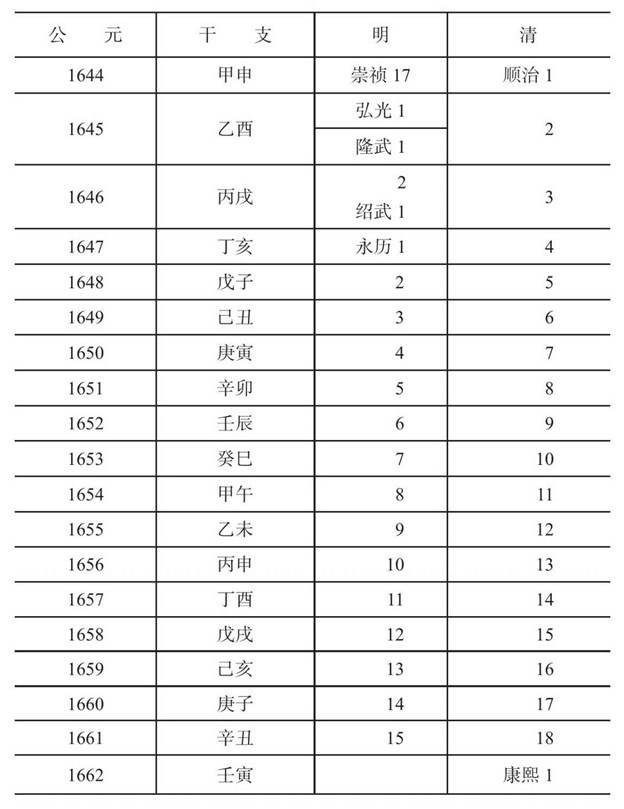
中文版后记
1988年夏,我获知在郑州有一群年轻学者——李荣庆、郭孟良、卞师军、魏林——在秦佩珩教授勉励之下,着手将拙著《南明史》译成中文。我对此至为感谢。不幸的是,1989年6月秦教授去世,因此翻译只完成了初稿。1989—1990年冬季,我到中国作短期访问,从李荣庆君处获得了初稿。其后,在我主持之下,我的胜任愉快的研究助手严寿澂君将此初稿重作校译,注释及参考书目亦全部译出。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阎崇年教授对译本提出了不少的看法和建议,裨益匪浅。本书为数不少的地图,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诸位学者予以审查。复旦大学历史系朱维铮教授,作为印第安纳大学高级学院客座教授,在印大应我的请求花了大量心血,对译文从头至尾仔细作了校订、润色。
承蒙上述诸位对拙著表示兴趣,并耗费了大量时间,译本已较原文更胜一筹。我也乘此机会修改了一些错误(当然错误还有不少)。17世纪文献中的术语,还有引文,用英文来写自然不及中文,我当然希望将拙著译成地道的现代汉语学术文体,以便对历史有兴趣的中国读者易于理解。但是在有些场合,我所使用的概念,与中国史学文章中通常表达的甚为不同。为求保持原意不走样,有些词语和句子结构读来难免佶屈聱牙,但不得不如此,因为将拙著译成中文出版,一个主要原因,是让读者了解,如何以非中国式的方法来解释中国历史。遇到这类艰涩之处,要把握其意义,自须多费精神,我希望读者诸君不会介意。
另一难题是:历史文献中的日期,依据的是中国旧历,还有不同政治系统的年号;而本书原是为西方读者而写的,因此书中日期一律改用西元格利高里历(即今日通用的公历)。为避免正文中夹杂大量日期换算,同时也为便利专业研究者参考原始资料,中译本后附有中西历对照表。
拙著有许多缺点,我自开始撰写以来,对此即有体会。另有一些疏误,已在有关拙著的书评中为人指出;当然书评作者一般是与人为善的。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在拙著译成中文之际,将其中有些部分大加修订。我写这部《南明史》,已是九年之前的事。当时未能得到的若干重要资料,现在已到我手边;当时未能利用的较好版本,现在亦已印出。不过,除去一例之外,我对拙著中所引用的资料,既未作增加,亦不予改动,因为这类工作一旦着手,几乎是没有止境的。我另在撰写一部自17世纪直至今日的南明史学史,其中包括主要原始文献介绍。有关的文献与版本,该书著录较多,资料亦更新。
附录《引用书目》,只包括某些章节中引用的各种著作,其目的绝不在于为南明研究开列详细书单。读者会发现,20世纪中国史学名家谢国桢、李洵、孟森、萧一山等人的南明史论说,未在书目中列出,尽管我在当研究生时即已熟悉这些著作。原因在于,我希望对这一个时代形成我自己的观点,对各类事件作出我自己的解释。因此我关注的资料,一是原始文献,二是有助于在技术上对原始资料作出处理的第二手著作。“引用书目”中开列的,主要是这两类著作,而不是现代人所撰述的其他南明史著作。
1644年至1662年的历史错综复杂,要在一篇之内予以叙述,只能是概括性的。我写《南明史》的目的,不是为这段历史作定论,而是希望由此激发他人,对这二十年间过渡时期的重要历史下更多功夫,让17世纪中国的历史能上下贯穿,而不是划分成明季、清初两大块。拙著中译本的出版,若能使此一想法更加为人所接受,我将不胜荣幸。
司徒琳
印第安纳大学
1990年10月
注解
1卒于咸丰年间(1851—1861)的钱绮,据说著有《南明书》。参看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二,页55甲。
2《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运用:清朝史籍中的南明》(Uses of Histo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The Southern Ming in Ch’ing Historiography),密歇根大学。
3《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4]卫思韩(John E.Wills),1983年1月11日私人通信。
[5]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近著《洪业:清朝开国史》(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198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满洲人征服中国与顺治朝》(The Manchu Conquest and the Shun-chih Reign),刊载于《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九卷第一册,为其中一章。
[6]有关“明清之际变迁”的范围问题,《从明到清:十七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区和连续性诸问题》(以下简称《从明到清》)(From Ming to Ching: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1979年纽黑文版)一书的编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卫思韩业已在该书的前言中提出。
[7]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The Shun Interregnum of 1644),载《从明到清》,43-87页。并参看恒慕义(Arthur Hummel)编二卷本《清代名人传》(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943年华盛顿版)中崇祯帝朱由检和李自成传:第一卷,191-192页,第二卷,491-492页。
[8]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1年天津版),715-744页。奚孙凝芝(Angela Hsi):《重新评价1644年的吴三桂》(Wu San-kuei in 1644:A Reappraisal),载《亚洲研究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三四卷二期(1975年2月),443-453页。李光涛:《多尔衮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载《明清史论集》(1971年台北版),第二卷,443-448页。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载《历史研究》1978年五期(五月),76-82页。并参看《清代名人传》中多尔衮与吴三桂传:第一卷,215-219页,第二卷,877-880页。
[9]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研究》(《清朝前史の研究》,1965年京都版)。梅谷(Franz Michael):《满洲统治中国溯源》(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1942年巴尔的摩版)。和田清(Wada Sei):《有关满洲开国者太祖兴起的若干问题》(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Rise of T’ai-tsu, Founder of the Manchu Dynasty),载《东洋文库研究部纪要》(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16卷(1957年),35-73页。皮埃罗·科拉迪尼(Piero Corradini):《清初文治政府:六部建立札记》(Civil Administr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anchu Dynasty:A Not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x Ministries[Liu-pu]),载《远东》(Oriens Extremus),九卷(1962年),133-138页。陆西华(Gertraude Roth):《1618至1636年的满洲与中国关系》(The Manchu-Chinese Relationship,1618-1636),载《从明到清》,4-38页。并参看《清代名人传》中皇太极与努尔哈赤传:第一卷,1-3页,594-599页。
[10]贺凯(Charles O.Hucker):《明末东林运动》(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载费正清(John K.Fairbank)编《中国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156页。
[11]李光涛:《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十二本(1947年),193-236页。满洲力量兴起之际,大规模暴动自内部耗竭了明朝的精力与资源。有关重要著作有下列三种:李文治著《晚明民变》(1948年上海版)、李光涛著《明季流寇始末》(1965年台北版)、詹姆斯·帕森斯(James B.Parsons)著《明末农民叛乱》(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1970年图森版)。
[12]参看黄仁宇(Ray Huang):《万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cance,1981年纽黑文版),第一章。此书对万历帝作了异乎寻常的同情刻画,不过并没完全回避万历帝所引起的问题。有关万历帝的更为标准的传记,参看富路特(L.C.Goodrich)、房兆楹(Fang Chao-ying)合编二卷本《明代名人传》(A Dictionairy of Ming Biography,1976年纽约版)中朱翊钧传:第一卷,324-338页。有关万历朝争执详情,参看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934年上海版),14-45页。有关明朝最后数十年间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大概情形,参看陈纶绪(Albert Chan)《明朝的兴盛与灭亡》(The Glory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1982年俄克拉何马州诺曼版),第二部,《明帝国的衰落》(The Ming Empire in Decline)。
[13]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赋税与财政》(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1974年剑桥版),全书各处。同一作者《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军事开支》(Military Expenditures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载《远东》,一七卷(1970年),39-62页。
[14]戴德(Edward L.Dreyer)所著《明初政治史:1355—1435年》(Early Ming China:A Political History,1355—1435,1982年斯坦福版)主要论题之一为:明初尚武精神源于元代的精神与制度,文治的再度确立则在1425—1450年间。其他有关明初的著作有:牟复礼(Frederict Mote)著《诗人高启,1336—1374年》(The Poet Kao Chin,1336—1374,1962年普林斯顿版),第一章;戴德著《1363年鄱阳湖之战:明朝建立时的内陆水战》(The Poyang Lake Campaign,1363:Inland Naval Warfare in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载柯尔曼(Frank-A.Kierman, Jr.):编《中国战法》(Chinese Ways in Warfare),哈佛东亚丛书第七四种(1974年麻省剑桥版),202-242页;陈少岳(David B.Chan)著《燕王篡位:1398—1402年》(The Usurpation of the Prince of Yen,1398—1402,1976年旧金山版)。并参看《明代名人传》中成祖(朱棣)与太祖(朱元璋)传:第一卷,355-365页,381-392页。
[15]此一双重特性并不适用于同样是世袭军权的土司。见贺凯:《明朝政府组织》(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载毕绍甫(John L.Bishop)编《中国历史上政府机构研究》(Studies of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in Chinese History,1968年麻省剑桥版),67、77-78,114-121页。
[16]王毓铨:《明代的军屯》(1965年北京版),第二部分。吴晗:《明代的军兵》,载《读史札记》(1956年北京版),92-141页。清水泰次:《明代军屯的瓦解》(《明代军屯の崩坏》),载《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1968年东京版),329-354页。黄仁宇:《明代的赋税与财政》,66-68页;及《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军事开支》,40-44页。
[17]佐伯富:《关于明清时代的民壮》(《明清時代の民壮について》),载《东洋史研究》,一五卷四期(1957年3月),33-64页。岩见宏:《明代的民壮与北边防卫》(《明代の民壮と北辺防衛》),载《东洋史研究》,一九卷二期(1960年10月),156-174页。孙金铭:《中国兵制史》(1960年台北版),173-176页。
[18]王贤德:《明末动乱时的乡村防卫》(《明末動乱期における郷村防衛》),载《明代史研究》,二卷(1975年),26-49页。
[19]黄仁宇:《明代的军事开支》,44-56、59-62页;及《明代财政》(Fisc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载贺凯编《明代中国政府研究七篇》(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1971年纽约版),112-123页。潘镇球:《明代北边军镇及卫所的崩溃》,载《崇基学报》,七卷一期(1966年11月),90-100页。
[20]《晚明民变》17-20、90-100页。《明末流寇始末》,11-21页。有关官军方面,参看《明末农民叛乱》,49-50页。南京城“流”民尤多,士兵纪律问题于是相应严重起来。见川胜守:《明末南京兵变——明末都市构造略述》(《明末南京兵士の叛乱—明末の都市構造についての一素描》),载《星博士退休纪念中国史论集》(1978年山形版),187-207页。
[21]罗香林:《狼兵狼田考》,载《广州学报》,一卷二期(1937年4月),无连续页码。
[22]吴晗:《明代的军兵》,126页,所引《明史》一八七卷洪钟传。
[23]谷光隆:《明代勋臣考察》(《明代の勳臣に関する一考察》),载《东洋史研究》,二九卷四期(1971年),68页。
[24]吴缉华:《明代最高军事机构的演变》,载《南洋大学学报》,六卷一期(1972年),149、152-154页。《明代勋臣考察》,92-103页。龙文彬:《明会要》,二册本(1956年北京版),第二册,745-746页。
[25]谷光隆:《明代勋臣考察》,106页。《明朝政府组织》,77-78页。
[26]见《明代名人传》中朱祈、朱祈钰、也先、王振各传:第一卷,289-298、416-420页;第二卷,1347-1349页。
[27]牟复礼:《1449年土木之变》(The Tu-mu Incident of 1449),载《中国战法》,267-272页。
[28]例如吴缉华(Wu Chi-hua):《明代中国北边防线的后退》(Contraction of Forward Defenses on the North China Frontier during the Ming Dynasty),载《远东史论丛》(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一七卷(1978年3月),1-13页。罗荣邦(Jung-pang Lo):《有关和战问题的筹划和决策》(Policy Formul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on Issues Respecting Peace and War),载《明代中国政府》,56-60、66-68页。黄仁宇:《1619年辽东之役》(The Liao-tung Campiagn of 1619),载《远东》,二八卷一期,30-54页。
[29]魏波渡(Bodo Weithoff):《中国第三条边界:传统中国国家与沿海地区》(Chinas dritte Grenze:Der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Staat und der küstennahe Seeraum,1969年威斯巴登版)。
[30]罗荣邦:《明初水师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载《远东》,五卷(1958年),158-162页。有关明初海上防御的详情,见川越泰博:《明代海防体制的运营构造——以创立期为中心》《明代海防体制の運営構造—創成期な中心に》,载《史学杂志》,八一卷六期(1972年),28-53页。
[31]《万历十五年》,第六章,尤见159页。苏均炜(Kwan-Wai So):《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倭寇》(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Sixteeth Century,1975年密歇根州东兰辛版),尤见135-140页。贺凯:《1556年胡宗宪击徐海之战》(Hu Tsung-hsien’s Campaign against Hsü Hai,1556),载《中国战法》,285-287页。玛丽琳·费兹帕屈克(Merrilyn Fitzpatrick):《中国东南的地方利益和反海盗管理》(Local Interests and the Anti-Pirate Adminstration in China’s South-east),载《清史问题》(Ch’ing-shih wen-T’i),四卷二期(1979年12月),1-33页。
[32]《中国战法》引言,7-11页。
[33]黄仁宇赞同此一解释,集中表现在《万历十五年》论戚继光一章,尤见157-158、175-176页。
[3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四部备要》本),《兵制三》,页28乙-29甲。
[35]艾森豪威尔是美国著名的军人总统。黑格是尼克松总统任命的国务卿,也是军人出身——译注
[36]牟复礼:《中国专制主义的成长:评以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魏特夫理论》(The Growth of Chinese Despotism:A Critique of Wittfogel’s Theory of Oriental Despotism as Applied to China),载《远东》,八卷(1961年),18-20、26-29页。
[37]有关君主与官僚体制的相互依赖,见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y),第二卷《君主制衰败问题》(The Problem of Mornarchical Decay)(1968年柏克莱版),第二部,第五章,尤见61-71页。
[38]笔者对晚明政治的了解得益于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有关当代中国政治的论著,尤其是《中共政治派系模式》(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五三卷(1973年1至3月),尤见46-51页。
[39]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1967年台北版),8-13页。有关内阁发展的简要概述,参看关文发《试论明朝内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45-65页。
[40]顾瑞伯(Robert Bruce Crawford):《明朝宦官权力》(Eunuch Power in the Ming Dynasty),载《通报》(T’oung Pao),四九卷三期(1961年),117、147页。
[41]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17-24、138-140页。吴缉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之祸》,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三一本(1960年),381-403页;及《论明代废相与相权之转移》,载《大陆杂志》,三四卷一期(1967年1月),6-8页。林懋(Tilemann Grimm):《明初至1506年的内阁》(Das Neiko der Ming-Zeit von den Anfangen bis 1506),载《远东》,一卷(1954年),139-177页。
[42]邓尔麟:《嘉定忠臣录:十七世纪中国儒家领导与社会变革》(The Chia-ting Loyalists:Confucian Leadership and Social Chang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1981年纽黑文版),88-89页。
[43]贺凯:《明朝政府组织》,88-89页。
[44]贺凯:《明末东林运动》,139页。黄宗羲亦看出相权问题,参看狄百瑞(W.T.de Bary):《中国专制主义与儒家理想:十七世纪的观点》(Chinese Despotism and the Confucian Ideal:A Seventeenth Century View),载《中国思想与制度》,175-176页。
[45]可参看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论申时行一节,42-74页。
[46]其中最著之例,参看苏均炜《对大学士严嵩(1480—1566?)的新评价》(Grand Secretary Yan Song[1480-1566?]:A New Appraisal),载《中国史与中美关系史论集》(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82年密歇根州东兰辛版),1-40页;关于张居正,参看《万历十五年》,第一、二章。并参《明代名人传》中张居正与严嵩传:第一卷53-61页,第二卷,1586-1591页。
[47]贺凯:《明末东林运动》,139-141页。卜恩礼(Heinrich Busch):《东林书院及其政治与哲学意义》(The Tunglin Academy and Its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cance),载《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一四卷(1949—1955年),14-21页。顾瑞伯:《儒化法家张居正》(Chang Chii-cheng’s Confucian Legalism),载《明代思想中的个人与社会》(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367-413页。
[48]艾维四(William S.Atwell):《从教育到政治:复社》(From Education to Politics The Fu She),载狄百瑞编《新儒家的展开》(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1975年纽约版),尤见339-341、349-35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46-98页。
[49]例如《明代思想中的个人与社会》一书中,顾瑞伯称张居正为“儒化法家”,黄仁宇称倪元璐为“现实主义的儒家”,367-449页。
[50]布目潮渢:《明朝的诸王政策及其影响》(《明朝の诸王政策とその影響》),载《史学杂志》,(一):五五卷三期(1944年3月),1-32页。(二):五五卷四期(1944年四月),50-87页。贺凯:《明朝政府组织》,66-67页。赵翼:《廿二史札记》,共二册(1965年台北版),下册,471-473页。最近有关明朝宗藩制度的总体研究,参看顾诚:《明代的宗室》,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89-111页。
[51]布目潮渢:《明朝的诸王政策》(三),载《史学杂志》,五五卷五期(1944年5月),尤见24、33-34、67-68页。吴缉华:《论明代宗藩人口》,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1970年台北版),第二集,237-289页。《明会要》,第二册,877页。《明史》,卷一百,页1甲-乙。有关潞王庄田的研究,见佐藤文俊:《明末就藩王府大土地所有的二三个问题——潞王府的情况》(《明末就藩王府の大土地所有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潞王府の場合》),(一):载《木村正雄先生退休纪念东洋史论集》(1976年东京版),325-357页;(二):载《明代史研究》,第三卷(1975年12月),23-41页。有关为清朝所没收明朝王庄的价值,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集(1979年北京版),149-255页。
[52]《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页20甲。
[53]《清世祖实录》,卷二十,页116;卷二五,页18乙-19甲;卷二六,页18乙。
[54]有关的开拓性研究,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北京版),68-153页(并参看傅氏《明末南方的“佃变”、“奴变”》)一文中最新发现,载《历史研究》,1975年五期[五月],61-67页;谢国桢:《明季奴变考》,载《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附录一(原刊于《清华学报》,八卷一期[1932年])。
[55]森正夫:《关于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明末社会関係における秩序の変動について》),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三十周年纪念论集》(1979年名古屋版),135-159页。
[56]有关某一重要地区的社会历史分析,见邓尔麟:《嘉定忠臣录》,71-103页
[57]有关北方某一地区的研究,见李成珪(I Songgyu)著、傅佛果(Joshua Fogel)译:《顺治时期的山东:地方控制的建立以及缙绅的反应》(Shan-tung in the Shun-chih Reign: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Control and the Gentry Resfponse),载《清史问题》,(一):四卷四期(1980年12月),17-18页;(二):四卷五期(1981年6月),9-10、15-16、22页。
[58]谈迁:《国榷》(1958年北京版),第六册,6035页。吴伟业:《绥寇纪略》(1968年台北重印),补遗中,页6乙。
[59]帕森斯:《明末农民叛乱》,38-41、58-60页。朱文长:《史可法传》(1974年台北版),第二章。
[60]祁彪佳:《甲乙日历》(1969年台北版),10、18、19页。《国榷》,第六册,6033-6034页。万言:《崇祯长编》(《痛史》本),卷二页23乙。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47-49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1608—1647)》(Ch’en Tzu-lung[1608—1647]:A Scholar-Offcial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博士论文(1974年普林斯顿印),127页。
[61]佚名:《淮城纪事》(《痛史》本),页1甲-2乙。计六奇:《明季南略》(1963年台北版),第一册,66-67、79页。
[62]《1644年的大顺政权》,50页。
[63]《淮城纪事》,页3甲。
[64]《明季南略》,第一册,115-118页。陈贞慧:《过江七事》(《痛史》本),页1甲。号召义兵事,冯梦龙亦有记载,参看其《甲申纪事》(1941年上海影印弘光本),卷七;以及史可法:《史忠正公集》(1968年台北版),卷四。
[65]陈贞慧:《书事七则》,载《陈定生遗书》(1654年版),页3甲。
[66]《国榷》,第六册,6071、6073页。崇祯帝已死的确讯于5月22日到达,参看《书事七则》,页3甲。黄玉斋撰有三篇文章概述弘光一朝历史:《弘光朝的建立》、《弘光朝的史略》、《弘光朝的崩溃》,分别载《台湾文献》,十八卷,一、三、四期(1967年3、9、12月),88-115页,92-118页,150-177页。杨云萍亦有一文论述弘光朝各种问题,颇可参考:《南明弘光时代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七卷(1975年5月),157-178页。
[67]因叛军攻击而逃离王庄、抵达淮河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其他主要藩王有:潞王(河南北部的卫辉)、鲁王(山东兖州)、周王(河南开封)、蕙王(湖北荆州),见《明史》,卷一百,页18甲;卷一〇一,页7甲-乙;卷一〇四,页32甲、34甲。逃离湖南王庄抵达广西的桂王也在考虑之列,但随后因相距太远而未被接受。
[68]《清代名人传》,第一卷,195-196页。参看本书第035页,注2。
[69]夏允彝、夏完淳:《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本,1971年台湾版),292-293页。
[70]崇祯帝生七子,四人夭折,自尽时存三人:太子朱慈烺,刚过十六岁;定王朱慈燦,约十二岁;永王朱慈焕,十岁。有关三人的名、字及相互关系,正史颇有混乱、谬误之处。欲知其详,请参看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载《明清史论著集刊》(1965年台北翻印本),28-70页。
[71]李清:《三垣笔记》(《古学汇刊》本,1964年翻印),附识下,页7甲-乙。在皇帝嗣子之后,潞王排行第五,而福王排行第一。
[72]《过江七事》,页1甲-2乙。《幸存录》,292页。谈迁:《枣林杂俎》(《笔记小说大观》本,1960年台湾翻印),仁集,页14甲;《国榷》,第六册,6077页。《明季南略》,第一册,47-48页。并参《清代名人传》刘泽清、马士英传,第一卷,531-532页、558-559页。
[73]《过江七事》,2乙-3甲。《明季南略》,第一册,48页。崇祯年间,刘孔昭曾在朝堂抱怨文臣对操江提督苛责太多,操江提督副都御史(和刘孔昭地位相当的文官)因此免职。见《枣林杂俎》,仁集,页8甲。弘光朝建立之初,两位有声望的南京文官被授协理操江右佥都御史之职,二人都怕得罪刘孔昭而拒绝此职。见《国榷》,第六册,6098页;《明季南略》,第一册,57页;《甲乙日历》,29页。
[74]《国榷》,第六册,6081页。《过江七事》,页3甲。《甲乙日历》,25页。佚名:《龙飞纪略》,载周昔雍纂《兴朝治略》,卷一,页1乙。
[75]《国榷》,第六册,6081页。《甲乙日历》,29页。《龙飞纪略》,页2乙。
[76]《甲乙日历》,26页。《龙飞纪略》,页2甲。《明季南略》,第一册,49页。
[77]按明代惯例,若皇帝因巡狩或亲征,决定离开京城相当时日,监国之称即授予太子,以为“摄政”。(参《大明会典》[1963年台湾重印本],卷五四,页1甲-13乙。)但是在有关福王问题上,文官们是援引景泰帝之例。1449年,正统帝为瓦剌部所俘,其同父异母之弟(即后之景泰帝)监国(参看本书第040页,注3、4)。有关福王事,见顾炎武《圣安本纪》(1964年台北版),第一册,2页;《国榷》,第六册,6083页。
[78]《明季南略》,第一册,49-50页。《甲乙日历》,28、30页。
[79]见《明会典》,第二册,901-904页。
[80]《明季南略》,第一册,56页。《甲乙日历》,28-29页《龙飞纪略》,页4甲。《枣林杂俎》,仁集,页8乙。《三垣笔记》,卷下,页22甲。刘孔昭举出一例,证明勋臣亦可入阁,表明他不清楚丞相和大学士之别。丞相为明太祖所废,后来才设置大学士以代替丞相(参看本书第044页,注3,及第045页,注2)。
[81]《明季南略》,第一册,49-50页。《甲乙日历》,25、27页。《龙飞纪略》,页3甲、乙。福王正式即监国位是在次日(六月七日)。见《国榷》,第六册,6083页;《龙飞纪略》,页3乙;《甲乙日历》,28页。
[82]《国榷》,第六册,6099-6100页。《圣安本纪》,第一册,4页。
[83]最详备的诏书内容见周昔雍纂《兴朝治略》,卷一,页1甲-17甲。
[84]《国榷》,第六册,6083、6088、6091、6097-6099页。《龙飞纪略》,页4甲。《明季南略》,第一册,3、57页。《圣安本纪》,第一册,2-3页。
[85]《明季南略》,第一册,56-57页。《圣安本纪》,第一册,3页。《国榷》,第六册,6092页。《淮城纪事》,页8甲。
[86]应廷吉《青燐屑》(《明季稗史汇编》本),卷上,页4甲。史可法《公恳留在朝疏》,载《史忠正公集》,附录,64-65页。
[87]《圣安本纪》,第一册,3页。《明季南略》,第一册,58页。《甲乙日历》,29页,《史忠正公集》,32-33页。
[88]有关史可法的著作很多,称引最多的年谱是杨德恩所撰《史可法年谱》(1940年长沙版),最著名的传记是上述朱文长之作。刘约瑟(音译)(Joseph Liu)撰有博士论文《史可法(1601—1645)与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She Ke-fa[l60l—1645]et la contexte Politique et Social de la Chine au moment de I’invasion mandchoue)(1969年,巴黎),藏索邦(Sorbonne)图书馆。有关内地对史可法生平所作解释,见魏宏运《史可法》(1955年上海版);中国大陆史学家关于史可法的争论,见刘辉等编《史可法评价问题汇编》(1968年香港版)。
[89]顾瑞伯撰有《阮大铖传》(The Biography of Juan Ta-Ch’-eng),载《中国文化》(Chinese Culture),六卷二期(1965年3月),36-48页。文中译出《明史》卷三〇八《马士英传》,加以注释,并附有一表,列出多种其他传记资料。
[90]关于马士英在徽州府纵容士卒所引致的不满,见金声《金太史集》,卷五,载《乾坤正气集》(1966年台北翻印本),卷四六一。
[91]《过江七事》,页12甲。
[92]《过江七事》,页10乙。《明季南略》,第一册,64-65页。《国榷》,第六册,6155页。《青燐屑》,卷上,页8甲;卷下,页4甲-乙。夏完淳《续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本),327页。
[93]《过江七事》,页11乙。
[94]上书,页11甲。《三垣笔记》,卷下,页3甲-乙。
[95]《过江七事》,页12甲。
[96]《国榷》,第六册,6090-6091页。《史忠正公集》,2-3页。
[97]《国榷》,第六册,6096页。《明季南略》,第一册,60页。《兴朝治略》,卷二,页6甲-9乙。《史忠正公集》,3-4页。史可法后来对于以这样的方式设立四镇可能感到后悔,但在当时,他完全支持这一计划。见《青燐屑》卷上,页15甲;及《过江七事》,页12甲-乙。各镇驻地并不固定,但是至少,应暂驻上述各城,或是其附近。
[98]《明季南略》,第一册,66页。
[99]《过江七事》,页10乙。
[100]淮安巡抚路振飞是一位能臣,在其辖区内有效地制止了流寇以及马士英、刘泽清部下骄兵悍卒的骚扰,但在马士英任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和刘泽清任淮安地区总兵官之后,即遭免职。见《国榷》第六册,6110页;及《淮城纪事》全书各处。后任湖广总督的巡抚何腾蛟以及九江总督袁继咸,与武昌的左良玉关系还不错,主要是靠二人的人格影响,不是靠体制。最后,二人不能阻止左良玉后果严重的兵变,险遭不测。何腾蛟事,见《清代名人传》,第一卷,290-291页;《国榷》第六册,6142、6167页;《三垣笔记》,附识下,弘光部分,页1甲-2乙。袁继咸事,见《清代名人传》第二卷,948-949页;《三垣笔记》卷下,页1乙-3乙、34甲-36乙;亦见袁继咸《浔阳纪事》(胡思敬《豫章丛书》本),全书各处。苏州巡抚祁彪佳所关注的,主要是下列各事:如何阻止高杰和刘泽清在镇江渡江南下;如何应付高、刘二人及史可法所派出的部下,这些人强征钱粮,供江北之用,扰乱了苏州民心;如何化解史可法的几支部队与镇江民众的隔阂,以及如何消弭这些部队与调来的浙军之间的冲突。见《清代名人传》,第一卷,126页;《甲乙日历》,全书各处。
[101]高杰事,见《清代名人传》第一卷,410-411页;《明季南略》,第一册,66-67页。
[102]佚名:《扬州变略》(《痛史》本),页1甲、2甲-3甲,《清燐屑》,卷上,页4乙。这位被害的调人是复社成员郑元勋。有关此人事,见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明清史料汇编》影印本),卷四,页21甲-乙。
[103]《过江七事》,页10乙。
[104]《青燐屑》,卷上,页5甲-乙。《续幸存录》,322、325页。《扬州变略》,页3乙。
[105]《青燐屑》,卷上,页5。《扬州变略》,页3乙。史可法有关此类事件的上疏,见《史忠正公集》,5-6页。
[106]最著之例是李成栋、金声桓、张天禄,留待第二、第五两章叙述。
[107]《青燐屑》,卷下,页1甲、2甲-3乙。《圣安本纪》,第一册,21-23页。陆圻:《纤言》(《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本),46页。《明季南略》,第一册,68、200页。《国榷》,第六册,6180、6183、6184-6186页。
[108]刘宗周:《刘子全书》(《中华文史丛书》影印道光本),卷一八,页3甲-5甲、8乙-11甲、13甲-16乙。姚名达:《刘蕺山先生年谱》(1937年上海版),320页。《圣安本纪》第一册,7页。刘宗周传略,见《清代名人传》,第一卷,532-533页。刘宗周官至都御史,又为“清流”耆宿,因此他的批评最为震撼。不过,上这类奏疏的,绝不止他一人。陈函辉和贺世寿的同类奏疏,见《甲申纪事》,卷七;《国榷》,第六册,6107页;《明季南略》,第一册,5、118-119页。
[109]《明季南略》,第一册,88-92页。《过江七事》,页14甲-15甲。关于这位好惹事的御史黄澍,《枣林杂俎》的传略多有贬辞,见该书仁集,页10甲-乙。
[110]笔者同意夏完淳对此所作的解释,见《续幸存录》,322页。马士英原先并不想和东林起衅,而是为刘宗周及其同气类的人所逼迫而出此。有关证据,见《甲乙日历》,73页。
[111]《国榷》,第六册,6129、6131页。《明季南略》,第一册,9页。
[112]《国榷》,第六册,6105页。《枣林杂俎》,仁集,页8甲-乙。《圣安本纪》,第一册,5页。《明季南略》,第一册,74-75页。
[113]《国榷》,第六册,6107、6113页。《圣安本纪》,第一册,6页。《明季南略》,第一册,76-77页。
[114]《过江七事》,页5甲-6甲。
[115]上书,页10乙。
[116]《国榷》,第六册,6131-6132页。《明季南略》,第一册,73-74页。《圣安本纪》,第一册,11页。
[117]《圣安本纪》,第一册,9页。史可法要求皇帝采取行动消弭此一争执事,见《史忠正公集》,4-5页。
[118]《刘子全书》,卷一八,页16乙-17乙。
[119]关于左良玉,见《清代名人传》,第二卷,761-762页。关于东林活跃人物侯恂及其子复社名士侯方域,见同书,第一卷,291-292页。并参看侯方域《壮悔堂集》(1968年台北版)卷首有关诸传。关于历史名剧《桃花扇》中人物侯方域与左良玉,见江香《桃花扇名人小史》(1970年香港版),1-7页,13-24页。迟至1644年9月,左良玉才被任命为第五镇总兵官。见《国榷》第六册,6136页;《圣安本纪》第一册,10页。
[120]《国榷》,第六册,6138、6140、6146页。《明季南略》,第一册,93-95页。《圣安本纪》,第一册,11页。《三垣笔记》,页7乙。
[121]阮大铖当时也以剧作家著称于世。见《清代名人传》,第一卷,398-399页;顾瑞伯:《阮大铖传》;钱秉镫:《阮大铖本末小纪》,载《所知录》(1970年台北影印本),(四)。
[122]有关此一公揭的讨论,见艾维四《从教育到政治:复社》,353-355页。公揭签署者姓氏,载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卷十,在《贵池先哲遗书》(1920年出版)内。有关其中一人的事略,见陈贞慧《书事七则》,页4甲-7乙。并参吴应箕为此举所作的辩白,见《楼山堂集》(1935年上海版),卷一五,176-177页。
[123]《阮大铖本末小纪》,页4甲-乙。
[124]《国榷》,第六册,6113-6114、6116-6118、6121页。《明季南略》,第一册,6、67、85-88页。
[125]《国榷》,第六册,6133、6141、6143页。《明季南略》,第一册,12、88、99-100页。《圣安本纪》,第一册,9、11页。多数记载径直以为,此一“内批”乃马士英所使。钱秉镫却说,这是阮大铖本人所为,马士英也感意外。(《阮大铖本末小纪》,页4甲)。
[126]贺凯,《明代监察制度》(The Censorial System of Ming China)(1966年斯坦福版),209-210页。
[127]《刘蕺山先生年谱》,324-325页。《国榷》,第六册,6144、6146、6154页。《明季南略》第一册,144页。《圣安本纪》,第一册,12-14页。
[128]例如,被指为对福王之立怀有“异志”的朝臣中,吕大器即是一位。他因而在7月20日辞去礼部左侍郎之职。见《国榷》第六册,6120页;《圣安本纪》第一册,7页。吏部尚书徐石麒亦受到马党御史的弹劾,于10月30日去职。见《国榷》第六册,6152-6153、6161页;《枣林杂俎》,仁集,页15乙-17乙;《三垣笔记》,卷下,页9甲、乙。有一位“马阮”党的御史张孙振攻击多名“清流”人物,其中包括得力的苏州巡抚祁彪佳,散布对他人品清白和正直的怀疑。祁彪佳因而于11月获准去职。但是有意思的是,祁彪佳接到马士英慰留他的私函,见《明季南略》,第一册,18-19页;《甲乙日历》,71、74-76页。长期受冤的刑部尚书解学龙最终屈从于纵逆的指控,于1645年2月被免职。见《国榷》,第六册,6178-6180页;《明季南略》,第一册,30页。礼部尚书顾锡畴拖到3月也辞职。他曾试图揭发一位马党官员的贪黩,因而受到报复,在3月被纠弹。见《国榷》,第六册,6146、6148、6185页;《三垣笔记》,卷下,页8甲。党争中最受鄙视的变节者是盛名文士钱谦益。见《清代名人传》,第一卷,48-51页;《三垣笔记》,附识下,弘光部分,页4甲;《续幸存录》,323页;《国榷》,第六册,6140、6154页。
[129]《国榷》,第六册,6114、6130-6131、6166、6171页。《兴朝治略》,卷二,页16甲-17乙。《圣安本纪》,第一册,8-9、10、13、16、28页。这次得到追赠的人物分为四类(页码据《明代名人传》):(1)为明太祖不当地处死或赐令自尽者,如傅友德(第一卷,466-470页)、冯胜(第一卷,433-455页)、廖永忠(第一卷,909-910页)、耿炳文(第一卷,713-718页);(2)建文帝朱允炆(第一卷,397、404页)及其父朱标(第一卷,346-348页),以及忠于建文而死者,如方孝孺(第一卷,426-433页);(3)景泰帝朱祁钰(第一卷,294-297页)及其大臣于谦(第二卷,1608-1611页);(4)反抗魏忠贤者,或在其淫威下被处死,或后死而未经表彰者,如李应昇(第一卷,708页)、文震孟与姚希孟(第二卷,1467-1470页)、吕维褀(第一卷,1014-1017页)。当时有人相信,明末的灾祸为建文帝及其忠臣的冤魂所致,见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1948年上海版),38-41页。
[130]《国榷》,第六册,6125-6126、6128页。《明季南略》,第一册,6、9、37页。《圣安本纪》,第一册,8、16、22、24、26页。
[131]《甲申纪事》中所载各公揭最能表明此种情绪,见该书卷七、八。并参《明季南略》;第一册,3页;《圣安本纪》,第一册,4页。
[132]《国榷》,第六册,6103、6151-6152页。《明季南略》,第一册,16页。《圣安本纪》,第一册,4页。《史忠正公集》,11页。
[133]朝廷仿照唐代在安史乱后以“六等法”定罪的例证。见《国榷》,第六册,6128、6136、6170、6175页;《明季南略》,第一册,9、29、124、129页;《圣安本纪》,第一册,12-13、18页。并参看《廿二史札记》,756-759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四部丛刊》本),卷二二〇,页7乙-12甲。
[134]《续幸存录》,328页。《明季南略》,第一册,126页。有关起用变节官员事,见《国榷》第六册,6154、6156页;《明季南略》,第一册,17、128页;《圣安本纪》,第一册,14、18页。处置最不公的恶例,是对1638年反阮大铖公揭签署者中著名人物,尤其是对周镳的迫害。见《明季南略》,第一册,6、11、18、19、41、126、130页;《国榷》,第六册,6116、6140、6156、6212页;《枣林杂俎》,仁集,页13乙-14甲;《三垣笔记》,卷下,页3乙、19乙、42乙-43甲;古藏室史臣:《弘光实录钞》(《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本),201、255、257-258页。有关吴应箕、陈贞慧、方以智、侯方域四公子事,见《清代名人传》,第一卷,52-53、82-83、232-233、291-292页;《国榷》,第六册,6142页;《弘光实录钞》,258页。有关弘光朝因党争而起的迫害,尤其是周镳事的一般论述,见赵令扬《论南明弘光朝之党祸》,载《联合书院学报》,四卷(1965年,单独标页码)。
[135]《过江七事》,页18甲。《续幸存录》,326页。《阮大铖本末小纪》,页4甲-乙。《国榷》,第六册,6177页。
[136]《幸存录》,309-310页;《续幸存录》,326页。《三垣笔记》,卷下,页13甲-乙、18乙-20甲、23乙。《明季南略》,第二册,173-176页。《枣林杂俎》,仁集,页17乙-18甲。《纤言》,45页。《国榷》,第六册,6195页。
[137]《国榷》,第六册,6168、6179页。《圣安本纪》,第一册,17页。当其他人反对此举时,弘光帝为整个事件所激怒,表露了他对政治一窍不通。他回答说,这只是他的家事,与负责的官员无关。见《圣安本纪》,第一册,23页;《明季南略》,第二册,175页。杨维垣及其同伙亦要求皇帝对已死的逆案中人正式抚恤,对其他入逆案者则予昭雪。见《国榷》,第六册,6170、6182页;《明季南略》,第一册,34页;第二册,174-175页。
[138]《幸存录》,309页。
[139]永乐帝朱棣朝是此一模式的例外。永乐篡位,颇得力于宦官,此后便尽量使用宦官。见顾瑞伯《明朝宦官权力》,126-129页。
[140]《阮大铖本末小纪》,页4甲。
[141]《国榷》,第六册,6126、6179页。《枣林杂俎》,仁集,页9甲-乙。《幸存录》,309页。《明季南略》,第一册,29页。
[142]《国榷》,第六册,6136、6140、6145页。《甲乙日历》,42页。《明季南略》,第一册,104页。《刘蕺山先生年谱》,323页。贺凯《明代监察制度》,44页。顾瑞伯《明朝宦官权力》,131-133页。祁彪佳《祁彪佳集》(1960年上海版),21-22页。
[143]《国榷》,第六册,6106、6110-6111、6150页。直至1645年一月底或二月初,马士英才被正式任命为大学士。见《圣安本纪》,第一册,21页;《明季南略》,第一册,27页。
[144]《三垣笔记》,卷下,页44乙。
[145]《兴朝治略》,卷二,页1甲-3甲。《国榷》,第六册,6103页。
[146]《过江七事》,页8甲-9乙、14甲。《三垣笔记》,卷下,页11甲。《圣安本纪》,第一册,6页。《国榷》,第六册,6139页。
[147]《国榷》,第六册,6154页。
[148]《纤言》,23页。
[149]《国榷》,第六册,6171、6175页。《明季南略》,第一册,149页。
[150]《国榷》,第六册,6141、6155、6157、6203页。《明季南略》,第一册,12、42页;第二册,172-173页。《圣安本纪》,第一册,11、14页。
[151]《三垣笔记》,卷下,页15甲。《国榷》,第六册,6138-6139、6149、6162页。《明季南略》,第二册,153、172页。
[152]《国榷》,第六册,6166页。《明季南略》,第一册,148页。
[153]钱秉镫:《南渡三疑案》,载《所知录》,(三),页1甲-乙、3甲-6乙。《明季南略》,第一册,24、26页。《续幸存录》,323页。《国榷》,第六册,6168、6191页。《圣安本纪》,第一册,13、18页。此案过后不久,有一名南京皮匠狂呼自己是皇帝之父,企图进入皇宫,但是立刻被殴致死。见《续幸存录》,327-328页;《明季南略》,第一册,40页。
[154]《国榷》,第六册,6120、6144、6171页。《明季南略》,第一册,8页;第二册,166页。
[155]《国榷》,第六册,6190-6194、6196、6198、6200-6201页。《明季南略》,第一册,37、39页;第二册,153-157、159-161页。《圣安本纪》,第一册,24-25页。《南渡三疑案》,页5甲-6乙。《三垣笔记》,卷下,页17甲、27甲-29乙、34甲-乙。《青燐屑》,卷下,页7乙-8甲。《纤言》,34-38页。林时对:《荷牐丛谈》,卷下,页7乙-8甲。
[156]《清世祖实录》,卷一二,页14甲-15乙。《明清实录》,甲,卷一,页96甲。钱:《甲申传信录》(《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本),149-153页。《明烈皇殉国后记》,29-43页。清朝地界的民众普遍相信“北太子”为真,导致不安。见《国榷》,第六册,6202-6203页;《甲申传信录》,153-154页。
[157]《国榷》,第六册,6195-6196页。《明季南略》,第二册,167-170页。《圣安本纪》,第一册,24页。《南渡三疑案》,页1乙-9乙。《三垣笔记》,卷下,页30甲-乙。《青燐屑》,卷下,页7乙。《纤言》,24-25页。林时对甚至把自称福王者的真实身份也列为“南都三疑案”之一,见《荷牐丛谈》,126-129页。
[158]有关南京如何成为明初首都事,见牟复礼《南京的转变,1350—1400年》,载史坚雅(G.Wm.Skinner)编《帝制中国后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7年斯坦福版),101-153页。有关南京降为陪都事,见范德(Edward Farmer)《明初政府:两京的演变》(Early Ming Government: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1976年麻省剑桥版)。关于有明一朝设置官员的方式,见黄开华《明史论集》(1972年香港版),第一、二章。就明朝而言,南京主要是一个军事基地,防卫富庶的江南地区,并维持其治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省份——南直隶——的首府,北京地区的衣食,正是依靠南直隶的生产或转输。因此,到了明朝后期,南京最重要的官员为南京户部尚书以及负责卫戍三要员:兵部尚书(常兼)参赞机务、守备、操江提督。见《明会要》,第一册,541、566-567页;第二册,1230-1231页。
[159]《国榷》,第六册,6090-6091、6095、6102、6110、6129、6140、6175页。《明季南略》,第一册,5、19、29页。《三垣笔记》,卷下,页14乙-15甲。《兴朝治略》,卷二,页13甲-15甲。
[160]《刘子全书》,卷一八,页3甲-5甲。《弘光实录钞》,185页。
[161]《过江七事》,页1甲。《史忠正公集》,3-4页。《兴朝治略》,卷二页6甲。《国榷》,第六册,6094-6095页。
[162]《国榷》,第六册,6142页。《明季南略》,第一册,73页。
[163]《国榷》,第六册,6110、6134页。《明季南略》,第一册,6页;第二册,213、216页。《兴朝治略》,卷二,页4甲。陈邦彦:《陈岩野先生全集》(1805年版),卷一,页29乙-30甲。
[164]《淮城纪事》,页1甲-乙、3乙、4乙-3甲、7乙-8甲。阎尔梅:《阎古古全集》(1911年版),卷一,页8甲。《国榷》,第六册,6106、6111页。《明季南略》,第一册,115-126页。《圣安本纪》,第一册,5页。
[165]5月和6月所得到的消息,似乎只是关于吴三桂的胜利。见《甲乙日历》,20、34页;《淮城纪事》,页9甲;《国榷》,第六册,6017、6106页;《明季南略》,第一册,4页。7月9日,南京得知满洲人对南方的晓谕;7月18日,公布此晓谕。见《国榷》,第六册,6120页;《明季南略》,第二册,213-214页。
[166]《陈岩野先生全集》卷一,页29甲-30乙。
[167]《国榷》,第六册,6086、6105、6107-6108、6120、6122、6147页。《明季南略》,第一册,9、123、133页。
[168]《国榷》,第六册,6127-6128页。《明季南略》,第一册,8页;第二册,214-215页。《圣安本纪》,第一册,7-9页。
[169]《国榷》,第六册,6127、6131-6132页。《明季南略》,第二册,216页。《甲乙日历》,54页。《史忠正公集》,6-7页。
[170]《三垣笔记》,卷下,页5乙、16甲-乙。钱:《使臣碧血》,载《甲申传信录》,卷十。《枣林杂俎》仁集,页13甲。《复社姓氏传略》,卷十,页3乙-4甲。
[171]《国榷》,第六册,6130页。《明季南略》,第二册,215页。1642年,崇祯朝兵部尚书陈新甲因议款而被诛。马绍愉曾在他手下服务。见《廿二史札记》,739-740页;罗荣邦:《有关和战问题的筹划与决策》,68-69页。
[172]《国榷》,第六册,6111、6114页。《清世祖实录》,卷五,页17甲、23乙。
[173]陈洪范:《北使纪略》(《荆驼逸史》本),全书各处。李光涛辑注:《明清档案存真选集》(1959年台北版),第一册,125-127页。《明季南略》,第二册,219、221页。《清世祖实录》,卷八,页17甲;卷一一,页3乙。《甲申传信录》,156-158页。多位论者以为,清军大举南下,是基于陈洪范透露的消息。第一手资料显示,清朝在和陈洪范接触之前已有其他人通报消息。不过,事实看来是,陈洪范对清朝最后决定大举南下起了作用。这一决定正是在明朝使节逗留北京期间作出的。见《明清档案存真选集》,第一册,115-116页;《清世祖实录》,卷十,页10甲-乙、12甲-乙;卷一一,页21甲-乙。
[174]《国榷》,第六册,6161页。《明季南略》,第一册,21、23页;第二册,217-218页。《圣安本纪》,第一册,15-16页。《青燐屑》,卷上,页14乙。
[175]《史忠正公集》,11-13页。《明季南略》,第一册,218页。《青燐屑》,卷上,页15乙。
[176]《国榷》,第六册,6169页。《明季南略》,第二册,220页。
[177]邓尔麟:《许都与南京的教训:政治统一和江南的地方防御》,载《从明到清》,118-122页。《明季南略》,第一册,145-146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114-121、126页。
[178]《国榷》,第六册,6140页。《甲乙日历》,32页。《刘蕺山先生年谱》,319页。有关组织义军事在南直隶南部所引起的恐惧,见《甲乙日历》,56-57页。
[179]《国榷》,第六册,6142、6144页。《明季南略》,第一册,145页,《甲乙日历》,54、59页。《弘光实录钞》,221页。
[180]佚名:《京口变略》(《痛史》本),全书各处。《甲乙日历》,32、45、47、56、63、66、69页。《国榷》,第六册,6091、6125页。《圣安本纪》,第一册,8页。
[181]《甲乙日历》,32、47页。《弘光实录钞》,198页。
[182]祁彪佳去职后,镇江事务由阮大铖本人及马士英妹夫、名画家杨文监管。见《清代名人传》,第二卷,895-896页;《甲乙日历》,72页。
[183]《明季南略》,第一册,3页。《甲乙日历》,33、37页。《祁彪佳集》,18-19页。《甲申纪事》,卷八。
[184]《国榷》,第六册,6152、6196、6165、6180-6181、6183、6185、6203页。《明季南略》,第一册,15、21、24、29、32、34、36页。
[185]《国榷》,第六册,6130、6132、6143页。《明季南略》,第一册,11、24页。《兴朝治略》,卷二,页11甲-12乙。《史忠正公集》,9-11页。
[186]《国榷》,第六册,6150页。并参看《三垣笔记》,卷下,页20乙。
[187]《三垣笔记》,卷下,页13甲-乙、19乙-20甲、23乙。《国榷》,第六册,6150页。《明季南略》,第一册,20页。《圣安本纪》,第一册,16页。
[188]《崇祯长编》,卷二,页3甲。《国榷》,第六册,6102页。
[189]安野省三:《“湖广熟,天下足”考》(《“湖広熟すれば天下足”考》),载《木村正雄先生退官纪念东洋史论集》(1976东京版),301-309页。重田德:《清代湖南米市场考察》(《清朝にわける湖南米市场の—考察》),载《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1975年东京版),尤见10-13页。伊懋可(Mark Elvin):《市镇与水道:1480至1910年的上海县(Market Towns and Waterways:The County of Shanghai from 1480 to 1910),载《帝制中国后期的城市》,441-473页。
[190]《崇祯长编》,卷二,页13甲-乙。《国榷》,第六册,6138页。《甲乙日历》,48、52-53、62-63、66-67页。当时曾试图从广东、福建输入粮食,略有成功。见《过江七事》,页1甲;《国榷》,第六册,6120、6150页。罗友枝(Evelyn Rawski)指出,尤其在1643—1644年间,湖广十二府中,有十府的衙门为各种军队所毁;到了18世纪,在清朝移民垦荒以充实人口严重减少地区的计划之下,该省农业生产才恢复到16世纪的水平(《华南农业变化与农民经济》[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ra,1972年麻省剑桥版],101-102页)。关于南京作为北都的供应中心,见吴缉华:《明成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转运的建立》,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第一卷,155-173页。
[191]黄仁宇:《明代的赋税与财政》,98-104页。邓尔麟:《财政改革与地方控制:官绅联盟经历满洲人的征服继续存在》(Fiscal Reform and Local Control:The Gentry-Bureaucratic Alliance Survives the Conquest)载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卡罗琳·格兰特(Carolyn Grant)合编:《帝制中国后期的冲突与控制》(Conf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5年柏克莱版),86-120页。吴缉华:《论明代税粮重心之地域及其重税之由来》,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第一卷,33-73页。
[192]《甲乙日历》,39、60、69-70、76、79页。《祁彪佳集》,18-19页。《圣安本纪》,第一册,16页。《明季南略》,第一册,4页。
[193]《国榷》,第六册,6096、6147页。《三垣笔记》,页13乙-14甲。
[194]7800余两用于膳食、餐具及厨役服装。见《明季南略》,第二册,153页。大婚耗费2万两,皇帝的镶珠朝冠价值高达3万两。见《三垣笔记》,卷下,页15乙。有关军队人数太多、粮饷缺乏的怨言,见《国榷》,第六册,6142、6151、6161、6163-6164页;《明季南略》,第一册,21、28-29、34页;《青燐屑》,卷下,页1甲。
[195]《国榷》,第六册,6148、6165、6167、6183、6187、6199、6204页。《明季南略》,第一册,15、24页。《圣安本纪》,第一册,13页。明代诸如此类的杂税,见黄仁宇:《明代的赋税与财政》,第六章;及《倪元璐:新儒家学者政治家的“现实主义”》(Ni Yüan-lu:“Realism”in a Neo-Confucian Scholar-Statesman),423页。有关弘光及南明其他各朝铸钱事,见杨云萍:《记新得南明钱币》,载《钱币天地》,二卷,一期(1962年1月),3-7页;石睢:《南明钱录》,载《台湾风物》,一一卷,四期(1962年),46-47页。
[196]《国榷》,第六册,6120、6126、6141、6143、6148、6164、6180、6183页。《明季南略》,第一册,13、17页。有关“金花银”的起源与含义,见黄仁宇:《明代的赋税与财政》,52-53页。
[197]《国榷》,第六册,6099-6100、6106、6136页。《圣安本纪》,第一册,2、4页,宣布监国和宣布登极时的赋税项目可资比较(《兴朝治略》,页1甲、14甲)。有关“辽饷”、“剿饷”、“练饷”诸分外科敛,见《明代的军兵》,138-141页;《晚明民变》,20-24页;《明会要》,第二册,1033-1034页。
[198]《青燐屑》,卷下,页17甲。崇祯朝兵部尚书亦主张带兵官在其各自辖区自行征收。见《倪元璐》,423页。
[199]《国榷》,第六册,6200-6202、6204页。《明季南略》,第一册,40-41页;第二册,160-162、192-197页。《圣安本纪》,第一册,26-27页。《三垣笔记》,卷下,页34乙-36甲、37乙-38乙;附录下弘光部分,页1甲-2乙。《浔阳纪事》,页11乙、13甲-14甲。
[200]《国榷》,第六册,6200页。《明季南略》,第一册,41页;第二册,197-198页。《青燐肩》,页10甲-11乙。《荷牐丛谈》,124-126页。
[201]李光涛:《清人与流贼》,载《明清史论集》,第二集,349-350页(并参看同一作者《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196-197页)。
[202]陆西华:《满洲与中国关系》,7-10页。
[203]《清世祖实录》,四卷,页5甲-7甲、8乙、11乙。
[204]上书同卷,页13甲-19乙。参看本书引言,第033页,注3。
[205]《明季南略》,第三册,469页。魏斐德:《大顺政权》,4页。此处日期则从《清世祖实录》,卷五,页1乙-2甲。并参看《清代名人传》,第一卷,顺治帝(福临)传,255-259页。有关满洲人轻易进入北京事,见《明清史料》,甲集,第一册,页65甲。
[206]《明季南略》所录上谕略有不同,见第一册,13-14页(日期为六月五日);并参看《国榷》,第六册,6087页(日期为六月九日)。《清世祖实录》则未载日期。
[207]《清世祖实录》,卷五,页2乙、4甲-乙、10甲-乙。李成珪:《顺治时期的山东》,(二),7页。所有人民皆须剃发以示归顺的政策,最终在南北方都实行。有关该项政策,见中山八郎:《汉地的辫发问题——清初辫发令的实行中心》(《漢土に於ける辮髪の問題—清初の辮髪令施行を中心として》),载《中国史研究》,五卷(1968年),1-24页。
[208]陆西华:《满洲与中国关系》,28-30页。
[209]房兆楹以为(见《早期满洲军队人力的估计方法》[A Technique for Estimating the Numerical Strength of the Early Manchu Military Forces],载《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一三卷,一二期[1950年六月],195-215页),1644年,满洲的牛录数是278,蒙古是120,汉军是563。每一牛录人数约为300。《清世祖实录》(卷四页9甲-乙)说,初次侵入华北时,使用了三分之二的满洲、蒙古兵以及全部汉军。这表明,兵力大约为248500人。今人对吴三桂军力的估计是,在与李自成作战前,在2万到5万之间(见陈生玺:《清兵入关》,738页;奚孙凝芝:《重新评价吴三桂》,448、450页)。
[210]《三垣笔记》,卷下,页14甲。
[211]帕森斯:《明末农民叛乱》,186-188页。
[212]《国榷》,第六册,6118-6119页。
[213]《清世祖实录》,卷五,页15乙-16甲、19乙;卷七,页12乙-13甲。
[214]顾诚持相同看法,见其所著《论清初社会矛盾》一文,载《清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二期(1980年),141-142页。
[215]赖家度、李光璧:《山东榆园起义军抗清史迹初探》,载《中国农民起义论文集》(1958年北京版),288-294页。谢国桢:《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1956年上海版),74-86页。李成珪:《顺治时期的山东》(一),14-15页。《明清史料》,甲集,第一册,页69甲、74甲-乙。《国榷》第六册,6143页。
[216]《清世祖实录》,卷五,页26甲;卷六,页7甲;卷八,页14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页86甲-乙。《明清档案存真选集》,第一册,118-119页。《明季南略》,第二册,214、216、217页。《国榷》,第六册,6127、6147、6155页。《北使纪略》,页1甲。
[217]《清世祖实录》,卷六,页2乙-3甲;卷八,页7甲-乙,8乙-9甲;卷十,页12乙-13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页77甲-乙,80甲、85甲-乙,87甲、91甲。《明清档案存真选集》,第一册,123-121页。
[218]《清世祖实录》,卷五,页17甲-乙,23乙;卷一一,页4甲,21甲-乙。《明清档案存真选集》,第二册,117页、32页注。凌事难以捉摸,他常常看来确实在为清朝出力,最后却为明朝殉节。见《国榷》,第六册,6139、6141、6163、6167、6198页;《明季南略》,第一册,2、23、28页;第二册,214-216、223-226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页81甲-乙;《明清档案存真选集》,第一册,124页,34页注。
[219]《明清档案存真选集》,第一册,122、129-130页,135页注。《北使纪略》,页2甲-乙,4甲。另一原因是:使节抵达北京附近时,“小汗”(即顺治帝)亦刚到北京入居皇宫,因而加强了治安措施。见《北使纪略》,页2甲。《清世祖实录》,卷七,页24甲;卷八,页14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页93甲。
[220]《清世祖实录》,卷六,页16乙-19乙。当时满洲首领的此类信件当然是与之合作的汉族文士所为。
[221]《史忠正公集》,23-25页。《明季南略》第二册,209页。并参看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多尔衮、史可法的通信》(Ein Briefwechsel Zwischen Durgan und Schi Ko-Fa),载《中国》(Sinica),八卷五——六期(1933年),239-245页。史可法此覆书为其幕宾黄日芳代拟,措辞更为强硬。据说史可法本人曾加修改,使语气稍婉转。因此,黄日芳将此代拟件分别印行。见《枣林杂俎》,仁集,页18乙。康熙间学者温睿临在其南明史著作《南疆逸史》中所采用的显然是草拟件。见该书(1960年上海版),38-39页。
[222]《明清档案存真选集》,第一册,115-116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215页。
[223]《北使纪略》,页1甲-2甲。《清世祖实录》,卷八,页17甲。
[224]《清世祖实录》,卷十,页12甲-乙。并参看《清代名人传》多铎传,第一卷,215页。
[225]欲知此阶段详情,可参看《明季流寇始末》,101-112页;《晚明民变》,156-159页;帕森斯:《明末农民叛乱》,163-166页。
[226]《清世祖实录》,卷七,2甲-3甲;卷八,11甲-乙;卷十,7甲-乙。
[227]上书,卷七,2乙;卷十,10甲-乙,12甲-乙,14乙-15乙,并参看《清代名人传》中阿济格传第一卷,4-5页。
[228]《清世祖实录》,卷十,页12甲-乙。《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90页。《国榷》,第六册,6158页。《明季南略》,第一册,124页;第二册,218页。《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117-119页。
[229]《清世祖实录》,卷一二,页5甲,7甲-乙;卷一四,1乙-3乙。《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99页。《国榷》,第六册,6174页。
[230]《国榷》,第六册,6161页。《明季南略》,第一册,20页;第二册,218页。《圣安本纪》,第一册,16页。《青燐屑》,卷上,15乙。《清世祖实录》,卷一一,页23乙。
[231]《国榷》,第六册,6162-6164、6171、6174页。《明季南略》,第二册,209-210、218、220页。《圣安本纪》,第一册,18页。《明清档案存真选集》,第一册,131页。
[232]《清世祖实录》,卷一三,页7乙、9乙;卷一四,7乙,15甲-乙。《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101页(并参看《明清档案存真选集》,第一册,134页)。笔者认为,陈洪范可能是受清朝派遣,沿大运河南下,一路声称清兵即到,目的就是增强此一部署的牵制效果。
[233]《国榷》,第六册,6192页。《明季南略》,第一册,37、40页。《明清档案存真选集》,第三册,81页。
[234]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玄览堂丛书》本),卷一八,页5乙-6甲。王夫之:《永历日录》(1965年《船山全集》本),卷一三,页1甲。彭普生:《李自成被害日期探考》,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三期(八月),39页。《国榷》,第六册,6206页。
[235]《清世祖实录》,卷一八,页4甲-6甲。
[236]上书,卷一四,7乙-8甲;卷一五,页6甲。
[237]《明季南略》,第一册,28页;第二册,199-201页。《青燐屑》,卷下,页1甲、2甲-3乙。《纤言》,46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100-101页(《明清档案存真选集》,第一册,133-134页)。
[238]《圣安本纪》,第一册,22-23、26页。《国榷》,第六册,6184-6185、6200页。《青燐屑》,卷下,页12甲。《明季南略》,第一册,43页。《史忠正公集》,17-18页。《续幸存录》,328-329页。《甲乙日历》,105页。
[239]《清世祖实录》,卷一五,页6乙、11乙-12甲。《实录》兰阳误作“南阳”。《清实录》中有关南明时代事,这一类人名地名错误颇多。致误之由,可能在于战况报告后来由满文译成了汉文。有关诸如此类问题,参看黄彰健:《读清世祖实录》,载《明清史研究丛稿》(1977年台北版),594-612页。并参《国榷》,第六册,6194、6199、6200页;《明季南略》,第一册,37页;第二册,227页;《圣安本纪》,第一册,24页。
[240]《清世祖实录》,卷一六,页19乙-20甲。《国榷》,第六册,6201、6203页。《明季南略》,第一册,41页;第二册,227页。《圣安本纪》,第一册,24页。淮安的水道当时称为清河,黄、淮交汇处的战略要地则称为“清河口”。
[241]《史忠正公集》,21-22页。《青燐屑》,卷下,页10甲。《国榷》,第六册,6200、6202页。《明季南略》,第一册,41页;第二册,228页。《圣安本纪》,第一册,26页。《浔阳纪事》,页13甲-14甲。
[242]《国榷》,第六册,6203-6204、6206页。《明季南略》,第一册,42、44页;第二册,197-198、227-228页。
[243]《青燐屑》,卷下,11甲-12甲。《清世祖实录》,卷一六,页20甲-乙。
[244]《青燐屑》,卷下,页14甲、15乙-16乙。
[245]《清世祖实录》,卷一六,页20甲。《青燐屑》,卷下,页14甲、15乙-16甲。《国榷》,第六册,6205-6206。舒翼:《史可法扬州死难考》,载1959年9月17日《光明日报》史学版。
[246]王秀楚:《扬州十日记》(《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本,第二册)。并参看张德芳:《〈扬州十日记〉辨误》,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1964年上海版),365-376页。
[247]《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13甲。《清世祖实录》,卷一六,页20乙;卷一七,页9乙-10乙。《青燐屑》卷下,页16乙。《国榷》,第六册,6206页。
[248]当时人对此事有各种记载,时有混淆不清之处。此处参以己意,作一概述。见《清世祖实录》,卷一六,页20乙-21甲;《青燐屑》,卷下,页17甲;《明季南略》,第二册,233-234页;《三垣笔记》,附识下,弘光部分,页3甲-乙;《甲乙日历》,106页。
[249]马丁·马丁努斯(Martin Martinus):《鞑靼战史》(Bellum Tartaricum),英译本(1654年伦敦版),115页。虽然该书作者当时在南京,但笔者引用该书,着眼处是描写生动,而不是叙述精确。陈明山(Chen Min-Sun):《有关晚明及满洲人征服中国的三种当时的西方资料》(Three Contemporary Western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Ming and the Manchu Conquest of China)(博士论文,芝加哥大学,1971年)及埃德温·冯克莱(Edwin J.Van Kley):《来自中国的消息:十七世纪有关满洲人征服(中国)的记录》(News from China:Sevehteenth-Century Notices of the Manchu Conquest)(载《现代史学报》[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四五卷四期[1973年12月],561-582页)都以为,马丁纳斯所述确实可靠。这二种著作固多精彩处,对马丁纳斯的赞誉却欠妥,因为马丁纳斯与记述满洲人征服中国史事的其他欧洲传教士一样,所依靠的主要是传闻和想象。
[250]《明季南略》,第二册,234-236页。《圣安本纪》,第一册,29页。《三垣笔记》,附识,弘光部分,页3乙。
[251]《国榷》,第六册,6206(引文)-6207页。《明季南略》,第二册,179页。
[252]《国榷》,第六册,6207-6208页。
[253]上书,6208-6209页。《明季南略》,第一册,44页;第二册,231页。《纤言》,30页。皇太后究竟与皇帝一行同出,还是与马士英同出,记载各有不同。有些说,马士英企图把自己母亲冒充为太后(如《三垣笔记》,附识下,弘光部分,页6乙)。但是清朝的报告以及有关杭州事情的记述(马士英一行逃往杭州),证实了本书的说法。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页6乙;《甲乙日历》,113页;及黄道周:《黄漳浦文选》(1962年台北版),第二册,282-284页。
[254]《国榷》,第六册,6209-6211页。《明季南略》,第二册,180-182页。《圣安本纪》,第一册,28-29页。《纤言》,30-31、38-40页。
[255]《清世祖实录》,卷一六,页21甲-22甲。《国榷》,第六册,6212-6213页。《明季南略》,第二册,234-237册。
[256]《明季南略》,第二册,235页。《清世祖实录》,卷十,页13乙-14甲。多尔衮的晓谕原先发布于上一年11月22日南征之初。
[257]《国榷》,第六册,6213、6216页。《明季南略》,第二册,237-238页。
[258]《纤言》,50页。
[259]《国榷》,第六册,6216-6217页。《明季南略》,第二册,237-238页。《弘光实录钞》,260-261页。
[260]《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页5乙-6乙。《国榷》(第六册,6213页)将此事置于六月四日;《圣安本纪》(第一册,29页)则置于6月15日,并参看《明季南略》,第二册,231-232页。
[261]《国榷》,第六册,6212、6216页。《明季南略》,第一册,45页;第二册,323、235页。《圣安本纪》,第一册,29页。《纤言》,49页。
[262]《清世祖实录》,卷一八,页19甲-乙。《国榷》,第六册,6217页。《明季南略》,第二册,238页。《甲乙日历》,110、113-117、120页。《黄漳浦文选》,第二册,282-284页。徐芳烈:《浙东纪略》(《痛史》本),页1甲-2甲。闽人(陈燕翼):《思文大纪》(1967年台湾版),1页。并参看《清代名人传》博洛传:第一卷,16-17页。
[263]潞王在1646年六七月间清算明朝诸王时被处死,表面的理由是诸王谋为不轨(《清世祖实录》,卷二六,页10甲-11甲,“潞”误作“鲁”);“(假)太子”可能亦在同时被杀(《纤言》,44页)。福王据说死于1648年春(《国榷》,第六册,6217页),但是另有资料说,他与“太子”同时受诛(《明季南略》,第二册,238页)。
[264]唯一主要的例外是上文提到的黄得功与凌,以及河南中部统领众多塞堡的总兵刘洪起。见《明季南略》,第一册,22页;《圣安本纪》,第一册,28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42甲-乙;《明清档案存真选集》,第一册,141-142页。勋臣中唯一不投降的是刘孔昭。见《明季南略》,第二册,238页;《国榷》,第六册,6212页。
[265]《清世祖实录》,卷一六,页22甲。
[266]左军由良玉之子、副帅梦庚率领,在九江与东流间某地投降阿济格。见《清世祖实录》,卷一八,页5甲。刘泽清从海岸乞降,最后在1645年8月回到淮安投顺。见《明清档案存真选集》,第一册,146-147页;《清世祖实录》,卷一八,页9甲;卷一九,页5乙。
[267]《清世祖实录》,卷一四,页12甲-乙;卷一六,页9乙-10甲;卷一七,页4甲-乙;卷一八,页2甲-3乙。
[268]《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页8甲、13甲;卷一八,页20甲-21乙、24甲;卷一九,页2甲-3乙、6甲-乙;卷二一,页17甲;卷二四,页6甲-7甲。《明清档案存真选集》,第一册,144-145页;《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页8乙。
[269]《清世祖实录》,卷一八,页15甲、22乙。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七本(1948年4月),227-301页。陈作鉴《论洪承畴变节与人才外流》,载《畅流》,二七卷一一期(1963年7月),2-3页;二七卷一二期(1963年8月),12-13页;二八卷一期(1963年8月),12-13页。
[270]《清世祖实录》,卷六,页9甲-11甲;卷一七,页1乙-2甲、15甲-23乙。《明清档案存真选集》,第一册,11-13页。
[271]《清世祖实录》,卷一七,页3甲-乙。中山八郎:《汉地的辫发问题》,13-16页。海外散人《榕城见闻》,载《清史资料》,第一辑(1980年北京版),5页。
[272]《国榷》,第六册,6212页。《明季南略》,第二册,236页。
[273]《多尔衮摄政日记》(1976年台湾版),页1甲。北京一直谣传,满洲人将做出各种可怪而又凶残之事,多尔衮起先对此感到震怒。见《清世祖实录》,卷九,页2乙-3甲,7乙-8甲。8月29日,剃发易服令亦在北方加紧尽速执行。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九,页7甲-乙。
[274]《国榷》,第六册,6216页。佚名:《苏城纪变》(《明季史料丛书》本),页4甲。并参看第070页注1。有关当时江湖盗匪这一现象,见吴智和:《明代的江湖盗》,载《明史研究专刊》,一卷(1978年7月),107-137页。
[275]参看本书第053页,注1。森正夫:《关于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叛乱》(《一六四五年太倉州沙溪鎮における烏龍会の反乱について》),载《中山八郎教授颂寿纪念明清史论丛》(1977年东京版),195-232页。黄淳耀:《黄陶庵先生全集》(有1761年序),卷二,页2乙-3甲。《甲乙日历》,34-35、41、44、46、54、56、75、95、100页。《明季南略》,第二册,255、266-267页。《苏城纪变》,而1乙-2乙。无业游民通常在各都市谋得保镖与脚夫之职,随着明季的经济扩展,尤为如此。他们渐渐地结伙为盗,从事有组织的罪恶活动;或是独当一面,或是秘密受雇于有钱有势的当地豪强。见上田信:《明末清初江南都市围绕“无赖”的社会关系》(《明末清初江南の都市の“無賴”なめぐる社会関係》),载《史学杂志》,九〇卷一一期(1981年十一月),1-35页。
[276]有关第二手的研究,见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期间的地方主义与忠明情绪:江阴的悲剧》(Localism and Loyalism during the Ch’ing Conquest of Chiang-nan:The Tragedy of Chiang-yin),载《帝制中国后期的冲突与控制》,43-85页;赖家度:《1645年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载李光璧编《明清史论丛》(1957年武汉版),195-225页;邓尔麟:《嘉定忠臣录》,261-301页;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1955年上海版);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1971年台北影印本),17页。有关当时的资料,见《苏城纪变》;赵曦明:《江上孤忠录》;许重熙:《江阴守城记》(常附于时代较后的韩菼所著篇幅较长的《江阴城守记》之后);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南园啸客:《平吴事略》;漫游野史:《海角遗编》;朱子素:《东塘日札》(亦名《嘉定屠城纪略》,并以题为《嘉定县乙酉纪事》的节本印行);《陈忠裕年谱》,卷中,页31甲-乙;《枣林杂俎》,仁集,页25甲-乙;《明季南略》,第二册,252-253、255-256、258-259、262-263、265、279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58甲-乙。有关可以看作“忠”明的行为,拙著《康熙时期几位郁郁不得志的学者:其矛盾心理与所作所为》(Ambivalence and Action:Some-Frustrated Scholars of the K’ang-hsi Period)有简短的讨论,载史景迁、卫思韩合编《从明到清》,326-328页。学者已花费大量的工夫,以求确认最激烈抗清人物的社会经济的或学术、官僚系统的背景。多位作者以为,最爱国的或是农民,或是处于上升地位的市民,或是最具改革思想倾向的晚明政治、文学团体中人物。第一种看法根据如下情况:抗清活动持续最长的是在边远地区,其居民多数是农民。后两种看法所根据的则是:人口稠密与高度都市化的地区抗清最烈,在这些地区内,市民和知识分子团体为数最多。本注第一节所列各研究著作表明,17世纪的中国有各种社会集团和阶层,献身抗清的程度各有不同;现在就要对此作确切的概括,为时还过早。即使在个别的地区,形势已够复杂;就整个南方而言,那更是如此了。将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除提出抗清行为的模式之外,还应精密考察,不同的人为何而战。为反对什么而战;除应注意抗清活跃分子的社会阶层之外,还应着眼于各地特有的地理形势及物质资源。研究抗清领导及其思想归属之间关系的学者,应当留意这一事实,即有关明季书院及社团中著名人物的作用,历史记载往往有所夸大。关于这一点,可参看笔者博士论文《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历史的运用:清代历史著述中的南明》(Uses of Histo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The Southern Ming in Ch’ing Historiogra-phy),105-108页,以及拙著《徐氏兄弟及康熙时期对学者的半官方扶助》(The Hsü Brothers and Semioffcial Patronage of Scholars in the K’ang-hsi period),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四二卷一期,1982年6月,262-264页。
[277]《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页7甲、8甲、12甲、13乙。《清世祖实录》,卷二二,页18甲。
[278]《明清史料》,丙集,第六册,页205甲-乙、516甲-517乙。《清世祖实录》,卷二一,页4甲-5甲。《明季南略》,第二册,页265-266、268-269。
[279]《清世祖实录》,卷二四,页3甲-乙、15甲;卷二九,页9甲-乙。《明清史料》,甲集,第二册,页170甲、175甲。《平吴事略》,117页。迟至1646年仲秋,还有一次引起了惊恐的反抗,由瑞昌王领导,横扫过的地区就在南昌以南。见《明清史料》,甲集,第二册,页170-乙;《清世祖实录》,卷二八,页2乙。
[280]《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页2乙-3甲、12乙、14乙、17乙-18乙。《明季南略》,第二册,272-275页。《平吴事略》,112页。《苏城纪变》,第二册,272-275页。柳亚子《怀旧集》(1947年上海版),178-210页。
[281]彭孙贻:《湖西遗事》(《适园丛书》本),页2乙、4甲。
[282]上书,页2乙。徐世溥:《江变纪略》(《荆驼逸史》本),页1甲-乙。《国榷》,第六册,6102、6127、6157页。《明季南略》,第一册,78页。《清代名人传》,第一卷,166-167页。
[283]其中最活跃的是益王(朱由本)、永宁王(朱由)、瑞昌王(朱议泐)、罗川王(名不详)。见徐承礼:《小腆纪传》(1963年台北版),第六册,948-950、957-960页。《清世祖实录》,卷二〇,页11甲、23甲;卷二三,页6乙。《明清史料》,己集,第一册,页5甲。《黄漳浦文选》,第一册,105、118、126页。《思文大纪》,35页。黄彰健:《读明史余应桂、揭重熙、傅鼎铨三人传》,载《明史研究丛刊》,第一卷,127页。
[284]钱秉镫:《隆武纪年》(《所知录[一]》),页10乙-11甲、16甲、17乙。《永历实录》,卷一八,页4甲。《黄漳浦文选》,第一册,127页。
[285]张家玉:《张文烈遗集》(《沧海丛书》本),卷二上,页17乙-21乙。《清世祖实录》,卷二四,页9乙-10甲。《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59甲-乙。
[286]李介:《天香阁随笔》(在《笔记小说大观》内),卷一,页7甲-乙。
[287]《湖西遗事》,页4甲。该地区确实能战之兵估计有一万。见《张文烈遗集》,卷二上,页17乙。
[288]《张文烈遗集》,卷二上,页17甲。有关江西南部“奴变”事,参看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09-110页。
[289]《湖西遗事》,页4甲-乙。
[290]《隆武纪年》,页16甲-乙。《湖西遗事》,页5乙。康范生:《仿指南录》(《荆驼逸本》本),页1甲-乙。《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页529甲-乙。
[291]《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56甲-乙。
[292]帕森斯:《明末农民叛乱》,149-156页。
[293]见《永历实录》,卷十,各将领传。
[294]一位监军建议,打破常规,把文武机构合而为一。据说何腾蛟对此颇为赞赏。但是他受到阻力(原因不明),未能如此做。见《三垣笔记》,附识下,弘光部分,页1甲-2乙。《永历实录》,卷七,页1乙-2甲。《清代名人传》何腾蛟传;第一卷,290-291页。
[295]《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21甲-乙;丙编,第六本,页511甲、512乙、513甲、515甲。《清世祖实录》,卷二〇,页23甲。
[296]《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八,页5乙-6乙。《永历日录》,卷七,页2甲,5甲-乙;卷一三,页1乙。赵俪生、高昭一:《“夔东十三家”考》,载赵俪生编《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1955年上海版),156-157页。
[297]《永历实录》,卷七,页2甲-乙,5乙-6甲;卷一三,页2甲-乙。
[298]《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39甲;丙编,第六本,页514甲、515甲-乙;己集,第一册,页22甲。
[299]《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38甲-乙、148甲;第六本,页503甲-乙;丙编,第六本,页606甲、607甲-乙、614甲-乙。《清世祖实录》,卷一八,页15甲。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139-140页。
[300]《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44甲。《清世祖实录》,卷二一,页14甲-乙;卷二五,页7乙。《清代名人传》勒克德浑传;第一卷,443-444页。
[301]蒙正发:《三湘从事录》(《笔记小说大观》本),1310-1313、1316-1319、1324-1325页。《清世祖实录》,卷二八,页9甲。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145页。雷亮功《桂林田海记》(《明季史料丛书》本),页11乙。
[302]《永历实录》,卷七,页2乙。
[303]《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39甲、172甲;丙编,第六本,页511乙-512甲、513甲、520-521甲、551-乙、560甲、564甲、565甲-乙。《清世祖实录》,卷二二,页8乙-9甲;卷二六,页19甲;卷三〇,页5乙-6甲。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1966年台北影印本),卷一,页24乙-25甲,并见全书各处。在崇祯朝后期,该地各区,如麻城,一直有组织严密的“奴变”,也一直与李自成、张献忠政权合作。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01-103页。
[304]《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47甲;丙编,第六本,页514甲。《清世祖实录》,卷二五,页7乙-8乙、14乙。勒克德浑设法捕获李自成的侄子兼养子、“一只虎”李锦,但未成功。清朝称为“二只虎”的是李自成主将之一的刘体纯。有关这些人物,见汪宗衍:《读清史稿札记》(1977年香港版),201-202页。
[305]《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21乙、143甲;丙编,第六本,545甲-548甲。《清世祖实录》,卷二五,页13乙、16甲;卷二八,页9乙。
[306]《清世祖实录》,卷二七,页21乙、22乙。参看《清代名人传》耿、孔、尚诸人传;第一卷,416-417、445-446页;第二卷,635-636页。
[307]《三湘从事录》,1321、1327-1329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页593甲-乙。
[308]《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页608甲。
[309]《浙东纪略》,页2甲-乙。《甲乙日历》,117页。《刘蕺山先生年谱》,336页。
[310]《浙东纪略》,页4甲-5甲。佚名:《监国纪年》(《明季史料丛书》本),页1甲。钱肃乐:《钱忠介公集》(《四明丛书》本),卷九,页2甲,页7甲-9甲。查继佐:《鲁春秋》(1961年台北版),3-6页。全祖望:《鲒埼亭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七,《钱肃乐墓志铭》85-95页;《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孙嘉绩墓志铭》681-685页。《荷牐丛谈》,131-132页。参看《清世祖实录》,卷一九,页7甲。
[311]《监国纪年》,页1乙-2甲。《浙东纪略》,页5乙-6甲、7甲。《钱忠介公集》,卷九,页2甲。翁洲老民:《海东逸史》(1961年台北版),2页。《鲁春秋》,15页。佚名:《隆武遗事》(《痛史》本),页12甲。《鲒埼亭集》,卷七,《钱肃乐墓志铭》,85-86页。《荷牐丛谈》,133页。显然,建立监国政权之议在台州作出,而正式仪式则在绍兴举行。有关鲁王离开台州抵达绍兴的日期,上述各资料所说颇不相同。诸如此类问题,参看杨云萍:《南明鲁监国事迹的研究》,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八卷(1976年5月),34-36页。有关鲁监国系年事迹,见庄金德:《明监国鲁王以海纪事年表》,载《台湾文献》,一一卷一期(1951年3月),1-59页。并参看《清代名人传》朱以海传,见第一卷,180-181页。
[312]《浙东纪略》,页5甲-乙、6乙、7乙。《鲒埼亭集》,卷二六,321-323页。《鲁春秋》,6-14页。《明清史料》,丙集,第六册,页524甲-乙。有关防御据点及其将帅表,见盛成:《沈光文与明思宗及南渡诸王》,载《学术季刊》,四卷三期(1956年3月),46-47页。
[313]《思文大纪》,1-5页。
[314]《浙东纪略》,页1乙。参看《清代名人传》中郑鸿逵传,见第一卷,112页。
[315]《思文大纪》,2-3、5-17、19-20页。海外散人:《榕城纪闻》,4页。黄玉斋:《明隆武帝拥立的经纬》,载《台湾文献》,二十卷二期(1969年六月),128-155页。有关唐王监国令谕全文,见冯梦龙辑:《中兴伟略》(《明清史料集》本),页34甲-44甲。有关隆武朝事大略,见黄玉斋:《明隆武帝的政略》,载《台湾文献》,二十卷四期(1969年12月),142-170页。
[316]《思文大纪》,22、24页。《张文烈遗集》,卷一,页1甲-4甲、5乙-7乙、8乙;卷二,页3甲-5甲。
[317]《黄漳浦文》,171-172页。《思文大纪》,33-34页。《鲁春秋》,17-18页。涉及这两个朝廷间外交关系的原始资料散见各处。有关研究可参看陈汉光:《鲁唐交恶及鲁王之死》,载《台湾文献》,一一卷一期(1960年三月),106-111页;及杨云萍:《南明鲁监国事迹的研究》,38-46页。有关生年问题:1645年秋,鲁王27岁,唐王43岁。按照鲁唐二王本人推算世系的现存记载,二人分别是太祖第九子与二十二子的后裔(见鲁德福[Richard C.Rudolph]《明监国鲁王真墓》[The Real Tomb of the Ming Regent, Prince of Lu],载《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二九卷[1970-1971年],487-489页;及《思文大纪》21-22页)。然而这些说法似乎并不可靠。依照《明史》的《诸王世系表》(二、三),鲁王为太祖第十子十世孙,唐王为太祖二十三子九世孙。此一说法为盛成《沈光文与明思宗及南渡诸王》后附世系表所遵用,66-73页。无论如何,唐王被公认长鲁王一辈。
[318]《明季南略》,第二册,294页。査继佐、沈起:《东山国语》(1963年台北版),8-10页。《隆武纪年》,页9乙-10甲。《浙东纪略》,页8乙-9甲。
[319]《隆武遗事》附纪,页11甲-12乙。并见《思文大纪》,63页。
[320]《思文大纪》,60、62、86页。《隆武纪年》,页14乙。《浙东纪略》,页14甲-乙。《监国纪年》,页6甲。《鲁春秋》,25页。另一使者是金堡,他自愿往来闽浙间以为联络,此时也成为鲁王诸将帅争议之的,险遭不测。见其所著《岭海焚余》,13-19页。
[321]《思文大纪》,91页。《隆武纪年》,页20乙-21甲。
[322]《监国纪年》,页2甲、6甲,《鲁春秋》,24页。汪光复:《航澥遗闻》(《荆驼逸史》本),页1甲。
[323]《监国纪年》,页2乙、3乙。《海东逸史》,2页。《鲁春秋》,15页。《浙东纪略》,页7甲-乙。有关鲁王任命诸臣的最完备记载,见《荷牐丛谈》,133-134页。
[324]其中最令人遗憾的是方国安阵营对钱肃乐的指控。方国安其实已暗地接受隆武帝的任命,而钱肃乐拒不接受。钱肃乐的辞职,这类指控也是部分原因。见《海东逸史》,4页。《钱忠介公集》,卷十,页14甲。《鲒埼亭集》,卷七,88页。
[325]《隆武纪年》,页1甲-2甲、5甲。《清代名人传》,第一卷,196-198页。
[326]《明季南略》,第一册,7、10页。《圣安本纪》,第一册,9页。弘光朝是否恢复朱聿键的王爵,尚有疑问。计六奇和钱秉镫认为,朱聿键恢复王爵的请求遭拒绝(《明季南略》,第一册,25页;《隆武纪年》,页2甲);而隆武朝史官陈燕翼以为,此一请求被同意(《思文大纪》,3页)。
[327]《隆武纪年》,页4乙-5甲、10甲、14甲。《思文大纪》,5-6、14-15、22、24、26、30-31、71页。《中兴伟略》,页34甲-乙、39乙、41甲、42乙-43甲。隆武朝灭亡前不久,皇后产下头胎(子,显然有缺陷)(《隆武纪年》,页24甲-乙);但是没有记载表明,父母死后婴儿还活着。
[328]《思文大纪》,44、69、78、97、114页。《黄漳浦文选》,105-106页。《中兴伟略》,页37甲。
[329]《桂林田海记》,页4甲-8甲。《隆武纪年》,页9甲-乙。《思文大纪》,26、86页。靖江王名亭嘉。
[330]《隆武纪年》,页3甲-4甲、5甲、6甲、10甲-乙。隆武帝后来认识到这一点,对自己命官不慎感到后悔。见《思文大纪》,104、111、118页。
[331]《隆武纪年》,页4乙-5甲。《永历实录》,卷六,页1乙。隆武帝大部分大学士的姓名,见《隆武纪年》,页3甲,及《思文大纪》,13页。
[332]隆武帝显然因此而受人批评。见《思文大纪》,91-92页。
[333]《黄漳浦文选》,第一册,116-117、130、139、149、151、155页。《张文烈遗集》,卷二上,页12甲-乙。《思文大纪》,61-62、69、71、78、81、87页。
[334]《鲁春秋》,17、20页;《东山国语》,8-9页,《枣林杂俎》,仁集,页25乙。《思文大纪》,82页。
[335]张麟白:《浮海记》(1972年台北版),1页。《思文大纪》,29、34、55、83、91页。《鲁春秋》,22页。
[336]《思文大纪》,71、74、76、84、92、96页。《张文烈遗集》,卷二上,页6乙、13甲-乙。《黄漳浦文选》,第一册,131-132页。
[337]《思文大纪》,32、35、59、62-63、87-88页。《张文烈遗集》,卷二上、下。有关张家玉全部抗清事迹的研究,见麦少麟:《民族英雄张家玉》,载《广东文物》(1941年),第二册,588-611页。
[338]《思文大纪》,35、59-60、63、67、74、76-77、88页。《隆武纪年》,页11甲。李锦(又名李过)赐名赤心,高一功赐名必正,郝摇旗赐名永忠。诸名都含忠诚之意,因而象征诸人已由叛寇变为国家忠臣。
[339]《思文大纪》,59-60、62、77、98、103、112页。《隆武纪年》,页16乙-17甲、23乙。《张文烈遗集》,卷一,页7乙-8甲。《湖西遗事》,页4乙。
[340]钱秉镫:《藏山阁集选辑》(1966年台北版),第一册,4-5页。《隆武纪年》,页14甲。《思文大纪》,93-94、101-102、113-114页。《张文烈遗集》,卷二下,页13乙-14乙。
[341]《思文大纪》,23-24、29、67、72-73、81、83-84、96、103-104、107-108、114、140页。《隆武纪年》,页17甲-乙,《湖西遗事》,页5甲。《张文烈遗集》,卷二下,页31甲。有关明末清初此类问题的透彻研究,见森正夫:《十七世纪福建宁化县黄通的抗租叛乱》(《十七世紀の福建寧化縣における黄通の抗租反乱》),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集,二十卷(1973年),1-31页;二一卷(1974年),13-25页;二五卷(1978年),2565页。有关崇祯至康熙年间福建西南部各种动乱的原始记载,参看李世熊:《寇变记》,载《清史资料》(1980年北京版),第一集。当时该地区的佃户暴动决非首次发生。自16世纪初以来,每隔一段时间便发生暴动,至少有25次。见吴振强(Ng Chin-keong)《闽南农民社会研究1506—1644年》(A Study of the Peasant Society of South Fukien,1506—1644),载《南洋大学学报》(Nanyang University Journal),六卷(1972年),204-205页。
[342]《思文大纪》,22、39-40、54、62、64、77、81、88、90、92-93、98-99、101-102、1008-109、116页。《隆武纪年》,页10乙、12乙、13甲、14甲-乙。《黄漳浦文选》,第一册,123页。3月底,隆武帝再度切望“五路并出”(《思文大纪》,83页),张家玉上疏警告说,出福州之路无一安全,隆武应守“以固王基”(《张文烈遗集》,卷二下,页12乙-13甲)。
[343]《隆武纪年》,页5乙。
[344]《思文大纪》,95-96页。满洲人征服福建之初宣布,受降人数高达68500余(《清世祖实录》,卷二九,页2乙)。
[345]《思文大纪》,14、108页。《岭海焚余》,22页。
[346]《思文大纪》,95、128-129、136页。另有一些银两,隆武敕令直接自两广运往江西、湖广。可参《思文大纪》,77页。隆武帝的悲叹,间接显示了在此动荡年代税入的急剧下降。1630年以后,仅明季加派一项,福建每年即须缴纳161069两,相当于正赋的12%(吴振强《闽南农民社会研究》,196页)。可见仅就福建每年正常田赋而言,肯定已超过200万两。
[347]《中兴伟略》,页39乙。《思文大纪》,59、64、70、72、82、83-84、100、107、110、125页。《隆武纪年》,页5乙-6甲。
[348]《隆武遗事》,页5甲。《隆武纪年》,页6甲。《思文大纪》,122、126页。
[349]《思文大纪》,35、84、96、101、125、127、129、133页。《隆武遗事》,页5甲。
[350]罗友枝:《华南农业变化与农民经济》,第四章。
[351]有关郑芝龙生平概况,见廖汉臣:《郑芝龙考》,载《台湾文献》,(一)十卷四期(1959年12月),63-72页;(二)一一卷三期(1960年9月),1-15页;查尔斯·勃克色(Charles Boxer):《郑芝龙的兴起与没落》(The Rise and Fall of Nicholas Iquan),载《天下月刊》(T’ien Hsia-Monthly),一一卷五期(1941年四—五月),401-439页;卫思韩:《从汪直到施琅的海上中国;有关边缘地区的历史》(Maritime China from Wang Chih to Shih Lang:Themes in Peripheral History),载《从明到清》,216-219页;《清代名人传》,第一卷,110-111页。有关郑芝龙投顺及以后为福建明朝当局服务事,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1968年台北版),卷三七五,39-42页;前信次:《关于郑芝龙招安的情况》(《鄭芝龍招安の事情について》),载《中国学志》,一卷(1964年),141-170页。
[352]《思文大纪》,20、60、83页。《隆武纪年》,页14甲。《隆武遗事》,页1乙。
[353]《思文大纪》,31、35页。《隆武纪年》,页5乙。《隆武遗事》,页5乙。参看《清代名人传》中郑成功传,见第一卷,108-110页。郑芝龙幼弟芝豹任统率锦衣卫禁军之责,见《思文大纪》,33-34页。芝龙有四弟,其名字年龄见张宗洽:《郑芝龙兄弟究系几人》,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三期(9月),167-168页;郑喜文:《明郑史事五则》,载《台北文物》,十卷一期(1961年3月),82页。上述著作可补廖汉臣:《郑氏世系及人物考》之不足,廖文载《文献专刊》,一卷三期(1950年),54-64页。
[354]《隆武纪年》,页6甲。《隆武遗事》,页5甲。
[355]《思文大纪》,68、70、78、91、104页。《隆武纪年》,页6甲。《榕城纪闻》,4页。
[356]《思文大纪》,39-40、59、65、68、70、83页。《隆武纪年》,页7甲、12乙。《张文烈遗集》,卷二上,页7甲、24乙-27甲。有关郑彩生平以及他与郑芝龙一系的关系,见毛一波:《南明武臣郑彩的事迹》,载《民主评论》,一二卷一四期(1961年7月),14-18页;郑喜文:《明郑史事五则》,83页。
[357]《藏山阁集选辑》,第一册,5页。
[358]《隆武遗事》,页6甲。黄宗羲:《海外恸哭记》(《梨洲遗著汇刊》本),页17甲。《隆武纪年》,页14乙-15甲。迟至1646年7月,一位大臣愿捐助1万两私财供发展水军之用,未被采纳。《思文大纪》,135页。
[359]《隆武纪年》,页20乙-21甲。《枣林杂俎》,仁集,页25甲。华廷献:《闽事纪略》(1967年台北版),16-17页。
[360]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见《黄漳浦文选》,第三册,附录二。《清代名人传》,第一卷,345-347页。黄玉斋:《明隆武帝与尚书黄道周》,载《台湾文献》,二一卷一期(1970年3月),67-102页。
[361]361《明季南略》,第一册,24-25页。《思文大纪》,22页。《张文烈遗集》,卷二下,页20乙-21甲。
[362]《黄漳浦文选》,第二册,161-163页。
[363]《黄漳浦文选》,第一册,104-105页。
[364]上书,第一册,108-109页。
[365]《思文大纪》,25页。
[366]《黄漳浦文选》,第一册,107、110-113、117、125-126、143页。《隆武纪年》,页7甲-乙。
[367]《隆武纪年》,页7乙。
[368]《黄漳浦文选》,第一册,141-142、144页。
[369]上书,第一册,131-132、151页。
[370]《黄漳浦文选》,第一册,134-136、141、148-149、155页。《思文大纪》,56-57、86-87页。《明清史料》,甲集,第二册,页145甲、146甲。《世祖实录》,卷二二,页3乙;卷二三,页10乙(该书以为,黄道周被俘不久,在徽州被斩首,误)。
[371]《黄漳浦文选》,第一册,142、144页。
[372]《隆武纪年》,页6甲-乙。
[373]《黄漳浦文选》,第一册,115、136、141-142页。
[374]据说郑芝龙想迎其老友马士英入闽,但隆武帝最后不允。见《思文大纪》,22-24、46页。“清流”领袖、黄道周密友、户部尚书何楷,批评在晚秋小阳春天气于朝会用扇之类事情,使郑氏诸人大为恼怒。何楷不久即去职,为刺客所伤(据说乃郑氏所使),抵家后不久去世。见《隆武纪年》,页6乙。这类党争困扰明廷40余年,隆武帝对此不断提出警告。见《中兴伟略》,页42甲;《思文大纪》,41-42、60-61、67、93页。
[375]《思文大纪》,16-17、72、92-93、99、120、125页。《隆武纪年》,页11甲。《藏山阁集选辑》,第一册,3页。
[376]《思文大纪》,67、90、115-116、123、130-132、138、149、151页。并参看谢浩:《隆武“福京”“选举”考》,载《台湾文献》,四十卷(1977年6月),105-192页。
[377]《监国纪年》,页4甲。《鲁春秋》,18页。
[378]参看第079页注1,第081页注1。有关熊汝霖事,见《海外恸哭记》,页9甲;《明季南略》,第一册,94-95、142-143、188-189页;《国榷》,第六册,6134页。
[379]有关方国安事,见《鲁春秋》,16、20页;《枣林杂俎》,仁集,页25乙-26甲。王之仁事,见《鲁春秋》,16、24页。许都事,见《浙东纪略》,页11乙(尤其是关于他与地方官摩擦事);《明季南略》,第二册,295-296页。郑遵谦事,见《鲁春秋》,6页;《纤言》,52页;《岭海焚余》,3-5、14-15页。
[380]《监国纪年》,页3乙、5甲-乙。《浙东纪略》,页15乙。《鲁春秋》,23-24页。《钱忠介公集》,卷九,页17甲-乙。
[381]《浙东纪略》,页8乙、13乙-14甲。《鲁春秋》,19-20页。
[382]《荷牐丛谈》,138-142页。
[383]《监国纪年》,页3甲-乙。《钱忠介公集》,卷九,页21甲-122甲;卷十,5乙-17甲、12甲-13甲。《浙东纪略》,页7乙。《鲁春秋》,18页。《荷牐丛谈》,137-138页。
[384]《浙东纪略》,页9乙、11乙-112乙、14甲、15乙。《钱忠介公集》,卷十,页9乙-111乙、12甲-13甲。《鲁春秋》,25页。
[385]《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501甲;丙编,第六本,页509甲、553甲-556乙;己编,第一本,页4乙-5甲、6甲-乙、14甲。《清世祖实录》,卷二十,页17乙;卷二一,页6甲-乙;卷二二,页18乙。并参看《浙东纪略》,页8甲、13甲。
[386]太湖以南,“义兵”大量被歼。消息传来,浙东忠明之士为之气索。见《浙东纪略》,页15甲。清朝方面在攻陷徽州府后,便派军深入,进入了安徽的广信与浙江西南的天目山区。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45乙、153甲、159乙。《清世祖实录》,卷二四,页15乙。金声桓的主要副将王得仁,在浙江东北部一直进攻顺利,此时轻易通过杉关,进入了隆武地界。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56甲-乙。《清世祖实录》,卷二五,页21乙-22甲。
[387]《清世祖实录》,卷二四,页16甲-乙;卷二六,页22甲。
[388]《浙东纪略》,页16甲-乙。《东山国语》,10页。《监国纪年》,页6乙。《清世祖实录》,卷二六,页21乙-22甲。当年一篇游记也证实了桐庐河水之浅:“水清澈底,游鱼可数。妇女争取五色石,舟几覆。至七里滩,江流渐狭,名虽云江,其实是涧”。华廷献:《闽游日记》(《荆驼逸史》本),卷一,页1乙。
[389]《浙东纪略》,页16乙。《监国纪年》,页6乙。《鲁春秋》,26页。《航澥遗闻》,页1甲。鲁王一妾及太子在海上被决意降清的一个明水军将领绑架,二人都为清朝所杀。见《海外恸哭记》,页2乙。鲁王妃于1644年大顺军威胁鲁王在山东的王庄时自尽。见《航澥遗闻》,页1甲。
[390]《浙东纪略》,页18甲、21乙。《鲁春秋》,30-31、40-41页。《枣林杂俎》,仁集,页26甲。《清世祖实录》,卷二七,页21甲。
[391]《鲁春秋》,27-28、30-31页。《明季南略》,第二册,297-300页。《荷牐丛谈》,135页。黄宗羲:《四明山寨记》(《梨洲遗著汇刊》本),页1甲。投降者的大致名单,见《明清史料》,己编,页17甲。据该件记载,投降明军只有骑兵500,步兵7000。
[392]《清世祖实录》,卷二九,页1乙-2甲。《榕城纪闻》,5页。
[393]《思文大纪》,150-151页。
[394]《隆武纪年》,页25甲-乙。
[395]《隆武纪年》,页26甲。《思文大纪》,152页。《闽事纪略》,29页。隆武帝及皇后最终命运如何,传闻不一。可参看另一种《隆武纪年》(《梨洲遗著汇刊》本)后附识。此书为第二手资料,题黄宗羲撰。见该书页4乙。笔者此处所依据的,是江日升所得到的特别见证。见江日升:《台湾外纪》(1960年台北版),第一册,94页。《清世祖实录》所记,与此相同,见该书卷二九,页2甲。
[396]《思文大纪》,152-154页。《榕城纪闻》,5页。
[397]《思文大纪》,152页。《隆武纪年》,页22乙、24甲、28甲-乙。《清世祖实录》,卷二九,页2乙。有关清朝为浙东和福建所制定的安抚政策各项条文,见《清世祖实录》,卷三十,页15甲-21乙;《明清档案存真选集》,第一册,14-1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页583甲-584乙。
[398]《湖西遗事》,页5乙-6乙。《隆武纪年》,页16乙、19乙-20乙、29乙。《仿指南录》,页1乙-2甲。《清世祖实录》,卷二六,页6乙;卷二七,页20乙-21甲。《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页10甲。
[399]《隆武纪年》,页30甲-乙。《仿指南录》,页2甲-乙。
[400]《湘西遗事》,页9乙-10乙。《隆武纪年》,页30乙-31甲。《仿指南录》,页2乙-3甲。《清世祖实录》,卷二八,页10乙。《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71甲;丙编,第六本,页573甲-乙。
[401]《永历实录》,卷一,页1甲-2甲。钱秉镫:《永历纪年》(《所知录》,第二部分),页1甲。《明史》,卷一〇四,页34乙。并参看《清代名人传》朱由榔、瞿式耜、丁魁楚各传,分别见该书第一卷,193—195、199-201,及第二卷,723页。不少清代及20世纪著作称朱由榔为桂王;即使是谨严的学者,在阅读了17世纪末及18世纪的作品以后亦以为,由榔正式继承了桂王称号(例如柳亚子:《季明四帝谥法考》,载《大风半月刊》,七八卷[1940年11月],2534-2535页)。不过这一论断缺乏根据,理由是没有任何原始资料记载此事。而且在隆武帝去世之前,由榔被敕封为下一任桂王似乎不大可能。
[402](鲁可藻)《岭表纪年》(手抄本,无抄写日期),卷一,页2甲-乙。无论是永明王的生母马氏(常瀛之妾)还是妻子王氏,对他的影响都不及这位未来的皇太后王氏。见《岭表纪年》,卷一,页1乙;《永历实录》,卷一,页2甲。
[403]《永历实录》,卷一,页1乙-2乙。《岭表纪年》,卷一,页2乙-3甲。《三湘从事录》,1323-1324页。何是非:《风倒梧桐记》(《荆驼逸史》本),卷一,页1甲。肇庆是以前明朝藩王王庄的所在地,广东巡抚及两广总督也都驻在肇庆。见阮元等修:《广东通志》(1864年刊本),卷一八,页1甲-乙;卷八三,页28甲。有一篇博士论文专论永历朝事;萧大伟(David Shore):《明代中国的最后一朝:南方的永历政权(1647—1662)》(Last Court of Ming China:The Reign of the Yung-li Emperor in the South[1647—1662],1976年普林斯顿大学)。
[404]《岭表纪年》,卷一,页3乙。《永历纪年》,页2乙。
[405]《永历纪年》,页2乙-3甲。《岭表纪年》,卷一页3甲、4乙。《风倒梧桐记》,卷一,页1甲。三位大学士为:苏观生(参看《思文大纪》,24、59-60页;《隆武纪年》,页5乙;苏:《明苏爵辅事略》[1919年东莞刊本]);何吾驺(参看《思文大纪》,13页;《永历实录》,卷四,页1乙-2甲;李履庵:《关于何吾驺伍瑞隆史迹之研究》,载《广东文物》,二卷,612-644页);黄士俊(参看《思文大纪》,146页;《永历实录》,卷四,页2乙)。
[406]《思文大纪》,24页。《永历纪年》,页2乙-3甲。《岭表纪年》,卷一,页3乙-4甲。并参看杨云萍:《南明永历时代的研究》,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九卷(1977年4月),59-62页;黄玉斋:《明隆武帝与昭武》,载《台湾文献》,二一卷二期(1970年6月),102-105页。
[407]《永历纪年》,页3甲。《岭表纪年》,卷一,页4乙。在广州、梧州做调人的是陈邦彦,见其所著《陈岩野先生全集》,卷二,页1乙-2甲、4甲-6甲,及附于此集后其子陈恭尹所述行状,尤见页28甲。并参看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广东丛书》校本),卷十,页355乙;颜虚心:《明史陈邦彦传旁证》,载《广东文物》,二卷,551-587页。
[408]《永历纪年》,页3乙。《岭表纪年》,页5乙。《永历实录》,卷一,页2甲。绍武方面的信心,因广州城处于特别有利的防御地位而得到增强。在最近的动乱之前,广州一直由广东都指挥司驻守。见阮元等修:《广东通志》,卷一七三,页17乙。
[409]陈恭尹所述陈邦彦行状,载《陈岩野先生全集》,卷四,页28乙。《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页596甲。《清世祖实录》,卷三十,页24乙。朱希祖:《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及逷先(朱希祖笔名):《恭谒南明绍武君臣塚记》,均载《文史杂志》,二卷七一八期(1942年8月),分别见51-54、55-57页。《风倒梧桐记》,卷二,页5甲。
[410]《永历纪年》,页3乙-4甲、5乙。《岭表纪年》,卷一,页6乙-7甲。《风倒梧桐记》,卷一,页1乙、2乙。瞿共美:《东明闻见录》(《明季稗史初编》本),387页。
[411]佟养甲事,见《清史列传》(1928年上海版),卷四,页27甲-28乙。
[412]《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90甲-乙。《岭表纪年》,卷一,页11甲、14乙、17乙。《永历实录》,卷一,页2乙。《东明闻见录》,389页。瞿式耜:《瞿忠宣公集》(《乾坤正气集》本),卷三,页4乙。丁魁楚携大量财宝在梧州向李成栋投降,但是不久与其子一同被杀,见《岭表纪年》,卷一,页8乙-9甲;《风倒梧桐记》,卷一,页1乙-2甲。
[413]《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88甲-乙;丙编,第六本,页582乙。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委员会编:《文献丛编》(1930—1943年北平刊),卷二四,页19甲-20甲。有关1647年8月25日所制定的对广东抚绥政策各项条文,见《清世祖实录》,卷三三,页9甲-14甲。由李成栋率领进入广东的军队不足9500人,半数来自南直隶,半数来自福建。除李成栋和佟养甲带走的以外,剩下的军队还够每一府驻防七八百人,同时还要攻击“盗匪”与永历军。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页601甲-乙。
[414]《永历纪年》,页6甲。《岭表纪年》,卷一,页11甲。《永历实录》,卷一,页2乙-3甲。《东明闻见录》,388-389页。《瞿忠宣公集》,卷三,页3乙。
[415]《永历纪年》,页7乙-8甲。《岭表纪年》,卷一,页13甲、21甲-乙、23乙-24乙。《风倒梧桐记》,页2乙。《东明闻见录》,391页。《瞿忠宣公集》,卷三,页4甲、13乙-14乙。反岷王起义是响应张献忠侵入湖广而起,岷王感到了叛军的威胁,设法加固城墙,为此要人民出劳力,出财物,而人民因叛军临近而胆壮,起义反对岷王的征发。见马少侨:《明末武冈人民的反藩役斗争》,载李光璧编《明清史论丛》,135-144页。
[416]《岭表纪年》,卷一,页10甲-乙、15甲-16甲、25乙-26甲(引文)。《东明闻见录》,390、392页。
[417]《三湘从事录》,1331-1334、1336页。《岭表纪年》,卷一,页26甲-乙。《永历实录》,卷一,页3甲-乙;卷七,页4甲。《东明闻见录》,390页。《瞿忠宣公集》,卷三,页15乙-17乙。
[418]《三湘从事录》,1327-1332、1334-1335、1341、1346-1347页。《岭表纪年》,卷一,页13甲、19甲、22乙。《永历实录》,卷一,页2乙-3甲。
[419]《清世祖实录》,卷三一,页16甲-乙;卷三二,页22乙;卷三五,页7甲、11乙-15甲。《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页593。有意思的是,清湖广总督抱怨说,虽然湖广清军(为进攻作战)人数已加倍,但因要求使用湖广资源援助河南与江宁(南京),可用的军需实际已减少。见《文献丛编》,卷二五,页28乙-29乙。
[420]《岭表纪年》,卷一,页31乙-22甲、34甲-乙。《三湘从事录》,1345-1346页。《东明闻见录》,392页。《风倒梧桐记》,卷一,页2乙。《永历纪年》,页9乙-10甲。《永历实录》,卷一,页3乙。
[421]《岭表纪年》,卷一,页30甲-32甲、33甲-乙、38乙、40甲-乙;卷二,页4乙-6乙。《桂林田海记》,页10甲-11乙。《三湘从事录》,1344-1345、1349-1350页。《东明闻见录》,394-395页。《瞿忠宣公集》,卷四,页3甲-5甲。《永历纪年》,页12甲-13甲、14甲。《风倒梧桐记》,卷一,页3甲。《清世祖实录》,卷三八,页5甲。
[422]《三湘从事录》,1350页。《桂林田海记》,页12甲-乙。《岭表纪年》,卷二,页6甲。《瞿忠宣公集》,卷四,页18甲。《永历纪年》,页13乙-14甲。
[423]张名振事,参看《清代名人传》,第一卷,46-47页。
[424]周鹤芝亦名崔芝。他因中年改名、异体字及其他字形异同,在不同著作及同一著作不同地方,往往有几个相似的名字。见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师研究》(《明末清初日本乞师の研究》,1945年东京版),11-14;《浮海记》,9-12页。
[425]《鲁春秋》,22页。《思文大纪》,34页。《浮海记》,7-8页。《航澥遗闻》,页1乙。《怀旧集》,178-210页。张家璧:《难游录》(载《明季野史杂钞》),无页码。
[426]《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85甲,第三本,页202甲;丁编,第一本,页6甲-乙;己编,第一本,页25甲。《清世祖实录》,卷三一,页19乙-20甲;卷三二,页1乙-2甲、4甲-5乙、8甲-乙。题黄宗義撰:《舟山兴废》(《梨洲遗著汇刊》本),页1乙-2甲。《航澥遗闻》,页1乙-2甲。黄宗羲以为,把吴胜兆的要求向黄斌卿提出的是陈子龙(《海外恸哭记》,页5甲-乙),但是这一说法看来有问题(见艾维四《陈子龙》,139-140页)。更有可能的是,吴胜兆差遣的是几个被俘的舟山人。这一年稍早,这些人试图从崇明攻入长江三角洲,失败被俘。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78甲-乙;丁编,第一本,页4甲-乙;己编,第一本,页4甲。有些著述认为,在这次计划中起领导作用的是热情的抗清少年夏完淳。见《东山国语》,101-103;《怀旧集》,211-237;以及新刊本《夏完淳集》(1959年北京版)中介绍夏完淳生平的前言。
[427]《鲁春秋》,46、65页。《海外恸哭记》,页8乙。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1970年台北版),第二册,124页。《清世祖实录》,卷三五,页8乙。并参《鲒埼亭集》,卷八,97-99页,《董志宁墓志铭》。
[428]《监国纪年》,页7乙。《舟山兴废》,页1甲。《航澥遗闻》,页1乙。
[429]《监国纪年》,页7乙-8甲。《海外恸哭记》,页3甲。
[430]《监国纪年》,页8甲-乙。《海外恸哭记》,页3乙-4甲。《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页5甲、8甲。《格城纪闻》,7-8页。
[431]鲁王朝任官诸人姓氏,见盛成:《沈光文》,55-57页,及毛一波:《鲁王抗清与明郑关系》,载《台湾文献》,一一卷一期(1960年3月),60-74页。不过二文均低估了福建人的参与,都没有指出几个来自浙东的人物先前曾在福建做官。
[432]《监国纪年》,页8甲-10乙。《海外恸哭记》,页4乙、7甲-8甲、9甲。《航澥遗闻》,页2甲。《鲁春秋》,43-45、48、52页。《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页8甲-乙。《清世祖实录》,卷三二,页8乙;卷三五,页19甲。对清军控制内陆最大的威胁,是明郧西王和一个名叫王祁的和尚所领导的反抗。虽然清军得以保住浦城,但建宁直到次年(1648)4月才安定下来,该地区的军事行动至少持续到1651年。1647—1648年冬,另外几位明朝次一级的藩王以及几群当地的忠明之士,在整个福建中部群山环抱的地区,也领导了起义,多年以后才完全平定。见《海外恸哭记》,页10乙。《鲁春秋》,44、53-54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页210甲、220甲-乙、221甲、230甲、245甲、277甲-乙;丁编,第一本,页10甲-11甲。《清世祖实录》,卷三三,页8甲-乙;卷三六,页2乙-3甲、10乙;卷四五,页18甲;卷四七,页5乙,1647年8月,福建北部各地,包括省府福州,爆发了暴动,起事者配合良好,清朝当局采取了严厉措施,才能维持对该地民众的脆弱统治。见《榕城纪闻》,6-7页。
[433]实际上,直至17世纪50年代晚期,闽赣交界处的整个山区,都公然蔑视中央政府的控制。而且,在70年代,当清朝在遥远的南方的控制力,因“三藩之乱”而陷于困境时,这里的骚乱又再度被激发。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05-107页,112-115页。然而,由于这些人民同清朝当局进行了如此长久的战斗,便断言他们是特别坚定的爱国主义者,那也还不能作为定论。
[434]《监国纪年》,页11乙。《鲁春秋》,56页。
[435]《监国纪年》,页10甲-乙。《海外恸哭记》,页9甲-10乙。《航澥遗闻》,页2甲。《鲁春秋》,47-48页。
[436]《监国纪年》,页11甲。《鲁春秋》,53-54页。《航澥遗闻》,页2乙。有一种说法是“钱肃乐原有先天疾病,因与郑彩不能相得,疾发而死”。但这一时期钱肃乐的各篇奏议表明,此一说法不确。事实是,钱肃乐一直支持郑彩,认为鲁王手下各支军队若要联合一致,维持军纪,非由郑彩统率不可;而各将领,尤其是义勇将领,不愿接受这样的指挥,他对此大感沮丧。见《钱忠介公集》,卷一三,页7乙-10乙、14乙-16甲、20乙。
[437]《航澥遗闻》,页2乙。
[438]《监国纪年》,页11甲-乙。《海外恸哭记》,页10乙。《鲁春秋》,56-57页。《清世祖实录》,卷四二,页1乙-2甲;卷四三,页9甲、18乙。
[439]《监国纪年》,页11乙。《海外恸哭记》,页11乙-12甲。《鲁春秋》,54页。林春胜辑:《华夷变态》(1958—1959年东京版),第一册,31、41、43页。
[440]有关张名振一生,参看廖汉臣:《鲁王抗清与二张的武功》,载《台湾文献》,一一卷一期(1960年3月),81-102页。据说张名振背上刺“赤心报国”四字,见《航澥遗闻》,页5甲。
[441]对张名振的政策指责最厉害的,是礼部尚书吴钟峦及副都御史黄宗羲。见《四明山寨记》,页2甲。《海外恸哭记》,页12乙。郑彩把持朝政,吴钟峦也表示同样的不满。见《监国纪年》,页9乙。有关吴钟峦事,参看《海外恸哭记》,页17甲-乙;有关黄宗羲事,参看《清代名人传》,第一卷,351-354页。
[442]《海外恸哭记》,页14乙-15甲、16甲。王翊与冯京第传记,分别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四,689-693页;陈田:《明诗纪事》,第二五册,2802-2803页。
[443]《四明山寨记》,页1甲-乙。《海外恸哭记》,页10乙、16甲-乙。
[444]《海外恸哭记》,页15甲。
[445]《监国纪年》,页12甲-乙。《浮海记》,9页。《航澥遗闻》,页2乙-3乙。《海外恸哭记》,页13乙-14甲。
[446]《海外恸哭记》,页14乙-15甲、16甲-乙。《四明山寨记》,页2甲。《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页213甲、257甲-乙、261甲-乙、265甲、268甲-乙;丁编,第一本,页7甲;己编,第一本,页23甲-24甲。《清世祖实录》,卷四十,页20乙;卷四六,页9乙。
[447]《监国纪年》,页13甲-乙。《海外恸哭记》,页15乙-16乙。《四明山寨记》,页2乙。《航澥遗闻》,页3乙。《鲁春秋》,60页。
[448]《监国纪年》,页13甲。《航澥遗闻》,页3乙。《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页284甲-285甲;第四本,页381乙。
[449]《监国纪年》,页13乙-15甲。《航澥遗闻》,页3乙-4甲。《难游录》,无页码。《海外恸哭记》,页16乙-17甲、19甲。《鲁春秋》,62-63页。《清世祖实录》,卷五九,页28乙;卷六十,页8甲-乙。殉难诸人有:张名振之兄及张家全家其余50人,鲁王家人至少13位,21名尚书、侍郎及其他官员,其中许多全家遇害。鲁王长子、次子被俘。鲁王妾亦被掳,被人所得,居于杭州。后来鲁王暗地设法将其妾从此人手中赎出。见苏同炳:《鲁王使刘忠至杭州赎取王妃及其子案》,载《台湾文献》,二十卷三期(1969年9月),111-117页。
[450]郑成功爵衔提升一事的始末,情形复杂,颇多问题,尤其是后来最为人知的延平王衔,更是如此。朱希祖《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一文对此作了最彻底的研究,载《国立北平大学国学季刊》,三卷一期(1932年3月),87-112页。并参黄玉斋:《明永历帝封朱成功为延平王考》,载《台湾文物论集》(1966年台北版),87-94页;毛一波:《郑成功官爵考》,载《台湾文物》二三卷四期(1973年12月),5-6页;苏同炳:《延平王与延平郡王之争平议》,载《台湾文献》,二四卷二期(1973年6月),10-13页。郑成功与在肇庆的永历帝之间有接触,有关此事,见《永历纪年》,页21甲-乙;《岭表纪年》,卷二,页18乙。
[451]鲁王究竟何时抵达;被招待住在厦门,处境如何,没有一种原始资料对此有清楚的说明。这里所说的有几点,是从原始记载或第二手资料推断而得,在某些方面是有问题的。有关此事,可参看庄金德:《明监国鲁王以海纪事年表》,30-31页,及234-235页注释;张菼:《郑成功纪事编年》(1965年台北版),46页注释。鲁王除在南澳岛居留三年(1656—1659)外,终其余年,一直住在金门(见其墓志铭。鲁德福译成英文,在其《明监国鲁王真墓》一文中,见490页)。清代著述中普遍有一看法:郑成功将鲁王溺死。这肯定是不确的。在中国学者中,毛一波最着力指出这一点。见其《书鲁王之死与郑成功受诬事》,载《文献专刊》,四卷三一四期(1953年12月),9-10页;及《浙闽公案与南澳公案》,载《台湾文献》,一一卷一期(1960年3月),75-80页(收入其《南明史谈》[1970年台北版],1-13页)。
[452]不过,郑成功郑重地焚烧其儒服一事,可能是齐东野人之谈。见杨云萍:《郑成功焚儒服考》,载《台湾研究》,一卷(1956年6月),31-37页;及陈碧笙:《一六四六年郑成功海上起兵经过》,载《历史研究》,1978年八期(8月),92-93页。
[453]阮旻锡(别号鹭岛道人):《海上见闻录》(1958年台北版),4-7页。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1931年北京版),页1乙-3乙。《台湾外记》,第一册,97-98、100-103、105-108页。《隆武纪年》,页29甲。《清世祖实录》,卷四三,页15乙;卷四六,页15甲;卷四九,页6乙。有关郑成功沿海抗清事业的早期阶段,见金成前:《郑成功起兵后十五年间征战事略》,载《台湾文献》,二三卷四期(1972年12月),80-82页。陈世庆:《明郑前后之金门兵事》,载《台湾文献》,六卷一期(1955年3月),1-3页。
[454]《海上见闻录》,7-9页。《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3乙-4乙、5乙-9乙。《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页276甲。《清世祖实录》,卷五十,页8乙。
[455]《海上见闻录》,9页。《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9乙-10甲。《台湾外记》,第一册,113-115页。
[456]《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0乙-14乙。《海上见闻录》,9页。魏永竹:《郑成功南下勤王之探讨》,载《台湾文献》,三三卷一期(1982年3月),133-134页。
[457]《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3乙、14乙-15甲。《海上见闻录》,10-11页。《台湾外记》,第一册,118-119页。
[458]王伊同(Wang Yi-T’ung)《1368—1549年的中日官方关系》(Off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1368—1549,1953年麻省剑桥版),80-81页。卫思韩《从汪直到施琅的海上中国》,210-215页。吴振强《明朝后半期福建人的海上贸易——政府政策与中坚集团的态度(The Fukienese Maritime Trad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Ming Period—Government Policy and Elite Groups’ Attitudes),载《南洋大学学报》(Nanyang University Journal),五卷二期(1971年),81-100页。
[459]苏均炜(Kwan-wai So)《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日本海盗》(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1975年密歇根州东莱辛版),第二章。
[460]上书,地图1-4。
[461]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师研究》为此一领域的经典性研究。见该书1-130页。并参看杨云萍:《南明时代与日本的关系》,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六卷(1974年5月),1-17页;黄玉斋:《明郑成功等的抗清与日本》,载《台湾文献》,九卷四期(1958年十二月),90-126页;及黄玉斋:《郑成功时代与日本德川幕府》,载《台湾文献》,一三卷一期(1962年3月),114-134页。1639年至1646年,中国船只前往日本贸易的有显著增加。由此事可见,随德川幕府的建立而来的稳定,使日本支付进口货物的能力增加;自1639年日本政府实施“锁国”政策以来,中国商人所起的作用增大。见岩生成一(Iwao Seiichi)《十六与十七世纪日本对外贸易》(Japanese Foreign Trad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载《亚洲学报》(Acta Asiatica),三十卷(1976年),11页。除此之外,这件事亦反映了明朝管理海疆的能力每况愈下之际,中国水手对朝廷禁令更为不屑一顾。
[462]朱之渝(其字舜水更为人所知)最后定居日本,教授弟子,创立了儒家水户学派,影响深远。见秦家懿(Juliu Ching):《朱舜水,1600—1632:日本德川时代的中国儒学者》(Chu Shun-shui,1600—1682:A Chinese Confucian Scholar in Tokugawa Japan),载《日本学志》(Monumenta Nipponica),三十卷二期(1975年夏),177-191页。朱之渝传记,见《清代名人传》,第一卷,179-180页;王进祥:《朱舜水评传》(1976年台北版);郭垣:《朱舜水》(1964年台北重刊1937年版)。特别有关其卷入沿海抗清活动事,见石原道博《郑成功与朱舜水》,载《台湾风物》,四卷八—九期(1954年9月),11-18页。全祖望以为,黄宗羲至少有一次曾随朱之渝与冯京第东渡日本。梁启超对此作了辩驳(见《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载《东方杂志》,二十卷六期[1923年3月],54-56页),但是证据并不坚实。欲深入考虑此一问题,参看《明末清初日本乞师研究》,20-21页。
[463]廖汉臣《郑芝龙考》,(1)69-70页,(2)1-2页。
[464]有关琉球王在中国与日本之间所保持的特殊双重政治地位,见罗伯特·K.沙加(Robert K.Sakai):《萨摩封邑琉球群岛》(The Ryukyu[Liu-Ch’iu]Islands as a Fief of Satsuma),载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1968年麻省剑桥版),112-134页。
[465]有关德川幕府经由长崎监督“唐船”即中国商船事,见浦廉一:《华夷变态解说——唐船风说书研究》(《華夷變態解説—唐船風説書の研究》),林春胜辑:《华夷变态》,第一卷前言。
[466]罗纳德·P.托比(Ronald P.Toby):《重论锁国问题:为使德川幕府取得合法地位所作的外交活动》(Reopening the Question of Sakohu:Diplomacy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okugawa Bakufu),载《日本研究学报》(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三卷二期(1977年夏),323-363页。有关因日本入侵朝鲜而引起的中日之战。见乔治·沙松(George Sansom)《l334—1615年日本史》(A History of Japan,1334—1615,1961年斯坦福版),36-39页;及查尔斯·R.勃克色(Charles R.Boxer)《日本的基督教世纪:1549—1650年》(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1549—1650,1951年柏克莱版),第八章,尤见383.-389页。有关反基督教运动,见乔治·艾利逊(George Elison):《上帝被毁:日本近代史初期的基督教形象》(Deus Destroyed:The Image of Christianity in Early Modern Japan)(1973年剑桥版)。
[467]《明末清初日本乞师研究》,9-10、40页。《华夷变态》,第一卷,11-13页。荷兰东印度公司编,村上直次郎译:《出岛兰馆日志》(1939年东京版),第三卷,日记,2、6页。
[468]《思文大纪》,144页。《华夷变态》,第一卷,16-20、22-25页。《明末清初日本乞师研究》,31-35、48页。许多日本领袖对派兵前往中国有兴趣,有关进一步的证据,见罗纳德·托比:《近代日本早期的国家与外文》(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As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kugawa Bakufu,1984年普林斯顿版),第4章。
[469]题黄宗羲撰:《日本乞师记》(《梨洲遗著汇刊》本),页1乙。《鲁春秋》,61页。
[470]《日本乞师记》,页1甲。《海外恸哭记》,页4甲-乙、6乙-7甲。《明末清初日本乞师研究》,2、6-7、16、18-19页。中国铜钱长期以来是日本的标准货币,明朝初年日本进口中国铜钱的数量尤为巨大,见《1368—1549年的中日官方关系》,101-106页,这次岛津所送的是洪武钱。
[471]《华夷变态》,第一卷,25-29页。此书所载郑成功函只有日文片假名译文,后由川口长孺重译成中文,载其所著《台湾郑氏纪事》(1958年台湾版),卷上,25页。
[472]《华夷变态》,第一卷,30-32、37-38、40-41页。有关明清交替时期琉球的地位,见《明末清初日本乞师研究》,131-187页;及杨云萍:《南明时代与琉球之关系的研究》,载《史学汇刊》,二卷(1969年8月),173-187页。
[473]《日本乞师记》,页2甲-乙。《海外恸哭记》,页3乙。《华夷变态》,第一卷,44页。
[474]《明末清初日本乞师研究》,51-52页。《鲁春秋》,61页。《台湾外记》,第一册,123页。《华夷变态》,第一卷,45-46页。《海上见闻录》,36页。
[475]托比:《重论锁国问题》,358页。
[476]有关就中国政治局势向幕府的报告,见《华夷变态》,第一卷,33-35页。
[477]拙著《影响广州三角洲地区南明诸事件概述》(A Sketch of Southern Ming Events Affecting the Canton Delta Area),提交1973年香港大学广州三角洲学术讨论会论文,1-4页。此类有关地方瓦解的资料,其主要来源是清代中期和后期的各县、府、省方志,例如《惠州府志》(1688年刊),卷五;《广州府志》(1879年刊),卷七九、八十;《揭阳县志》(1779年刊),卷七九;《顺德县志》(咸丰时刊),卷三一;《新会县志》(1840年刊),卷一三;《高要县志》(1826年刊),卷十。地方志并非这一时期当时人的记载,因此笔者不用它们来研究南明本身。但是若要对该时期社会瓦解作系统的研究,非依靠地方志不可。有关后一种研究之例,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尤其是120-122页论广东部分。
[478]《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页29乙。
[479]有关“岭表三忠”抗清活动最为综合性的研究,见黎杰:《南明广东三忠史迹考》,载《珠海学报》三卷(1970年6月),162-173页。有关佟养甲所作的扼要报告,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页639甲-640乙。并参看《清代名人传》陈子龙条见第一卷,101-102页。
[480]李健儿:《陈子壮年谱》,载《广东文物》,第二册,516-550页。《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页374甲-377乙。《永历实录》,卷六,页1甲-乙。
[481]颜虚心:《明史陈邦彦传旁证》,载《广东文物》,第二册,551-587页。《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页355甲-362甲。《陈岩野先生集》,卷二,页4甲,6甲-乙;卷四,页26甲-32乙(行状)。
[482]麦少麟:《民族英雄张家玉》,载《广东文物》,第二册,588-611页。《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页363乙-369甲。《张文烈遗集》,卷四,页1甲-乙,3甲-7乙。
[483]《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页356乙-357甲。《陈岩野先生集》,卷四,页29甲。《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91甲;己编,第一本,29乙。
[484]《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页357乙。《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页30甲。《清世祖实录》,卷三四,页7甲-乙。
[485]《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页365乙-366甲。《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页29乙。《清世祖实录》,卷三四,页7乙。
[486]《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页366乙-367甲。《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页639乙。
[487]有关其他例子,则见本书第130页注1章旷部分,及本书第225页注1张同敞部分。
[488]《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页357甲-乙。《永历纪年》,页10乙。《陈岩野先生集》,卷四,页29乙-30乙。《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页610甲-乙、619甲。
[489]《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页358甲-乙、376甲-乙。《陈岩野先生集》,卷四,页31乙。《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页639甲-乙。《清世祖实录》,卷三五,页2乙。
[490]《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页367甲-乙。《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页639甲-乙。
[491]《国榷》,第六册,6155、6159页。
[492]《小腆纪传》,页1甲-乙。
[493]徐世溥《江变纪略》以为,金声桓被任为副总兵官,因而不满(页1乙);但是从各种清朝文献可见,他所担任的是总兵官。这种矛盾说法的原因其实在于:他失去了原在明朝一个都督府的都督佥事之职,因为清朝并未设立此一职位。参看《湖西遗事》,页2乙;《江变纪略》,页3乙;《永历实录》,卷一一,页1乙。
[494]《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22乙。金声桓在奏疏中自称战功辉煌,见《清世祖实录》,卷二二,页6甲-乙,及《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页552甲-乙。而后来清江西巡抚的奏疏则称金声桓“真系江省腹蠹也”,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页616乙。并参故宫博物院文献委员会《文献丛编》,卷二五,页33乙-34甲。
[495]王得仁起家于自湖广入北赣的大顺军。《江变纪略》,页1甲-2乙。《永历实录》,卷一一,页2乙-3甲。
[496]《清世祖实录》,卷二六,页9乙-10甲。《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页3乙。
[497]《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页575甲。《文献丛编》,卷二五,页34乙、36甲。《永历实录》,卷一一,页2甲-乙。
[498]《永历实录》,卷一一,页1甲、2乙-3乙。《江变纪略》,页2乙-3甲。《三湘从事录》,1351页。《岭表纪年》,卷二,页4甲-乙。《永历纪年》,页15甲。《清世祖实录》,卷三六,页9甲-乙。《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页663甲、674甲。
[499]《永历实录》,卷一,页3乙-4甲;卷六,页4乙。
[500]《清世祖实录》,卷三六,页10乙;卷三七,页20甲;第三八,页4甲-乙、8乙-10甲。《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页663甲、674甲;第八本,页701甲-乙。《监国纪年》,页10乙。《海外恸哭记》,页10甲-乙。
[501]有关西北伊斯兰教徒与李自成起事的关系以及清军压服伊斯兰教徒所遇到的棘手事,见罗茂锐(Morris Rossabi):《穆斯林与中亚的叛乱》(Muslim and Central Asian Revolts),载《从明到清》,185-192页。清朝直至此时平定陕西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贺珍、孙守法、武大定等前大顺军与明军的将领。这些人活动于陕西最南部汉中、兴安一带。他们虽从南明各朝廷接受封爵,却都是独立行事。《清世祖实录》,卷二三,页2乙-3甲、7乙;卷二四,页9乙;卷二九,页12甲-乙;卷三一,页20乙;卷三二,页22乙;卷三七,页24乙-25甲。《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页103。《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137-138页。上述二事,均可参考谢国桢:《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267-284页。
[502]《清世祖实录》,卷四一,页17甲、19甲、20甲-乙、21乙;卷四二,页2甲、4甲、6甲-8乙、12乙-13甲、17甲;卷四三,页1乙-7甲、11甲、12甲、19甲-乙;卷四四,页16乙、19乙、26乙-27甲;卷四五,页1乙、3乙、6甲-乙、9乙-10甲;卷四六,页2甲-乙、8甲-乙、15甲、25甲;卷四七,页1乙(以上仅是有关晋省事)。有关姜瓖事,参看《清代名人传》,第一卷,138页。
[503]此一时期北方的不安,大半起因于清廷的一项禁令,即凡盗寇所用的各种武器、牲口,百姓不得拥有,亦不得买卖。两年前,清廷以为此禁令当予废除;此时则予以恢复,并严厉执行。《清世祖实录》,卷二八,页14乙;卷三四,页16甲-乙;卷四十,页7甲-8乙。各绿林团体因此感受压力,只能公开攻掠以取得这类必需之物。普通百姓亦因此禁令而丧失了对抗歹徒的自卫手段,于是起而暴动。1649年5月,清廷感到此一禁令以取消为宜,只禁止大炮与甲胄。《清世祖实录》,卷四三,页9乙。1648-1649年间,就清朝方面而言,因其领导层的某些损失而局势更形恶化。在多尔衮的严厉统治下,几位重要的亲王与其他贵族因各类违法事件而受到质询(《清世祖实录》,卷三七,页2甲,15乙);在大同战役中,北直隶北部突然有天花流行,满洲最有才略的领袖人物之一、多尔衮之弟多铎亦因此丧命,年仅36岁(卷四三,页4乙、8乙)。
[504]《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页673甲、682甲、689甲-乙。《文献丛编》,卷一三,顺治揭帖,页3乙-4甲。《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152-153、155-158、159-160页。《岭表纪年》,卷二,页11甲、21甲-乙。《瞿忠宣公集》,卷四,页19甲-乙。《永历纪年》,页22乙、24甲。《永历实录》,卷一,页4甲。《三湘从事录》,1359页。
[505]《岭表纪年》,页12甲、21乙-22甲。《三湘从事录》,1351、1359页。《永历实录》,卷一,页4乙;卷七,页4甲。《永历纪年》,页19乙-20甲、21甲-乙。《瞿忠宣公集》,卷四,页5甲-7甲、18甲、19乙-20甲。
[506]《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李,页8甲、12甲、13乙。
[507]上书,丙编,第六本,页596甲-乙;丁编,第一本,页2甲-乙。
[508]《清世祖实录》,卷三二,页6乙、16甲。
[509]《永历实录》,卷一一,页3乙。《三湘从事录》,1352页。不过,有种常为人所引用的记载说,李成栋已派人将其部分家属自松江接出,可见他准备反正(《永历纪年》,页15甲-乙,16甲-乙)。此一说法与清廷允佟养甲所请事吻合,当时佟养甲请求清廷允许李成栋及其部将将家属接至广东(《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595页甲)。
[510]《风倒梧桐记》,卷一,页3甲-乙。《永历纪年》,页16甲。《永历实录》,卷一一,页4甲。这位爱国妇女后来成了许多民间唱词与戏曲中的英雄人物。见简又文:《南明民族女英雄张玉乔考证》,载《大陆杂志》,四一卷六期(1970年9月),1-19页。
[511]《永历纪年》,页15甲-乙。《岭表纪年》,卷二,页8甲。《永历实录》,卷一一,页5乙。
[512]《永历纪年》,页15乙-17甲。《永历实录》,卷一一,页4甲。《岭表纪年》,卷二,页8甲、9甲。《三湘从事录》,1352页。永历朝廷授官职予佟养甲,但他从未积极支持永历朝,在感情上始终忠于满洲人。此年(1648)稍晚时候,永历朝廷发觉,佟养甲设法与北方的清人联络,于是在12月将其处死。见《永历纪年》,页21甲。《永历实录》,卷一,页4乙;卷一一,页5甲-6乙。《岭表纪年》,卷二,页22甲。
[513]《岭表纪年》,卷二,页8乙-9乙。《永历纪年》,页16甲。
[514]《风倒梧桐记》,卷一,页3甲。
[515]《永历纪年》,页14乙、16甲。《永历实录》,卷一一,页3乙-4甲。《岭表纪年》,卷二,页10甲-11甲、12乙。《三湘从事录》,1353页。
[516]永历帝还都日期,本书依照《三湘从事录》,1354页。有关此事,该书所载较经常引用的钱秉镫《永历纪年》(页17乙)为可靠。并见《岭表纪年》,卷二,页10甲、11甲-12甲、15甲、16乙、17乙;及《风倒梧桐记》,卷一,页3乙-4甲。瞿式耜再度请永历帝重回桂林,准备经由湖广北进。这一请求也曾得到考虑,但是朝廷感到,这次的时来运转,金、李二人厥功至伟,因此朝廷应迁回肇庆,既接近广州,又在通往江西的主要道路之上,以此鼓励二人。此外,李成栋声言,朝廷须还都肇庆,以证实他的归附行为为合法,否则他不能安定广东人心,也不能维护该省安全。朝廷同意了他的要求。见《永历实录》,卷一,页4甲;卷二,页3甲-乙;《永历纪年》,页17甲;《三湘从事录》,1353页;《瞿忠宣公集》,卷四,页10乙-11乙。永历帝要瞿式耜前来肇庆,式耜抗命,说他仍期望朝廷经桂林入湖广。见《瞿忠宣公集》,卷四,页12甲-13甲、20甲-乙。
[517]《岭表纪年》,卷一,页10甲;卷二,页15甲、23甲。《三湘从事录》,1356-1357页。《永历实录》,卷一,页3乙、4乙。《隆武纪年》,页9甲。
[518]《岭表纪年》,卷二,页2甲。
[519]《永历实录》,卷一一,页6甲。《岭海焚余》,29-30页。
[520]《风倒梧桐记》,卷一,页4甲。
[521]《永历实录》,卷一一,页4乙-5甲。《永历纪年》,页17乙-18甲、19甲、21乙。《岭表纪年》,卷二,页17乙;卷三,页3乙-4甲。《风倒梧桐记》,卷一,页4甲-乙。
[522]元胤本姓贾。其传记见《永历实录》,卷一一,页5乙-8甲。
[523]绍武帝主要支持者黄士俊、何吾驺,因李成栋之荐,在永历朝任大学士。但二人不久感到不为同僚所喜,尤其为楚党同僚所恶(见下注),于是辞职。见《永历纪年》,页27甲-28甲、36甲。《永历实录》,卷一,页4甲、5甲-乙;卷四,页2甲-3甲;卷一九,页2乙。《岭表纪年》,卷二,页13乙、19甲-乙。李履庵《关于何吾驺伍瑞隆史迹之研究》,185-187页。永历朝当时所任命各官员的最详尽名单,见《三湘从事录》,1355-1356页。
[524]袁彭年为策动李成栋归附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是著名文学家袁宏道之侄),时任都御史;丁时魁时任吏科给事中。五虎中其余三人为:左副都御史刘湘客、户科给事中蒙正发、兵科给事中金堡。见《岭表纪年》,卷二,页14乙、23乙;卷四,页3甲。《永历纪年》,页22甲、26甲-乙、28甲、35甲。《永历实录》,卷一一,页6甲;卷二一,页2乙。《风倒梧桐记》,卷一,页4乙。有关金堡生平详情,见《清代名人传》,第一卷,166页。当时有假虎丘图,分别以虎头、虎牙、虎脚、虎皮、虎尾喻五人(《风倒梧桐记》,卷二,页1甲)。李元胤为楚党直接的后盾;在宦官中,楚党最重要的盟友为司礼监庞天寿。著名士大夫王夫之曾短期出仕永历朝,坚决支持楚党。读其《永历实录》时,这一点应予注意。该书《严起桓传》(卷二,页4甲-8甲)尤富同情笔调。见马克穆伦(Ian McMorran):《爱国者与党人:论王夫之与永历朝政治》(The Patriot and the Partisans:Wang Fu-chih’s Involvement in the Politics of the Yung-li Court),载《从明到清》,136-166页,并参黄玉斋:《明季三大儒与永历帝》,载《台湾文献》,一九卷四期(1968年12月),68-70页。
[525]例如大学士朱天麟昆山籍,吏部侍郎吴贞毓宜兴籍;吴党中另一集团,包括大学士王化澄(与朱天麟常不能相得),则来自江西东北部。吴党靠山,自然是马吉翔。宦官中夏国祥则与马吉翔有联。见《永历纪年》,页36甲-乙。《永历实录》,卷二,页2乙-3甲。
[526]《永历实录》,卷一九,页1甲-2甲;卷二一,页2乙。
[527]《风倒梧桐记》,卷一,页3乙。
[528]《岭表纪年》,卷一,页1乙、6甲-乙;卷四,页24乙-25甲。
[529]金堡断言,文武职能截然划分,是高皇帝祖训的要义;而马吉翔之类勋贵行大学士职权,干预每一衙门的事务,为本朝史无前例之事(《岭海焚余》,29-30页)。钱秉镫对于中央与省一级的改革,有更为积极的建议。但他显然也认为,皇帝应与数十位贤人相处,而且不指定其中任何一人为大学士,他还以为,重建府、县一级政府的首要步骤,应是以文官替换武人统治,并再度使武将从属于兵部(《藏山阁集选辑》,第一册,12-15页)。
[530]《永历实录》,卷二,页2乙、5乙;卷一九,页2乙。《岭表纪年》,卷二,页15乙。
[531]《永历纪年》,页20甲-21甲、31甲。《永历实录》,卷一,页4甲;卷二一,页2乙。《岭表纪年》,卷一,页9乙;卷二,页12甲-乙、19乙-20甲。《风倒梧桐记》,卷一,页5乙-6甲。
[532]《永历纪年》,页26甲、27甲。《岭表纪年》,卷三,页1甲-乙。《风倒梧桐记》,卷一,页5乙。
[533]《永历实录》,卷一,页5甲;卷二,页3甲;卷一九,页2乙。《岭表纪年》,卷二,页23甲-24甲;卷三,页3乙;卷四,页3甲。《永历纪年》,页34乙-35甲。王化澄因向土司与宗室卖爵位及文官职务而被参劾。见《永历纪年》,页47乙。《永历实录》,卷二,页2甲。
[534]《岭表纪年》,卷三,页8乙、22甲-乙。《永历实录》,卷一,页5乙。《风倒梧桐记》,卷二,页1甲。《永历纪年》,页32甲。
[535]《岭海焚馀》,51-54页。《永历实录》,卷二一,页3甲-4甲。《风倒梧桐记》,卷二,页1乙。
[536]《永历纪年》,页32乙-33甲。《永历实录》,卷一,页5乙。《岭表纪年》,卷三,页8乙。
[537]《岭表纪年》,卷三,页5甲。《永历实录》,卷一,页6甲。昆明无名氏:《滇南外史》,页7乙。据说陈邦傅伪造诏书及其他拥兵自重的举动,是受了胡执恭的怂恿。此人以前是他的保护者,现在则成了他的特别书记与谋士。此人曾在北京兵部任兵部火房,因此颇识字,于衙门事务亦相当熟悉,现在似乎想利用自己在这两方面的长处,使自己和陈邦傅成为广西半合法的土皇帝。见《永历纪年》,页20甲-21甲;《岭表纪年》,卷二,页5甲-乙。据《风倒梧桐记》卷二,页1甲-乙,孙可望原先向永历朝廷提出的要求,其含义是张献忠曾自称“秦王”。此一说法若是事实,则有助于解释为何孙可望执意要称秦王,而不要其他封号。
[538]《永历纪年》,页33甲-34甲、45乙-46乙。《三湘从事录》,1361页,《风倒梧桐记》,卷二,页1乙。
[539]《永历纪年》,页18乙-19甲。《永历实录》,卷一一,页1乙。陆世仪:《江右纪变》(《绍兴先正遗书》本),页3甲-4甲。
[540]《江右纪变》,页4乙-6甲。《永历实录》,卷一,页4甲-乙。《岭表纪年》,卷二,页13甲。《清世祖实录》,卷三七,页18乙-19甲;卷三八,页17乙;卷四十,页1乙。《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页687甲;第八本,页706-707乙,713甲-714乙。清军领导这次战役的大将军是谭泰,以何洛会为副。
[541]《永历实录》,卷一,页4乙;卷七,页4乙、6甲、7甲;卷一三,页2乙。《永历纪年》,页22乙、24甲。李自成军及其残部,通常亦称为“十三家”。湖广各支明军的猜疑与怨恨,一个原因是何腾蛟与堵胤锡二人的不和,堵胤锡感到,自己因迁就前叛军而受人鄙视。
[542]《永历实录》,卷一,页5甲-乙;卷七,页7甲-乙。《永历纪年》,页24乙-25甲、30甲。《岭表纪年》,卷二,页21乙-22甲;卷三,页2乙、9乙。《三湘从事录》,1359、1361页。“忠贞营”经过梧州所造成的混乱与破坏,见瞿昌文:《粵行纪事》(载《笔记小说大观》),卷一,页5甲-乙。堵胤锡尾随“忠贞营”,最后在广西再度与他们取得了联络。但是这支一度令人望而生畏的军队,在衡州、宾州、南宁间的三角地区,许多部队都溃散了;另一些则内部分裂,折回湖广最南部,最后向清军投降。此外,李锦不久死于南宁,“忠贞营”残余部队的指挥权交于高一功之手。见《永历实录》,卷一,页6甲;卷一三,页3乙。《岭表纪年》,卷三,页12甲。
[543]《永历纪年》,页19甲、21乙。《永历实录》,卷一一,页1乙-2甲。《岭表纪年》,卷二,页24甲。《风倒梧桐记》,卷一,页5甲、6甲。《清世祖实录》,卷四一,页2甲-乙。瞿式耜经常一有机会,就向永历帝作过分乐观的奏报,见于他当时对江西、湖广二省形势的说明。见《瞿忠宣公集》,卷四,页16乙-17甲。
[544]《江右纪变》,页6乙。《永历实录》,卷一,页5甲;卷六,页4乙-5甲;卷一一,页2乙。《清世祖实录》,卷四二,页12甲-乙。《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页706甲。清廷命谭泰仅留汉人老兵驻守江西,并将长江之役以来投降的汉人兵士全部调往北京,重新部署。见《清世祖实录》,卷四二,页15甲。
[545]《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页712甲。《永历实录》,卷七,页4乙。《永历纪年》,页25甲-乙。《三湘从事录》,1359-1360页。《岭表纪年》,卷三,页2乙。《桂林田海记》,页12乙-13甲。
[546]《三湘从事录》,1360-1361页。《永历纪年》,页28甲。《风倒梧桐记》,卷一,页6甲-乙。《清世祖实录》,卷四三,页10乙-11甲。《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页727甲-乙。李成栋死讯于4月18日抵达肇庆,见《风倒梧桐记》,卷二,页1甲。
[547]《清世祖实录》,卷四十,页16甲-乙。参看本书第130页,注3。
[548]《清世祖实录》,卷四五,页13甲-15甲;卷四六,页26甲-27乙。《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页768甲-乙。《永历实录》,页1,页5甲。《岭表纪年》,卷三,页21乙-22甲。《永历纪年》,页39甲。
[549]《清世祖实录》,卷四五,页7乙。《三湘从事录》,1361页。
[550]《清世祖实录》,卷四四,页6甲、9乙-11甲、19乙。参看本书第130页,及第131页,注3。
[551]《清世祖实录》,卷四六,页25甲;卷四七,页6甲-乙。《永历纪年》,页23甲。满洲人在北方大量掳汉人为奴,汉奴时有逃亡,成了清朝方面的严重问题,因此不准窝藏逃人的禁令甚严。有关此一问题,参看刘家驹:《顺治年间的逃人问题》,载《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1967年台北版),第二卷,1049-1080页;杨学琛:《关于清初的“逃人法”》,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十期(10月),46-55页;马奉琛(Ma Feng-Ch’en):《清初满汉间的社会与经济冲突》(Manchu-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ficts in Early Ch’ing),载孙以都(E-tu Sun)及约翰·德·弗朗西斯(John de Francis)编:《中国社会史》(Chi-nese Social History,1956年华盛顿版),343-347页。关于耿继茂,参《清代名人传》,第一卷,415页。
[552]《岭表纪年》,卷三,页22甲;卷四,页5甲。《永历纪年》,页42甲-43甲。《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页744甲、769甲。《清世祖实录》,卷四七,页2甲。惠州、潮州二府的明将事先已与清军勾结,安排好投降,使尚、耿二人能轻易进入广东。见《永历纪年》,页44甲-乙。《岭表纪年》,卷四,页6甲。
[553]《永历实录》,卷一,页5乙、6乙-7甲;卷二,页3乙。《岭表纪年》,卷三,页6甲、8甲-乙、11甲、15乙。《永历纪年》,页37甲-乙。李元胤不愿接掌其养父的军队,于是这支军队就由李成栋的一名部将杜永和统领。但是杜永和原来和诸将平起平坐,诸将不易受其号令,他必须采取一些激烈措施,才能使诸将稍微听命。见《永历纪年》,页29乙、47甲。《永历实录》,卷一,页6甲;卷一一,页6甲-7甲。《岭表纪年》,卷三,页13乙。何腾蛟的湖广总督一职,授予了瞿式耜,但他的职权在其他方面反而有所削弱;湖广撤回的军队是一片混乱,瞿式耜即使只想与何腾蛟一样,对这些军队作最小限度的控制,也极少可能(参看本书第224页,注3,及第225页,注1)。甚至瞿式耜想阻止、调停湖广与广西东部二方军队的冲突,也未能成功。见《岭表纪年》,卷三,页12乙-13甲;卷四,页12甲。此外,瞿式耜自己也承认,他的长处不是带兵,而是运筹帷幄;他的大部分精力用于征集与调度粮饷,而不是上战场指挥。见《瞿忠宣公集》,卷三,页12乙-13甲。按照一位桂林居民的说法,瞿式耜出生于常熟(属南直隶),“是读书的世家,敦诗说礼,樽俎雍容,却不比何督师素娴韬略,出入疆场,到底有些书生气习。”《桂林田海记》,页13甲。
[554]《永历实录》,卷一,页6乙、7乙;卷一一,页7甲-8甲。《岭表纪年》,卷四,页1甲、2甲。《永历纪年》,页43甲-44甲。《风倒梧桐记》,卷二,页3乙。
[555]《永历实录》,卷一,页5乙;卷一一,页7甲;卷二一,页4甲-乙。《岭表纪年》,卷四,页2甲、3乙-4乙。《风倒梧桐记》,卷二,页1甲。袁彭年先前即已辞职,此时因“反正功”大而幸免。他也像李元胤一样,来到朝廷,为五虎中其余四虎辩护。见《永历实录》,卷一,页5乙、6乙-7甲;卷一九,页3甲。《岭表纪年》,卷四,页2甲。
[556]《永历实录》,卷一,页6乙;卷一一,页7乙;卷一八,页2乙;卷二一,页4乙。《永历纪年》,页44乙-45乙、48甲-乙。《岭表纪年》,卷四,页2甲-3甲、6乙-7乙。一位史家说,永历帝即位三年来第一次表现出热情,是在迫害五虎开始之后。见《风倒梧桐记》,卷二,页4甲。
[557]《永历纪年》,卷一,页5乙、7甲;卷一三,页3乙-4甲;卷二一,页4乙。《永历纪年》,页45乙、47乙-48甲、49甲-乙。《岭表纪年》,卷四,页10甲-乙、15乙。瞿昌文:《粤行纪事》,卷二,页3甲。
[558]三路如下:(一)从永州溯河而上,直指全州;(二)从武冈渡过西延河向北;(三)从永明经镇峡关(亦名龙虎关)向南。见《岭表纪年》,卷四,页7乙-8甲、26甲。《永历纪年》,页51乙-22甲。《永历实录》,卷一,页7甲-乙。《清世祖实录》,卷四七,页14乙;卷四八,页16乙-17甲。
[559]《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页769甲-770乙。《清世祖实录》,卷五一,页6乙。《岭表纪年》,卷四,页3甲、4乙、18乙、28甲。《风倒梧桐记》,卷二,页4乙。《永历实录》,卷一,页7乙。《永历纪年》,页55甲。明军防卫广州的统帅是杜永和,叛将则为范承恩。清军攻破广州,杜永和逃入海。据说两名荷兰炮手协助守城(见本书第224页,注1);永历朝廷先前亦曾接受葡萄牙人的军事援助。见查尔斯·R·勃克色(Charles R.Boxer):《葡萄牙援明抗清的远征》(Portuguese Military Expeditions in Aid of the Mings against the Manchus),载《天下月刊》,七卷一期(1938年8月),34页。有关这几次战役中所有大炮种类,见罗香林:《香港新发现南明永历四年所造大炮考》,载《文史荟刊》,一卷一—二期(1959年6月)。
[560]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著、约翰·奥吉比尔(John Ogilby)译:《从联合诸省的东印度公司出使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An Embassy from the East 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1669年曼斯顿版),39页。此书为稀见之籍,E.C.波拉(E.C.Bowra):《满洲人征服广州》(The Manchu Conquest of Canton)一文曾大量引用,该文载《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一卷(1872—1873),92-93页。有关清军攻下广州城以后在广东西部的绥靖措施,见陈舜系:《乱离见闻系》(在《高凉耆旧遗集》内),卷中,页14甲-15甲。
[561]《永历纪年》,页52甲-乙。《永历实录》,卷一,页7乙。《岭表纪年》,卷四,页27甲、28乙-29乙。《清世祖实录》,卷五一,页2乙;卷五二,页15乙-16甲;卷五三,页25乙。
[562]瞿元锡《庚寅十一月初五日始安事略》(收入《荆驼逸史》),见全书各处。《永历纪年》,页52乙-54乙。《永历实录》,卷一八,页2乙-3乙。《岭表纪年》,卷四,页29乙。《桂林田海记》,页13乙-14甲。颜复礼(Fritz Jäger):《瞿式耜的最后时日》(Die letzen Tage des Kü Schï-sï),载《汉学》(Sinica),八卷五—六期(1933年),203页。这位忠实助手是张同敞,为颇引起争议的万历大学士张居正之孙。在文人出身的明朝臣忠中,组织与领导军事确有长才的为数极少,张同敞是其中之一。何腾蛟死后,瞿式耜试图让张同敞接掌湖广诸军,但未获成功,原因大约在于党争,于是湖广明军继续趋于解体。见《永历实录》,卷一八,页2甲-乙。遇害日期是1月8日。在这一点上前引各资料的说法明显不一,究其原因,在于各历法置闰的不同。在某几年(尤其是1648、1650-1651、1653、1659、1662年),南明各历法的置闰,与现今标准的清历不同。见黄典权《南明大统历》(1962年台南版);及傅以礼《残明大统历》,载《二十五史补编》(1937年上海版),第六册,8841-8845页。
[563]《粤行纪事》,卷二,页4甲-乙。当时内廷的焦虑可从下面一件有趣的事看出:皇太后王氏及司礼太监庞天寿乞求罗马教皇英诺森特十世(Innocent X)给予精神上(可能还有政治上)的援助。庞天寿、瞿式耜及瞿式耜最忠贞不二的部将焦琏,先前都曾受洗礼入基督教,或许还将皇室介绍给德国耶稣会士瞿纱微(Andreas Koffler),(此事的大略情形,以及瞿式耜皈依基督教的程度,雅格在《瞿式耜的最后时日》一文有所讨论。)其后,瞿纱微又为永历帝的嫡母、生母两位太后、皇后及太子施洗礼。但瞿纱微除进西洋历供朝廷颁行(以后受到保守官员的反对,见《永历实录》,卷一,页5甲、6乙)外,对永历朝政治的影响甚微。瞿纱微的助手,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曾于1650年随朝廷自肇庆奔梧州。其后允诺将王太后及庞天寿11月1日与4日的两封书信携往梵蒂冈的,正是这位卜弥格。信中乞求教皇为他们的灵魂及恢复明朝而祈祷,并派遣更多天主教神父来华。见桑原骘藏:《明庞天寿致罗马教皇之文书》(《明の龐天寿より羅馬法皇に送呈せし文書》),载《史学杂志》,一一卷(1900年)三期,338-339页,同卷五期,617-630页。有关这两封书信的英译本,见英千里(Ignatius Ying-Ki):《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与天主教》(The Last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Catholicity),载《辅仁学志》,一卷(1925年),25-27页。1658年,卜弥格终于回到了东京湾,带来了教皇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Ⅶ)的复信,信中在精神上大加鼓励,政治上则不作承诺。但此时王太后与庞天寿都已去世,永历帝被迫逃入大西南,卜弥格因此无法见到他了。见伯希和(Paul Pelliot):《卜弥格》(Michel Boym)载《通报》(T’oung Pao),二辑,三一卷,一—二期(1935年),95-151页。
[564]《永历纪年》,页55甲。《永历实录》,卷一,页7乙。《岭表纪年》,页29甲-乙。《风倒梧桐记》,卷二,页5乙。永历朝后期编年事略,见杨云萍:《南明永历时代的研究》,62-84页。在此期间,忠贞营少量残余部队,由高必正率领,避开进攻的清军,进入了贵州。但在贵州受到孙可望袭击,高必正阵亡。其后,在四川东部与湖广西北部交界的崎岖山地,另外几位前李自成部将及几个杂牌的独立武人,与这支一度令人生畏的忠贞营最后残余再度会合。见《永历实录》,卷一三,页4甲-乙。李光璧:《农民起义军在川鄂地区的联明抗清斗争》,载李光璧等人合编的《中国农民起义论文集》(1958年北京版),296-297、300-305页。又见李光璧:《记后明政府的抗清斗争》,载《历史教学》,二卷三期(1951年9月),26-28页。
[565]詹姆斯·B·帕森斯(James B.Parsons):《一次中国农民暴乱的高峰:1644一1646年间张献忠在四川》(The Culmination of a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Chang Hsien-chung in Sze-chuan,1644—1646),载《亚洲研究学报》,六卷三期(1957年5月),387-400页。《清世祖实录》,卷二九,页8乙。佚名:《蜀记》(《痛史》本),页14甲。《怀陵流寇始终录》,补遗,页7甲-乙。四川在明季,并不仅受祸于张献忠,而且这一次也不是张献忠首次侵入四川。见黎光明:《明末清初之四川》,载《东方杂志》,三一卷一期(1934年1月),171-176页。
[566]研究这几个人物,尤其是李定国的近作,最佳者为郭影秋:《李定国纪年》(1960年上海版)。并参李光涛:《李定国与南明》,载《明清史论集》,第二册,591-614页;《清代名人传》,第一卷,490页;第二卷,679页。有关李定国早年生涯的佳作,见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载《滇粹》(1981年杭州重印本),页52甲-58乙。
[567]《蜀记》,页14乙-16乙;《李定国纪年》,78页。关于重庆明将曾英事,见帕森斯:《一次中国农民暴乱的高峰》,174页。
[568]余贻泽:《中国土司制度》(1944年重庆版),第二章。李龙华(Li Lung-wah):《明季对川贵边界地区的控制:明朝政府边疆政策及土司制度的个案研究》(The Control of the Szechuan-Kweichow Frontier Regions during the Late Ming:A Case Study of the Frontier Policy and Trib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Ming Government),国立澳洲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黄开华:《明代土司制度设施与西南开发》,载《明史论集》,211-414页。有关明清控制“土著”制度的比较,见胡耐安:《明清两代土司》,载《大陆杂志》,一九卷七期(1959年10月15日),1-8页。
[569]彼得·R.赖特(Peter R.Lighte):《云南的蒙古人与沐英——在帝国边缘》(The Mongols and Mu Ying in Yunnan:At the Empire’s Edge),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1981年。并参《明代名人传》中傅友德、蓝玉、沐英诸人传:第一卷,468-469、789页;第二卷,1079-1083页;及《明史》,卷一二六。
[570]昆明无名氏:《滇南外史》(在《明季史料丛书》内),页1乙-2乙。《风倒梧桐记》,卷二,页1乙-2乙。
[571]冯甦:《滇考》(《台州丛书》二编本),卷二,页91甲-93乙。有关整个明代以西南土著用于各次战争事,见李龙华:《明季对川贵边界地区的控制》,17-21、31-32页。有关明季土著领袖叛乱事,尤其是四川的情形,见上述此文91-94页;及《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九。
[572]《滇南外史》,页3甲-5乙。《滇考》,卷二,页94甲。
[573]《滇考》,卷二,页93甲-乙、95乙。
[574]《滇南外史》,页5乙-7甲。《滇考》,卷二,页95乙-97甲、98甲。彭孙贻:《平寇志》(1931年重印康熙刊本),卷一二,页11甲。《李定国纪年》,79-80,88-89页。抵抗沙定洲、支持沐氏的最主要明朝文官,是云南道监察御史杨畏知。此人以后名列孙可望驻永历朝廷的使节。
[575]《滇南外史》,页6甲、7甲-乙。《滇考》,卷二,页97乙。
[576]《滇考》,卷二,页97乙。《滇南外史》,页8甲。艾能奇不久出使四川,被杀;刘文秀则甘愿归顺孙可望。
[577]费密:《荒书》(怡兰堂丛书本),页28乙。《怀陵流寇始终录》,补遗,页10乙。
[578]沈荀蔚:《蜀难叙略》,页11乙-12甲。《荒书》,页29甲-31乙。《怀陵流寇始终录》,补遗,页11甲。《平寇志》,卷一二,页11乙。《清世祖实录》,卷六九,页11乙-12甲。
[579]《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页274甲;第六本,页550甲;丙编,第八本,页785甲-786甲;第九本,页822甲、833甲。《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165、169-172、182-184、258-266页。《清世祖实录》,卷七一,页12乙-13甲;卷七六,页7甲-乙;卷九二,页8甲;卷九三,页2乙-3乙,洪承畴:《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1937年上海版),第一册,112、118页。
[580]《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页306甲、333甲;丙编,卷九本,页812甲、813甲、828甲。《清世祖实录》,卷六五,页21甲-乙。《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178-179页。据说李定国军一日夜行进三百里,抵达桂林,“如从天而降,从地而涌一般”。见《桂林田海记》,页16甲。
[581]《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页812甲、813甲、823甲、856甲、877甲-878乙。《清世祖实录》,卷七六,页7甲。《桂林田海记》,页17甲。《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176-178、187-188、190页。
[582]《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页300甲-乙;丙编,第九本,页856甲-乙、877甲-878乙。《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195页。《清世祖实录》,卷七七,页20乙;卷八一,页9乙。《桂林田海记》,页17甲-18乙。
[583]《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页884甲。《乱离见闻录》,卷中,页17乙-18乙、21乙-22甲。《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248、289页。
[584]《明清史料》,丙编,页887甲。《清代档案》,第六辑,243-245页。《清世祖实录》,卷八六,页20乙-21甲。《乱离见闻录》,卷中,页22甲-乙。《滇南外史》,页9乙。李定国同时派出几支军队再度骚扰梧州地区。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页149甲-150甲。
[585]《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页885甲-886甲、887甲-乙、893甲-乙。《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245-247、272-274页。《乱离见闻录》,卷中,页22乙-23甲。《清世祖实录》,卷八四,页6甲;卷八七,页16乙-17甲;卷八九,页11乙-12甲;卷九一,页6甲-乙。《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45乙-47乙。《李定国纪年》,133-135页。屈大均《安龙逸史》(《嘉业堂丛书》本),卷下,页10甲。《平寇志》,卷一二,页12甲。有关李定国与郑成功未能结盟的第二手著述,见朱锋:《李晋王与郑延平》,载《台湾文献》,一二卷三期(1961年9月),155-158页;金成前:《郑成功李定国会师未成之原因》,载《台湾文献》,一六卷一期(1965年3月),115-127页;谢浩:《李郑的事功及其联军与联婚的研析》,载《南明暨清领台湾史考辨》,28-162页;魏永竹:《郑成功南下勤王之探讨》,134-136页。
[586]《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页892甲-乙。有关徐勇事,见《清世祖实录》,卷六七,页5甲;卷六八,页31甲;卷六九,页3甲;卷七十,页10乙。《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页347甲。孔有德事,见《清世祖实录》,卷六六,页2甲。《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页300乙;丙编,第九本,页874甲-875乙。《桂林田海记》,页16甲。尼堪事,见《清世祖实录》,卷六六,页9乙-10乙;卷六七,页4乙-5甲。《永历实录》,卷一四,页4乙。此外,多尔衮(时年39岁)于1650年12月31日去世(《清世祖实录》,卷五一,页10乙-11甲),博洛(时年40岁)及勒克德浑(时年24岁)分别于1652年4月及5月去世(《清世祖实录》,卷六三,页14甲、26甲)。其后清朝领导层一直在作调整。济尔哈朗(时年57岁)亦于1655年6月去世(《清世祖实录》,卷九一,页14甲-乙)。
[587]《清世祖实录》,卷六七,页6甲。《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页821甲、833甲-乙;第十本,页928甲。《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185-187页。清廷认识到了华南与西南的重要,也懂得若要真正取得控制,军事和文治的手段都得采用,因而在1653年6月,将总督洪承畴调往武汉,授予经略湖广、两广、云贵五省的广泛权力。见《清世祖实录》,卷七五,页22乙-23甲;《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页305甲、333甲。自1652年秋起,因北方水灾与南方干旱,清廷亦开始担心给养短缺(《清世祖实录》,卷六七,页25乙-26甲;卷七九,页18甲;卷八五,页14乙、15乙;卷九六,页5乙-6甲)。洪承畴确实最能应付此一问题。虽然起先清廷持乐观态度,只命洪承畴“教化”云贵,但他不久即发现,仅在湖广一地,问题就很多,清朝的控制也只是表面的,他于是用更渐进的方法来作绥靖。见《清世祖实录》,卷七九,页14乙-15乙。《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页583甲;丙编,第二本,页157乙。《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一册,68页。对于1652年清朝在湖广所遇到的问题的生动描述,见《明清史料》,第九本,页822甲;《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180-181页。这几年中,清朝收获甚微,有关进一步的证据,见刘翠溶:《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减免赋税的过程》,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三七卷二期(1967年),760至761页间图表。该表显示,在整个清初时期,因水旱而起的大量免征赋税,集中于1652—1654年间。
[588]《永历实录》,卷一四,页4甲-5甲。《滇南外史》,页9甲。《安龙逸史》,卷下,页6乙-7甲。
[589]《永历实录》,卷一,页8甲。《滇南外史》,页8甲。《安龙逸史》,卷上,页20甲。《风倒梧桐记》,卷二,页5乙-6甲。
[590]《安龙逸史》,卷上,页22乙-24甲。《清世祖实录》,卷五九,页12乙;卷六四,页6甲-乙。江之春:《安隆纪事》(《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本),311页。自从万历后期以来,安南就分为互相敌视的南北两个政权,清军占领两广以后,安南决无可能抵抗清朝的压力。虽然在1659年8月以前,安南人并未正式成为清朝藩属,但事实上在此之前,安南人已多年赞成清朝,并阻挠南明的事业。见彭国栋:《南明中越关系史话》,载《中越文化论集》(1956年台北版),第二册,256-258页;陈以令:《明代与越南、高棉、寮国的邦交》,载《中国外交史论集》(1957年台北版),第一册,5页;张效乾:《明清两代与越南》,载《大陆杂志》,三五卷三期(1967年8月),19页。郑成功的使节经过安南时受阻,不能到达云南永历朝廷。有关记载,见徐孚远:《交行摘稿》(1961年台北版)。
[591]《安隆纪事》,313页。《滇南外史》,页8乙。《安龙逸史》,卷下,页1甲-2甲。《蜀难叙略》,页13甲。
[592]黄向坚:《黄孝子寻亲纪程》(收入《笔记小说大观》),页3甲。
[593]皇帝以前曾两次设法取得李定国援助,分别是在1652年12月及1653年仲夏。见《安隆纪事》,313-316页。
[594]上书,315-319页。关于所有这一系列事件的彻底研究,见朱希祖:《永历大狱十八先生史料评》,载《国学季刊》,二卷二期(1929年12月),237-259页。
[595]当李定国留下一妾及她的家人离开之后,清军迅速进驻李定国原在广西的各据点,并击败了他的殿后部队。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页157甲-乙;第十本,页912甲-乙。《清世祖实录》,卷九八,页11甲;卷一百,页3乙;卷一零一,页13乙;卷一零五,页19甲。
[596]《安龙逸史》,卷下,页10乙-15甲、17乙-18甲。《滇南外史》,页9乙。
[597]《安龙逸史》,卷下,页16乙-17甲、18乙。
[598]《安龙逸史》,卷下,页18乙-21甲。杨德泽:《杨监笔记》(1910年《玉简斋丛书》本),页3乙、4乙、7甲-乙。胡钦华:《求野录》(《明季稗史初编》本),331页。《滇南外史》,页9乙。
[599]《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页579甲-乙、582甲-583乙;丙编,第二本,页176甲。《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册,页296-297。《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页7甲-乙;卷一一七,页2甲-乙、6甲。《安龙逸史》,卷下,页22甲。《杨监笔记》,页6甲。
[600]郭适(Ralph C.Croizier):《国姓爷与中国民族主义:历史、神话、英雄》(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History, Myth, and the Hero,1977年麻省剑桥版)。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国姓爷诸战役:近松的傀儡剧及其背景与意义》(The Battles of Coxinga:Chikamatsu’s Puppet Play, Its Background and Importance,1951年伦敦版),引言及三、四二章。中国学者中,娄子匡是研究民间传说中郑成功生平的先驱。有关他的四篇文章,见参考书目。
[601]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载《幼狮学志》,一一卷二期(1973年6月),10、18页;石万寿:《明郑的军事行政组织》,载《台湾文献》,二六卷四期—二七卷一期(1975年12月—1976年3月;二期合刊),50-66页。
[602]尼尔斯·斯蒂斯哥哈德(Niels Steensgaard):《十七世纪的亚洲贸易革命》(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973年芝加哥版),第一部第三章及第三部第九章。卫思韩:《胡椒、枪炮与谈判:1662—1681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Pepper, Guns, and Parleys: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1662—1681,1974年麻省剑桥版),尤见第一章。张天泽(Chang T’ien-tse):《1514至1644年的中葡贸易》(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1934年莱顿版)。全汉升(Han-sheng Chuan):《明末叶至清中叶中国与西属美洲的丝绸贸易》(The Chinese Silk Trade with Spanish America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Ch’ing Period),载劳伦斯·汤普森(Lawrence Thompson)编:《亚洲研究》(Studia Asiatica)(1975年旧金山版),99-117页。艾维四:《1530—1650年间国际金块流通与中国经济》(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载《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九五卷(1982年5月),68-90页。
[603]黄玉斋:《明郑抗清的财政与军需的来源》,载《台湾文献》,九卷二期(1958年6月),17-21页。山胁悌二郎(Yamawaki Teijirō):《大贸易商、国姓爷及其子嗣》(The Great Trading Merchants, Cocksinja and His Son),载《亚洲学志》(Acta Asiatica),三十卷(1976年),111-112页。郑成功在其生平事业中,从何处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获得战士,有关概述见石万寿:《论明郑的兵源》,载《大陆杂志》,四一卷六期(1970年9月),20-29页。
[604]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附录二,290-329页。苏梅芳:《清初迁界事件之研究》,载《历史学报》,五卷(1978年7月),367-425页。
[605]庄金德:《郑氏军粮问题的研讨》,载《台湾文献》,一二卷一期(1961年3月),55-60页。方豪:《由顺治八年福建武闱试题论郑氏抗清的主力》,载《大陆杂志》,二二卷六期(1961年3月),1-20页。黄玉斋:《明郑抗清的财政与军需的来源》,21-32页。
[606]《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7甲-乙。《台湾外纪》,119页。石万寿:《论郑成功以前的兵镇》,5-6页。
[607]《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8乙-26乙。《榕城纪闻》,8页。《航澥遗闻》,页5甲-乙。《清世祖实录》,卷六六,页4乙。郑成功刚从这次战役中撤出,就首次会见了来自广西的李定国使节,并回派部下一人,谈判将来可能的联合行动(《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28甲-乙)。
[608]《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页276甲;丁编,第二本,页116甲-167乙。《清世祖实录》,卷七十,页26乙-27甲。《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28乙、30甲-32乙。许多官员急着要没收郑氏所有之田,以供支付军饷之用。据说郑氏之田,值银数十万两。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页164甲。有关每次满洲人驻兵福州,当地人民的遭遇,《榕城纪闻》有生动描述,见该书5-6、10-11、13-14页。
[609]《清世祖实录》,卷六六,页18乙;卷六七,页1乙-2甲。庄金德:《郑清和议始末》,载《台湾文献》,一二卷四期(1961年12月),1-40页。
[610]《清世祖实录》,卷六九,页6乙-7乙。
[611]《清世祖实录》,卷七二,页17乙-18甲。《榕城纪闻》,8页。
[612]《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卷28甲-29甲。
[613]《清世祖实录》,卷七五,页8乙-10乙。《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页84甲-87甲。
[614]《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卷34甲-35乙。
[615]《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页91甲-乙。《清世祖实录》,卷七五,页20甲、21甲;卷七八,页13乙;卷七九,页3甲-7甲。
[616]《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34甲。
[617]《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36甲-38甲、41甲-42乙、43甲、44乙-45甲、57甲。《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页107甲;己编,第二本,页197甲-乙。1650年代,郑成功亦在福建内陆设法“招抚”不法之徒以为兵源。他推行这一政策,是因为考虑到了自己在福建军事上的弱点,其后果亦与清朝所遇到的相似。自丙申、丁酉行招抚之令,山贼愈多。欲做官须先做贼,年余,以盗劫物赂当事者招安,为投诚官,招摇街市,人不敢言,仇不敢指。……永北里有贼既投诚,人皆不防,行劫如故,曰:“我投诚经费若干,兹于汝等取偿。”地方告于当事,不准。督、巡两院招安多者,即为首功进爵,名利俱得。(《榕城纪闻》,12页)
[618]《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29甲、39甲-40甲。《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页337甲、341甲-乙、346甲;丁编,第二本,页109甲。《文献丛编》,卷一三,页11甲-12乙、13甲、14甲、15甲、16乙-17甲。《清世祖实录》,卷七九,页22乙;卷八十,页9乙、10乙;卷八一,页12乙-13甲;卷八三,页6甲。《航澥遗闻》,页5乙。并参李学智:《重考李振华先生〈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载《大陆杂志》,七卷一一期(1953年12月15日),7-8页;七卷一二期(1953年12月30日),21-27页;及廖汉臣:《鲁王抗清与二张的武功》,93-100页。
[619]《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41甲-乙。1653年(农历)五月曾有数信,显然已遗失(上书,页32乙-33甲)。
[620]《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38甲-39甲。《清世祖实录》,卷八三,页9乙、17乙-18甲。
[621]《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43甲-44乙。《清世祖实录》,卷八五,页6甲-乙。《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页544甲。
[622]《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页97。
[623]《清世祖实录》,卷八四,页25乙-26甲;卷八五,页3甲-4甲。《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页106乙。《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45甲-乙、48甲。
[624]《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45甲-49乙、53乙。《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页106甲-乙。朱希祖:《延平王受明官爵考》,102页。郑成功在第二轮“和议”破裂后,于11月底开始准备援助李定国。见《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55甲-56甲。但他在冬季信风期间所派先遣队,于次年夏归来,并未与李定国联系上。见夏琳:《海纪辑要》(1958年台湾版),14-15页。《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68乙。并参第180页,注1。
[625]《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48甲、49乙、51甲-52乙、53乙。
[626]《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49乙、53乙-54甲。《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页106甲-107乙。《清世祖实录》,卷八七,页4甲、6乙-7甲。
[627]《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50甲-乙。
[628]《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52乙-53甲、54乙。
[629]《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页106甲-107甲。
[630]《清世祖实录》,卷八七,页15甲-16甲。《清代名人传》济度传(第一卷397页),有关此一任命的日期有误。
[631]《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56甲-57甲,《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页545甲-乙。
[632]冯甦:《见闻随笔》(在《台州丛书》甲编内),卷下,页19乙-20甲。《清世祖实录》,卷一〇四,页13乙;卷一一三,页11乙、12甲-乙、15乙-18乙;卷一一六,页5乙-6甲;卷一一七,页23甲;卷一一八,页2乙-3甲;卷一二〇,页7甲。这段时间内,仍活跃于南宁、衡州、宾州的前流寇部队,不是被击败,就是被逐出广西,逃入了交趾(越南西北部)边界地区。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页955甲。《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五,页13甲-乙;卷一一七,页22甲。
[633]《求野录》,331-332页。《安龙逸史》,卷下,页23甲-24甲。《杨监笔记》,页10甲-乙。《见闻随笔》,卷下,页19乙。尤为可悲的,是李定国与其以前的叛军中“兄弟”刘文秀的互不信任。1658年3月,刘文秀绝望而死。
[634]《求野录》,333页。《安龙逸史》,卷下,页25乙-26甲。《杨监笔记》,页7乙。《滇南外史》,页9乙-10甲。土司可能叛乱,一直是一个问题(见下注)。
[635]《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四,页7甲-乙;卷一二三,页2甲-4甲。王先谦等撰:《十二朝东华录》(1963年台北版)。顺治十五年八月十一日,吴三桂成功地肃清了北路,但他只是在厚赂当地各土司,取得他们合作之后,才得以击败李定国部下诸将。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二〇,页7甲。《怀陵流寇始终录》,附录,页12甲。《李定国纪年》,160页。吴三桂及其他清军将领奉到命令,不可搔扰、激怒土著居民,其头领若来归顺,当宽厚对待。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五,页14乙-15甲;卷一一二,页15乙-16甲。
[636]《杨监笔记》,页10乙-14乙、15乙。《求野录》,333页。《安龙逸史》,卷下,页26乙-27甲。《见闻随笔》,卷下,页20甲。
[637]《杨监笔记》,页11乙-12甲、15甲、17甲-26乙。《安龙逸史》,卷下,页27乙-28乙。《求野录》,333-334页。邓凯:《也是录》(《明季稗史初编》本),345页。《见闻随笔》,卷下,页20乙。
[638]《杨监笔记》,页8乙-10甲、29甲-36乙。《安龙逸史》,卷下,页28乙-29乙。《也是录》,345页。《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七,页12甲-13甲。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卷四页,3甲-乙;刘茝《狩缅纪事》,6页;《李定国纪年》,171页。
[639]《杨监笔记》,页33甲-34甲。《求野录》,335页。《也是录》,345页。《狩缅纪事》,7页。《怀陵流寇始终录》,附录,页12甲-乙。据《也是录》,永历帝一行所经过的是铁壁关;但《狩缅纪事》所述道里远近,更为精确,据此书,此关当为北面的铜壁关。永历朝廷奔亡缅甸途中诸事,欲确定其日期颇为复杂,原因如下:《杨监笔记》(《乃一回忆录》)虽按时间先后记事,但不精确;当时永历与清朝所用历法不同(详见本书第225页,注1);《求野录》与《也是录》两书,将这一年记历正朔的正月与闰正月所发生之事合并叙述。
[640]《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五,页28甲-乙。《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页595甲。
[641]《安隆纪事》,311-314页。《狩缅纪事》,7页。《也是录》,345页。《杨监笔记》,页37乙-38甲。
[642]《杨监笔记》作者杨德泽,其父母为西北回族,为叛军所杀,后来为孙可望军中一战士所抚养。8岁(虚龄)时,被送往云南府,做永历太子的书童,而后受阉,在宫中做太监。因为他年轻,又和皇帝亲近,所以宫内诸人在缅甸蒙难时,他是少数几个未被杀戮的男性之一。见其《杨监笔记》序。《狩缅纪事》作者刘茝,在永历朝有翰林学士与经筵讲官的头衔。朝廷抵达阿瓦后,他与朝廷相失,因而未死。见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1961年北京版),62页。《也是录》作者邓凯,江西吉安人,早年在江西“清流”抗清领袖杨廷麟与刘同升手下任事。后来在云南府出仕永历朝,此后任直接保护皇室的卫队首领,因而拥有武臣衔,但自其著作及以后的生活可见,他是一位文士,他因与马吉翔争吵,而伤残一腿,不料因祸得福,永历朝所有成年男子悉被诛戮时,得幸免于难。见徐鼒:《小腆纪年》(1962年台北版),第五册,914-915页;邵廷宷:《思复堂文集》,《遗民所知传》,页73甲-乙;《也是录》,348页。
[643]见维克多·B.列伯曼(Victor B.Lieberman):《细甸首都由攀固移至阿瓦》(The Transfer of the Burmese Capital from Pegu to Ava),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80年一期,64-83页。
[644]《也是录》,345-346页。《狩缅纪事》,8页。《求野录》,335-336页。
[645]《也是录》,347页。《狩缅纪事》,9页。
[646]《也是录》,347页。《狩缅纪事》,10页。《求野录》,336页。
[647]张城孙:《中英滇缅疆界问题》(1937年北京版),19-23页。维克多·雷伯曼:《冬努缅甸的省政改革》(Provincial Reforms in Toung-ngu Burma),载《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四三卷三期(1980年),548-569页。维克多·雷伯曼:《1540至1620年间缅甸的欧洲人、贸易与统一》(Europeans, Trade, and the Unifcation of Burma,1540-1620),载《远东》。二七卷二期(1980年),203-226页。《明代名人传》思任发传,该书第二卷,1209-1214页。
[648]貌·赫丁·昂(Maung Htin Aung):《细甸史》(A History of Burma)(1967年纽约版),147-148页。《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351-352页。
[649]《也是录》,347-349页。《求野录》,337-339页。《狩缅纪事》,引自《李定国纪年》,180页。
[650]《也是录》,348页。《求野录》,337页。
[651]亭奥:《缅甸史》,149-150页。《也是录》349页。《求野录》,339页。
[652]《杨监笔记》,页40甲-乙。
[653]《杨监笔记》,页40甲-41乙。《也是录》,349-350页。《求野录》,339-340页。
[654]《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页595甲-596甲。《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五,页30甲;卷一二六,页22甲-乙。《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335-338页。
[655]《文献丛编》,卷二四,卷首原件照片(《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排印,338-339页)。又,清廷对洪承畴的指示,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页597甲。
[656]《清世祖实录》,卷一二四,页14乙-15甲;卷一二九,页9乙-10乙。《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页598甲。吴三桂得以在西南建藩,从而导致1670年代的“三藩之乱”,此事实为肇始。有关吴三桂在西南羽翼丰满的军事组织事,参看神田信夫:《平西王吴三桂研究》(《平西王呉三桂の研究》)(1952年东京版);有关三藩之乱,参看曹介夫(Tsao Kai-fu):《康熙与三藩之乱》(K’ang-hsi and the San-fan War),载《华裔学志》,三一卷(1974—1975年),108-130页。
[657]《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页193甲;丁编,第八本,页701乙。《清世祖实录》,卷一三〇,页11乙;卷一三二,页2甲。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292页。刘健《庭闻录》(1968年台北版),20-22页。
[658]《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四,页18乙-20甲。《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199甲-200甲。《庭闻录》,23-25页。在云南,沐氏庄田被授予壮丁,以减轻严重缺粮。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五,页6乙-7甲。
[659]《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四,页22甲-乙;卷一三六,页21甲-22乙;卷一三七,页9甲-10甲、11甲-12甲;卷一三九,页16甲-17甲。
[660]《清世祖录》,卷一四一,页11甲-乙。《清圣祖实录》,卷六,页9甲-10甲。《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页702甲。《十二朝东华录》,康熙元年二月庚午。彭孙贻:《平寇志》,卷一二,页13甲。
[661]载蒋良骐原本《东华录》(系顺治十八年十一月),王崇武《跋永历帝致吴三桂书》照录全文,载《东方杂志》,四三卷九期(1947年5月),37页。并参隐(笔名)《明桂王致吴三桂书》,载《天津益世报》“说苑”副刊,1937年4月24日—26日。
[662]《十二朝东华录》,康熙元年二月庚午。《平寇志》,卷一二,页13甲。
[663]《杨监笔记》,页43乙-45甲。并参《也是录》,350-351页。
[664]《杨监笔记》,页45乙-46甲。4月18日,清帝兴高采烈,将俘获永历帝事告诉礼部;29日举行大典,并发布告谕,庆祝此事。见《清圣祖实录》,卷六,页11甲-乙、13乙-14甲。《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353页。
[665]《也是录》,351页。《求野录》,340页。《杨监笔记》,页46甲-乙。《十二朝东华录》,康熙元年二月庚午。
[666]安熙龙(Robert B.Oxnam):《马上治之:1661—1669年的满洲政治与鳌拜辅政》(Ruling from Horseback:Manchu Politics and the Oboi Regency,1661—1669,1975年芝加哥版)。《清世祖实录》,卷一四四,页2甲-乙。《清圣祖实录》,卷一,页6乙。
[667]官方记载从未提及此事。永历帝被害,据邓凯《也是录》(351页),在5月25日。数日前,永历帝感觉末日临近,遣邓凯出外。北京图书馆藏杨德泽:《杨监笔记》抄本,中有数行为刻本所删(页46乙)。据此数行,永历被害日期是5月19日,但所记年份误。几种清初记载,都不是完全可靠,有关综述及评论,见陈去病:《永明皇帝殉国实纪》,载《民报》二三期(1908年8月),“谭丛”副刊,89-96页。司徒琳:《悲惨结局:永历帝死期考》(The Bitter End:Notes on the Demise of the Yongli Emperor),载《明史研究》(Ming Studies),二一卷(1986年春季),62-76页。吴三桂晋级事,见《清圣祖实录》,卷六,页21乙-22甲;《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页702甲。
[668]《杨监笔记》,页39甲-乙。《清圣祖实录》,卷七,页17甲。《李定国纪年》,184-186页。有关李定国死于何处的专门研究,见《李定国纪年》前言,27-30页。
[669]《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58甲-59甲。
[670]上书,页59乙-60乙。
[671]《清世祖实录》,卷八七,页17甲。《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页545甲;丁编,第二本,页138甲-140乙、152甲-153甲。《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61甲-64乙、71乙-72甲、76甲。夏琳:《海纪辑要》,16页。阮旻锡:《海上见闻录》,20页。
[672]这些官吏的头衔和职掌,在许多情况下与明朝正规用法不同,一个原因是,这类官职为郑成功所独创;另一原因是,避免有僭设王官之嫌。不过,有些官职,在明朝体制中原属低阶,郑成功要求永历朝廷授予高阶,获得允准。见《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66甲-67乙。《海纪辑要》,13页。朱希祖:《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105页。郑成功亦设立特别机构,以容纳曾获明朝科名的“贤”人,并培育殉难的武将子弟。但是有一次,一位将领抱怨说,这些人只是“纨绔”,在战阵之间并无用处,郑成功当即亲自裁决,只有阅历丰富的人才能任监军之职。见《海上见闻录》,17页。郑成功麾下的勋臣及文武官员的详尽名单,见赖永祥:《明郑藩下官爵表》,载《台湾研究》,一卷(1956年),79-101页;二卷(1957年),47-48页。
[673]《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68乙-69甲、72乙-73甲。因郑成功的严酷军纪而逃走的诸人中,最重要的是施琅与黄梧。1651年春,郑成功在厦门欲杀施琅,琅逃去,后投入清朝水师,但未获大用;郑成功死后,施琅则成了清朝征服台湾的主要出谋划策者。见《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5乙-16乙。《台湾外纪》,121-122页。朱维铮:《施琅与郑延平的恩怨》,载《文史荟刊》,一卷(1959年6月),88-95页。《清代名人传》,第二卷,653页。1656年春初,郑军攻潮州府揭阳失利,郑成功严议丧师罪,黄梧亦被责,于是在当年8月投清,将郑氏在海澄最大宗的粮饷军需积聚献于清朝。黄梧因此得到了原先为郑成功所拒的海澄公封号,并获其他厚赏,以后就竭力为清朝效劳,主张除掉郑芝龙。在鼓吹控制沿海地区诸人中,他也是主角。这些控制措施,最终迫使郑氏集团放弃福建沿海,完全退往台湾。见《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76乙、78乙。《海纪辑要》,17页。《海上见闻录》,21页。《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页400甲-乙、406甲、412甲;丁编,第三本,页159甲-60甲。《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二,页22乙;卷一〇三,页10乙、13乙;卷一〇八,页21甲-22甲。《清代名人传》,第一卷,355页。有关施琅、黄梧及郑氏麾下其他逃走或反叛诸将,见金成前:《明郑重要将领史事分述》,载《台湾文献》,二四卷四期(1973年12月),74-78、81-83页;金成前:《施琅黄梧降清对明郑之影响》,载《台湾文献》,一七卷三期(1966年9月),151-166页。
[674]《清世祖实录》,卷八八,页16甲;卷九十,页21甲;卷一〇八,页18乙-19甲。《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页355甲-乙。《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81乙、83甲-84乙。1657年5月初,清廷得到了郑成功对郑芝龙的最后答复,于是敕刑部正式告发芝龙、其弟芝豹、其子四人。顺治帝宽免芝龙死刑,但将其流徙东北极边的宁古塔地方,家产籍没。见《清世祖实录》,卷一〇八,页19乙-20甲;卷一〇九,页3乙-4甲。清廷更恐芝龙从徙所脱逃,由海路遁回东南,与其子会合,因此下令加铁链,手足杻镣,严饬兵丁谨加看守。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一〇,页4甲;卷一一一,页3甲-乙。
[675]《清世祖实录》,卷九二,页10乙;卷一〇二,页10甲-12甲。《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页155甲。秦世禛:《抚浙檄草》(《清史资料》第二辑,1981年),171-172页。
[676]《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二,页18乙-20乙。《明清史料》,己编,第三本,页236甲。
[677]《清世祖实录》,卷八七,页15甲、16甲。《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70乙、72甲、73乙。《海纪辑要》,15页。
[678]《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69甲-70乙、77甲-乙。《榕城纪闻》,15页。北京清廷敕谕济度时,没有料到会如此旷日持久。见《清世祖实录》,卷一百,页8甲。
[679]郑成功与李定国最后通函,正在此时。他再次敦促李定国从西方发动攻势,因为“中原有可乘之机,胡运值将尽之时,宜速乘势,并力齐举。……表里合应,立洗腥膻之穴,然后扫清宫阙,会盟畿辅,岂不大符夙愿哉”。此函载《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41甲-乙。学者多以为,该书所说此函在1654年初春发出,误。但是发信日期究竟是在1656年仲夏,还是在1657年初春,学者看法不一。见张菼:《郑成功纪事编年》,87页;郭影秋:《李定国纪年》,148页。
[680]下文所列各阶段,大体与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所述一致。该文载《台湾文献》,一五卷二期(1964年6月),47-74页。
[681]《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71甲-72甲、73乙-75乙。《航澥遗闻》,页6甲。清廷派驻舟山要塞的,只有骑兵240人,步兵3000人,而且其中只有半数到达。此外,全部水军舰只,当时都在定海检修。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页123甲-乙。明军自舟山出发,深入袭击浙江内地。此一陆上攻击,迫使清朝再次征剿“海寇”的岛上基地。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页338甲;丁编,第二本,页142甲-143甲;己编,第三本,页294甲-295甲、299乙。
[682]《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78甲、79甲-81甲。《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三,页12甲。《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页181甲。《榕城纪闻》,10页。
[683]《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81甲-82乙、84乙-85乙。《榕城纪闻》,10-11页。《清世祖实录》,卷一〇六,页9甲-10乙。《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页409甲-乙;己编,第四本,页395甲。郑成功亦自福宁派兵进入浙江最东南端的温州。见《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85甲。《明清史料》,己编,第五本,页403甲。
[684]张名振卒于1656年1月12日至25日间。见廖汉臣:《鲁王抗清与二张的武功》,102页;及《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页576乙。再度征剿浙江的满洲大将军是伊尔德。有关这次战役,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页376甲-乙、381甲-383乙;丁编,第二本,页161甲、163甲、165甲-乙;己编,第三本,页270甲-乙。《清世祖实录》,卷九六,页11甲-乙;卷九七,页9乙-10甲;卷一〇三,页21乙-22甲、27乙。《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76乙、80乙。《航澥遗闻》,页6甲。
[685]《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85甲-乙。
[686]上书,页88甲-90乙。《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一,页13甲-乙。最近的清军增援部队在天台,不足八百人,但因惧怕郑成功继续进攻,已被派往宁波与定海(该二地的水师守军依然人数不足,令人不可思议)。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页179甲-乙。
[687]《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页181甲。《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一,页22乙-23甲。《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90乙-92乙、94乙。《海上见闻录》,26页。《榕城纪闻》,11页。可能在这年冬天,永历朝廷封郑成功为潮王(第一等藩王),但成功不受。参朱希祖:《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107-109页。
[688]《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95甲-96甲。《海上见闻录》,25页。有关郑氏铁军,见黄玉斋:《明郑抗清的财政与军需的来源》,21-24页。
[689]《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97乙-101乙。《海上见闻录》,27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页421甲-423乙。《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八,页15甲。
[690]《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02乙-104甲、105甲-106甲。《海上见闻录》,28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页429甲-431甲;丁编,第三本,页201甲-204甲;己编,第五本,页428乙、433甲-乙、435甲-乙。《清世祖实录》,卷一二〇,页11乙。
[691]《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06甲-109甲。《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页443甲-444甲、465乙-466甲;丁编,第三本,页206甲、217甲-219乙;己编,第五本,页452甲。《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三,页15乙;卷一二四,页13甲-乙;卷一二六,页9甲。有些清朝地方官疏报,在浙江大胜海上来犯者,其实是大可怀疑的。见《郑成功纪事编年》,106页。
[692]《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09甲-110乙、112甲。《清世祖实录》,卷一二六,页10乙。
[693]《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12乙-113甲、114甲-115乙。张煌言:《北征得失纪略》,载《张苍水诗文集》(1962年台北版),第一册,1页。《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页233乙。郑成功至少三次企图与吴淞清水军统帅马进宝(入清后改名逢知)合作,未果。
[694]自从张名振进攻以来,江南即采取措施,加强水军防御。见《清世祖实录》,卷八三,页4甲-乙;卷九一,页15甲;卷一一二,页15甲。《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页341甲-乙。《明季南略》,第二册,330页。清军在郑成功攻击以后,当然知道,以前所做远远不够。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页8乙-10甲、14乙、17乙-18乙。
[695]《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页11甲-乙、21甲-乙。《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页226甲。郑成功在南京失利的原因,金成前另有补充的看法,见其所著《郑成功南京战败与征台之役》,载《台湾文献》,二五卷一期(1974年3月),45-53页。
[696]李振华:《张苍水传》(1967年台北版)。石原道博:《张煌言的江南江北经略》(《张煌言の江南江北経畧》),载《台湾风物》,五卷一一—一二期(1955年),7-53页。《清代名人传》,第一卷,41-42页。
[697]《明季南略》,第二册,329-330页。《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15乙。
[698]题郑成功、郑经撰:《延平二王遗集》,收入《增订中国学术名著》,第一辑,第八册(1965年台北版),未标页码。
[699]《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16乙-121乙。《北征得失纪略》,2-3页。《明季南略》,第二册,330-332页。《明清史料》,己编,第五本,页491乙-492甲、541甲-542甲;第六本,页539甲;丁编,第三本,页238甲。《清世祖实录》,卷一二六,页22甲。
[700]《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21乙-127乙。《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页6乙、11乙-12甲。据清朝方面估计,南京四周有83营,以通常每营1025人计,总共有85075人。这当然还不包括停泊在附近的郑氏海军,也不包括留驻崇明、瓜洲、镇江的郑军。
[701]这是本书著者所作估计,所依据的是明清双方各自的分散资料,因此与常为人征引的张煌言:《北征得失纪略》所说数目不同(见该书2-3页),清朝方面一项重要史料,在《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页465乙-457甲。
[702]《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21乙-122甲、124乙-125乙、127乙-128甲。《北征得失纪略》,2、5页。
[703]清朝方面主要人物是总督郎廷佐、江南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苏松水军总兵梁化凤,以及满洲梅勒章京噶褚哈、喀喀木。尽管这些人对郑军取得大胜,清廷事后仍是非常沮丧,形象地说,很多红蓝顶子在江南落地。蒋国柱与管效忠甚至被发为奴,家产俱籍没。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页30甲;卷一三三,页16乙-17甲。
[704]《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28乙-130乙。《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页12乙-13甲。《明清史料》,己编,第五本,页490甲。有关死于这次战役的甘辉和其他将领,见金成前:《甘辉周全斌刘国轩与明郑三世》,载《台湾文献》,一六卷四期(1965年12月),133-143页;金成前:《明郑重要将领史事分述》,67-73页。
[705]《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30乙-34甲。《北征得失纪略》,4-6页。《明季南略》,第二册,306-310页。《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页13甲、21甲-乙、22乙。《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页233甲。论郑成功北征的第二手著作,除本书第276页注2所引述的廖汉臣一文外,可参黄玉斋:《明郑成功北伐三百周年的纪念》,载《台湾文物》,七卷四期(1958年12月),123-128页;八卷一期(1959年4月),122-128页;八卷二期(1959年6月),116-124页;八卷三期(1959年10月),146-152页;并参金成前:《郑成功起兵后十五年间征战事略》,88-92页。
[706]《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页3乙-4乙。《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页462甲-乙;丁编,第三本,页243甲、265甲;己编,第五本,页500甲、524乙。《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40甲-141甲。《郑成功纪事编年》,123页。清朝官员中重起辩论:郑成功一旦被逐出厦门,便会占领舟山,因此,是否要劳神费钱,派兵驻守舟山。1661年12月,清廷下令自舟山撤兵,这一次是全面迁海政策的一部分。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页464甲;丁编,第三本,页243乙、250甲-乙。《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九,页2乙-3甲、7乙;卷一四三,页11乙-12甲。《清世祖实录》,卷一,页18乙;卷五,页4乙。
[707]《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34乙、136乙、138甲-乙。《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页462甲;丁编,第三本,页243甲-乙。
[708]《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35乙、138甲-142甲。
[709]上书,页140甲、146乙-147甲。杨英叙述这次战役,头绪欠清楚,谈及清朝方面将领的官职,也不准确。叙述这次战事而首尾条贯者,见《郑成功纪事编年》。
[710]《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46甲-乙。《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八。页14甲-15甲、22甲-23甲。《榕城纪闻》,15、19页。
[711]《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34乙、148乙-149甲。吴密察:《郑成功征台之背景——郑氏政权性格之考察》,载《史译》,一五卷(1978年9月),24-44页。廖汉臣:《延平王东征始末》,载《台湾文献》,一二卷二期(1961年6月),57-84页。1657年夏,何廷斌:(荷兰人称他为平夸[Pincqua])受荷兰人派遣,与郑成功谈判一项交易。而后他和郑氏手下一个主要税吏合谋,在台湾向开往郑氏辖地各处的船只征税。1659年,此事为荷兰人所发觉,何廷斌被解职,并被罚巨款。他便投奔郑氏组织,逃避了罚款。见C.E.S(即揆一[Frederic Coyett])著、伊奈慈·德·博格莱尔(Inez de Beauclair)等编译:《被忽视的“福摩萨”》(Neglected Formosa,1975年旧金山版),19-20、108、111-112页。有关当时台湾的一般情形,见许文雄(Wen-Hsiung hsu):《从土著岛屿到中国边疆:1683年前台湾的发展》(From Aboriginal Island to Chinese Frontier: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before 1683),载那仲良(Ronald Knapp)编《中国岛屿边疆》(China’s Island Frontier,1980年火奴鲁鲁版),12-23页;曹永和:《荷兰与西班牙占据时期的台湾》,载《台湾文化论集》(1954年台北版),105-122页。有关这段时期全亚洲荷兰商业企业的著作,见查尔斯·R.勃克色(Charles R.Boxer):《1600—1800年的荷兰海上帝国》(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1600—1800,1965年伦敦版);M.A.P.梅林克—劳鲁夫兹(M.A.P.Meilink-Roelofsz):《十七世纪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发展诸方面》(Aspects of Dutch Colonial Development in As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载《在欧亚的英国与荷兰》(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in Europe and Asia),三卷本(1968年纽约版),56-82页。
[712]《被忽视的“福摩萨”》,16、19、21-23、25、30、105-107、109-113页。林朝栋:《郑成功克台前台厦之间的经纬》,载《台南文化》,五卷二期(1956年7月),91-98页。苏同炳:《由崇祯六年的料罗海战讨论当时的闽海情势及荷郑关系》,载《台湾文献》,四二卷(1977年12月),1-39页。卫思韩:《胡椒、枪炮与谈判》,23-24页。有关荷郑间的摩擦,见山胁《大贸易商》,107-110页。
[713]《被忽视的“福摩萨”》,27-29页;引文见34-36页。1661年6月,荷兰东印度公司暹罗分部,发一报告给该公司在台湾的同僚,说郑成功已准备“向吕宋或‘福摩萨’”发动主要攻势,但其时郑成功已包围了台湾城(Castle Zeelandia)(同书114页)。
[714]《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49甲-150乙。《被忽视的“福摩萨”》,44页。杨英与揆一的叙述中,日期互不符合,一直令人不解。欲知此一问题的各种解答,见田大熊原著、石万寿译:《国姓爷的登陆台湾》,载《台湾文献》,四四卷(1978年6月),111-121页;陈国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问题》,载《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一期(4月),161页。有关郑成功征服台湾荷兰殖民地的概述,见张菼:《郑荷和约签订日期之考订及郑成功复台之战概述》,载《台湾文献》,一八卷三期(1956年9月),1-18页;查尔斯·R.勃克色:《1661—1662年包围台湾城以及从荷兰人手中夺得“福摩萨”》(The Siege of Fort Zeelandia and the Capture of Formosa from the Dutch,1661—1662),载《伦敦日本学会学报》(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London),二四卷(1926—1927年),16-47页;卫思韩:《胡椒、枪炮与谈判》,25-27页。关于郑成功带往台湾的兵力,见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后的兵镇》,载《台湾文献》,二四卷四期(1973年12月),15-26页。
[715]《被忽视的“福摩萨”》,49-53、57-58、128-130页。《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51甲。
[716]《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51乙-152乙、154乙-155甲。《海上见闻录》,39页。《被忽视的“福摩萨”》,59、64、75页。
[717]《被忽视的“福摩萨”》,70、71-73、75、77-78、131-132、134页。
[718]《被忽视的“福摩萨”》,80-86、134-137页。
[719]《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52乙-154甲。朱锋:《郑氏在台创建政制日期考》,载《台南文化》,二卷二期(1952年4月),50-54页。有关郑成功致吕宋总督唐·萨皮尼阿诺·曼利克(Don Sabiniano Manrique de Tara)的信及其后果,见《郑成功纪事编年》,145-146页;埃玛·布莱尔(Emma Blair)、詹姆斯·罗伯特逊(James Robertson)合著:《1493—1898年的菲律宾群岛》(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1903—1909年克利夫兰版),三六卷《1662—1663年的马尼拉事件》(Events in Manila,1662—1663);弗朗西斯科·孔贝(Francisco Combés):《棉兰老与霍洛史》(Historia de Mindanao y Jolό,1897[1667]马德里版),第八部分,十三章,并参阿方索·菲利克斯(Alfonso Felix)编:《1570—1770年菲律宾华人》(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1570—1770,1966年马尼拉版)一书中米拉格罗·格雷洛(Mi-lagros Guerrero)、拉斐尔·伯纳尔(Rafael Bernal)合撰的第二、三章。
[720]许文雄(Wen-hsiung Hsu):《从土著岛屿到中国边疆》,22页。
[721]方豪:《由顺治八年福建武闱试题论郑氏抗清的主力》,第二部分,18-19页。
[722]有关叛逃事,见《清圣祖实录》,卷三,页13甲;卷四,页2乙;卷六,页6甲。《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页154甲-乙。有关清朝加强沿海政策事,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六,页4乙、6甲;卷一四〇;页2乙-3甲、6甲-乙;卷一四一,页4甲。《清圣祖实录》,卷二,页21乙;卷四,页10乙。庄金德:《郑氏军粮问题的研讨》,59-60页。《榕城纪闻》,23页。
[723]《海上见闻录》,40页。
[724]同上。
[725]《台湾外纪》,第二册,210页。《清圣祖实录》,卷五,页2甲。1662年2月1日在福州公开宣布,郑芝龙已被凌迟处死。见《榕城见闻》,24页。
[726]李腾岳:《郑成功死因考》,载《文献专刊》,一卷三期(1950年),54-64页。并参《清圣祖实录》,卷六,页27乙-28甲;《航澥遗闻》,页5甲。
[727]《张苍水诗文集》,29-31页。并参毛一波:《郑成功与张苍水》,载《台湾风物》,四卷四期(1954年4月),4-10页。
[728]《张苍水诗文集》,42-44页。张煌言在南田附近一小岛被清军俘获,1664年被害。参看第227页,注3。
[729]《航澥遗闻》,页5甲。陈汉光:《鲁唐交恶及鲁王之死》,113-114页。下述诸文录有鲁王墓志铭:鲁德福著《明监国鲁王真墓》,486-487页;陈汉光、廖汉臣著《鲁王史迹考察记》,载《台湾文献》,一一卷一期(1960年3月),119页;朱锋《金门发现的南明碑碣二件》,载《文史荟刊》,二卷(1960年12月),100页。有关鲁王墓的其他研究,见黄仲琴、夏廷棫:《金门明监国鲁王墓》,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六卷六九期(1929年2月),2805-2808页。
[730]大顺军老将李来亨,率领李自成军最后残部,在湖广西南部僻远的房县山区坚持数年。他们拥戴一个来自陕西自称明汉王的人,宣布成立“后明”政权。但是此人是否真是汉王,无从证实。清军在1664年秋最终突袭叛军最后据点,将此政权消灭之前,此人显然已死,因而更无从证实。参看本书第226页注1所列李光璧著作,以及查继佐著《罪惟录》选辑(《台湾文献丛刊》一三六种),第二册,74-75页。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由其子郑经领导。1681年郑经卒,名义上由成功孙克塽接掌。1683年,清军最终征服台湾,克塽降。郑成功的两位继承人虽然奉明正朔,郑经而且与清闽藩耿精忠有过松散的合作,从而协助了1674—1680年间反满洲人统治的三藩之乱,但是他们并未推举任何明朝宗室来继承永历帝或是鲁王。有关这段时间的台湾以及清初历史,已有不少文章。可靠的概述,见盛清沂等著:《台湾史》(1977年台中版),152-240页。一位明朝宗室宁靖王,随郑军来到台湾,受到郑成功的礼遇,却为郑经所冷落,并被剥夺俸给。而后就住在今台南以南的竹沪村,处境艰困。1683年,清军舰队逼近台湾,他与二妃三妾(四个子女已前卒)自尽殉明。见陈汉光:《明宁靖王及五妃文献》,载《台湾文献》,二十卷三期(1969年11月),45-64页。崇祯帝男性后裔中最年幼的朱慈焕,在清朝夺取天下后得不死,用假名默默度日,直至18世纪的最初几年,他“朱三太子”的真身份方为人所知。1707年浙江和江苏的两次反清起义,就是被这消息激发出来的。朱慈焕于是被清朝发现,于1709年初秘密处死。许多人以为,此一事件是天地会成因。蕴蓄“反清复明”宗旨的秘密社会中,天地会是最重要的,贯穿于其后的整个清朝历史。有关“朱三太子案”的文件,见《革命远源》(1963年台北版),第二册,298-308页;有关此案详情及介绍天地会文献,见竺沙雅章:《朱三太子案》(《朱三太子案について》),载《史林》,六二卷四期(1979年),1-21页。
[731]引用中文书目,原编按繁体字笔顺排列,现改简体,笔顺依旧。——译者



